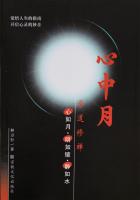一个好奇的和尚问师父:“道是什么?”
“它就在你的眼前。”师父说。
“为什么我看不到?”那个和尚问。
“因为你在想你自己。”师父说。
“你呢?”那个和尚说,“你看得到它吗?”
师父说:“只要你看到‘二’,说我不要,你要,等等,你的眼睛就被遮住了。”
“当既不是我,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看到它吗?”那个和尚说。
“当既不是我,也不是你,那么谁是那个想要看它的?”师父回答。
是的,道就在你的眼前,但你的眼睛并不是就在道的前面,它们是闭起来的,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闭起来。它们是被遮住的,有无数的思想遮住它们,有无数的梦飘浮在它们上面;任何你曾经看过的都在那里,任何你曾经想过的都在那里,而你已经活了很久——有很多世了,你曾经想了很多,它全部都聚集在你的眼睛,但因为思想是看不到的,所以你以为你的眼睛是清晰的,事实上,那个清晰并不存在,有好几百万层的思想和梦在你的眼睛里。道就在你的面前,一切的存在就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并不在这里,你没有处于那个静止的片刻——在那里,眼睛是完全空的、没有被遮蔽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是的。
第一件必须加以了解的事是:如何达到没有被遮蔽的眼睛;如何使你的眼睛变成空的,这样它们才能够反映真理;如何在内在不要一直疯狂地赶来赶去;如何不要一直思考、思考、又思考;如何将思想放松下来,当思想不存在,那个“看清”就发生了;当思想存在,你会继续解释,同时继续错过。
不要成为一个真相的解释者,要成为一个有洞见的人;不要去想它,要直接看清它!
要怎么做呢?有一件事:每当你看,就只是看。试试看!它将会很困难,之所以困难只是因为旧有的习惯,但是试试看!它会发生,它曾经发生在很多人身上,所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你并不是例外,宇宙的法则对一个佛或是任何人来讲跟对你是一样敞开的,只要作一些努力。
你看一朵花,就只是看,不要说什么。河流在流动,你只要坐在河边看河流,什么话都不要说。云在天空中移动,你只要躺在地上看,什么话都不要说,不要将它化成语言!
将每一件事化成语言是一种最根深蒂固的习惯,这是你的整个训练——立刻从真相跳到文字,立刻开始形成文字:“很美的花”,“可爱的落日”。如果它很可爱,那么就让它是可爱的!为什么要将话语带进来?如果它很美,你认为你的话语会使它变得更美吗?相反地,你会错过狂喜的片刻。语言介入了,在你能够真正看清之前,你移开了,移到内在的歧途,如果你在这个歧途走得太远,你会发疯。
疯子是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回到真相,他一直徘徊在他自己的语言世界里,他逛得太远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将他带回来。他没有跟真相在一起,但是你跟真相在一起吗?你也没有跟真相在一起。那个差别就只是在于程度。一个疯子逛得太远了,你从来没有逛那么远,只是在附近,你一再地回来碰触真相,然后再去逛。
你在某一个地方还有一些碰触、一些接触,虽然被拔了根,但是似乎有一条根还在真相里,但是那条根非常脆弱,它随时都会断掉,任何意外事件——比方说太太死了,或是先生离家出走,或是你破产了,那根很脆弱的根就断掉了,你就继续在歧途逛来逛去,不知道要回来,然后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碰触到真相,这就是疯子的状态,而正常人跟他们的差别就只是在于程度而已。
一个佛,或是一个成道的人,一个在道上的人,或是一个有了解、有觉知的人的状态是怎么样?他深深地根植于真相之中,他从来不会从它跑出去,刚好跟疯子相反。
你在中间,从那个中间点,你可以走向成为一个疯子,或者你可以走向成为一个佛,它依你而定。不要给思想太多能量,那是自毁的,你在毒化你自己。每当思考开始,如果它是不必要的——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它是不必要的——你就要立刻把你自己带回真相。任何事都能够有所帮助,甚至只是碰触一下你所坐的椅子,或是碰触一下你所躺的床。感觉那个碰触,它比你在思考神来得更真实,它比你在思考神来得更富有神性,因为它是真实的东西。
碰触它,感觉那个碰触,成为那个碰触,要在此时此地。你在吃东西吗?好好地去感觉那个食物的味道、那个气味,好好地闻它、嚼它——你在嚼真实的存在!不要一直在思想的歧途上乱逛。你在洗澡吗?享受它!那个莲蓬头的水冲在你身上,感觉它!变得越来越是一个感觉的中心,而不是一个思考的中心。 是的,道就在你的眼前,但是你不太允许感觉存在。社会以一个思考的人把你带大,而不是以一个感觉的人把你带大,因为感觉是不能预测的,没有人知道它会引导到哪里,社会不能让你自己来。它给你思想,所有的学校、专校和大学都是在训练你的思考,使你更加语言化。你能够用越多的语言,你就被认为是越有才华;你越善于言辞,你就越被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它将会很困难,因为你受了这样的训练已经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六十年了……但是如果你能够越早开始就越好。把你自己带回真实的存在里。
这就是所有增进敏感度的团体的意义。在西方,那些团体已经变成了一个焦点,所有对意识或意识的扩张有兴趣的人都对增进敏感度的团体有兴趣,对训练得更敏感有兴趣。你并不需要去任何地方学习它,整个生活就是敏感度,一天二十四小时,真相都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周围,围绕着你;你在它里面呼吸,你吃它。不论你做什么都跟真相有关。
但是头脑会走到很远的地方。在你的存在和你的头脑之间有一个空隙,它们不在一起,头脑在其他某一个地方。你必须在此地的真相里,因为当你吃东西,你必须吃真实的面包,光想面包是不会有帮助的;当你洗澡的时候,你必须洗一个真正的澡,光想它是没有用的;当你呼吸,你必须呼吸真正的空气,光想它是没有用的。真实的存在从每一个地方围绕着你,从所有的方面碰撞着你,不论你去哪里,你都会碰到它。
那就是“道就在你眼前”的意思,它到处都是,因为不可能有其他东西存在,只有那个真实的存在。
那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人们一直在找寻,却从来找不到它?为什么会有那个问题存在?这整个困难的基本核心在哪里?那个困难就是:头脑可能会在思想里。头脑停留在思想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身体处于真实的存在里,但是头脑可能停留在思想里,那就是二分性。你们所有的宗教都赞成头脑,而不赞成身体,那一直都是存在于这个世界里最大的障碍。他们毒化了人类的整个头脑,他们赞成头脑,不赞成真相。
如果我告诉你说:当你吃东西的时候,要仔细品尝那个味道,吃得很融入,融入到连那个吃者都被忘掉了,只是变成吃的过程——你将会感到很惊讶,因为没有一个宗教会这样说。宗教人士一直在教导: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品尝那个味道,他们认为训练人们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品尝味道是很棒的。
在甘地的社区里,他们有十一个规则,其中一个就是吃东西不能品尝滋味,要完全扼杀味觉。喝饮料,但是不能品尝滋味。要使你的生活变得尽可能不敏感。完全把你的身体弄得死气沉沉,这样你才会变成一个纯粹的头脑,你将会变成这样,但人们就是这样在发疯的。
我的教导刚好相反,我不反对生命,生命就是道。我完全肯定生命,我不是一个否定者,我不是一个拒绝的人,我想要把你的头脑带回到真相里。你的身体比你的头脑更真实。你可以愚弄头脑,但是你没有办法愚弄身体。身体更根植于世界里,身体比你的头脑更是存在性的,你的头脑只是心理的,它会思考,它会编织文字,它会创造系统,而所有的系统都是愚蠢的。
有一次,木拉那斯鲁丁在赌马。第一回合他输掉了,第二回合他也输掉了,然后第三回合——他继续输,有两个坐在他旁边包厢的女士一直在赢,每一个回合都赢。
到了第七个回合,他已经忍不住他的好奇心。她们是遵循什么系统?每一个回合,现在已经是第七回合了,她们都是赢家,而他一直都是输家,况且他很用心在赌,所以他就鼓足勇气靠过去问那两个女士:“你们赌得很好,是吗?”
她们很高兴地说:“是的。”话语之间洋溢着快乐的表情。
所以他就低声说:“能否告诉我你们的系统?只要一个暗示就可以了。”
其中有一个女士说:“我们有很多系统!但是今天我们决定压长尾巴。” 但是所有的系统和所有的哲学都只是像那样——长尾巴的。没有一个系统忠于真相,因为没有一个系统可以忠于真相。我并不是说某些系统可以——不,所有的系统都无法忠于真相,因为所有的系统都是头脑所伪造的,都是你的解释,都是你的投射,都是头脑将它化成语言的——这是头脑在真相上面操作。一个系统就是这样诞生的,所有的系统都是假的。
真相不需要系统,真相需要清晰的洞见。去看它不需要哲学,它就在此时此地。在你进入一个哲学之前,它就在那里了;当你回来,它还是在那里,它一直都会在那里跟你在一起,而你却去想它。想它是错过它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是一个印度教教徒,你将会错过;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将会错过;如果你是一个回教徒,你将会错过;每一种“主义”都是一种错过的方式。如果你的头脑里有古兰经,你将会错过;如果你的头脑里有吉踏经,你将会错过,不论你携带着哪一种经典——经典是头脑,真相没有办法跟头脑并存,真相不会去管你的头脑和你的伪造。
你编织出很美的故事,你给出很美的论点,你找出合乎逻辑的合理化解释。你很努力编织,你继续精炼你的理论,粉饰它们,但是它们就好像砖块一样,你可以继续磨光它们,但是它们永远没有办法变成一面镜子。但是我说:
或许砖块可以变成一面镜子,但是头脑永远没有办法变成一面反映真相的镜子。头脑是一个破坏者,它一进入,每一件事就都被遮蔽了。
请不要成为一个哲学家,不要成为任何系统的耽溺者。要把一个酒鬼带回来是容易的,要把一个沉溺于药物的人带回来是容易的,但是要把一个沉溺于系统的人带回来是困难的。对于酒鬼和沉溺于药物的人有一些机构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对于沉溺于系统的人并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帮助他们,不可能有,因为每当有一个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