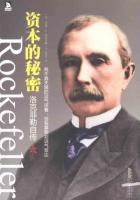你必须当面跟孙治谈这件事,弄清楚她的意图和愿望。假如他们是正常恋爱关系,假如他们早就有见面,甚至已发生过性关系──看到那些赤裸裸的对话,你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这件事就不必过多干涉。翟同军让你把你的处女身份保持到结婚前夜──可惜最终并未交给他──那是从前的事情,子淇这一代可不会那样有克制,也无法要求他们那样,也没这个必要。但你心里难受,觉得子淇跟女孩子好,你应该最早知道,可现在不是这样。原先你认为这方面子淇啥也不懂,对女孩子没兴趣,有性冷淡倾向,不会出去谈情说爱,情愿天天待在家里陪你说话给你炒蛋炒饭,可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一刻,荀琳和子淇共进午餐,吃蛋炒饭喝菠菜汤。两个人已经讲好,晚上到得月楼吃松鼠桂鱼。子淇喜欢喝干红,两个人喝一瓶,喝一样多,能喝好久好久。荀琳跟子淇讲下午她仍去采访李宗祥,结束后发短信来。并告诉子淇坐八十五路车,得月楼门口就有一个站头不用转车。
这时候,李宗祥跟王修也在共进午餐。李宗祥出去买了两块叉烧肉、二两花生米,家里有黄瓜和水芹,就简简单单凉拌一个黄瓜,水里滚一下水芹也凉拌,又煮了两碗阳春面,把香葱切得细碎,把鸡蛋丝切得细长,均匀撒在面碗里。
李宗祥的灶具全在楼下楼梯旁的门厅里。而这个门厅,就是他和小马合用的厨房。以前是三户人家合用,朱老师家尚未搬走时,也在这里煮饭烧菜。朱老师家住东厢房,下雨天要打着伞穿过天井来这里下厨很不方便。这门厅很小,十平米不到,也没窗户,也不通风,早先烧煤炉有蜂窝煤的煤气味,现在烧燃气灶有液化气的煤气味。小马的房间门常常是开着的,烧东西的时候就叫他把门关上,免得煤气味更多地跑到他房间里。小马还在弯铜丝,今天弯了一个牛头和一个自行车。此刻手里在弯什么,看半天没看出来。李宗祥提醒小马要做饭了,小马说不饿,早饭吃得晚。
李宗祥现在喝的丹阳封缸酒是王修送的。那是一个八斤装的酒瓮,连瓮带酒十来斤重呢,王修的大儿子吩咐小孙子驾别克车给李宗祥送来,不让王修自己拿,怕老爷子闪了腰摔了腿出事。两个老人喝酒吃面,讲讲闲话,说说新闻,不亦乐乎。那张画葛正才的画像还在桌上,王修又讲了一句画得像,李宗祥仍不搭这个话头。
喝了酒吃了面两个老人都坐在窗口的藤椅里闭目养神,中午都要打一会儿瞌睡,不然下午下棋没精神。太阳已经出来了,太阳光从窗口照进来,照到桌上的茶壶、茶盅及棋盘;也照到那张画像上,照到半个脸。两个老人都坐在光线稍暗的地方,像泥塑般一动不动。
身体不动的时候,大脑皮层就活跃起来,遗忘最久的事情,最容易想起来。王修刚合上眼睑,就看到葛小妹的脸;不是桌上的头像,而是法场上的面孔。假如你精神状态不错,你闭目凝神时,就会看到你想看到的那样东西,有时甚至能看出它的颜色,这种现象科学家把它叫做遗觉像。这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知道了看得到,有的人知道了看不到。
王修小时候就晓得看遗觉像,想看到谁就能看到谁,不管这个人在不在跟前。印象中葛小妹是眼睛看着你给砍头的。他脸上的最后一个表情,是看着你的面孔朝你微笑,显然已认出了你。半个月前他去过你家,知道你是丁山桥王绅士家的小孩,他跟你父亲在客厅里下棋时,你跪在骨牌凳上看他们下。
你父亲埋怨你叔叔带你去法场看杀头,因为你一连好几个夜晚做杀头的梦把自己吓得灵魂出窍醒来后就睡不着。起初你父母都不知道这件事,不晓得你为何半夜做噩梦突然尖叫起来,把全家人都吵醒。后来就发烧,整日躺在床上,白天也说胡话。请了医生来看,吃了医生开的药,可病情并无好转。
你母亲跟山东佬的老婆讲你的病,山东佬是你家的长工,他老婆常来你家陪你母亲说话。她叫你母亲替你喊魂,太阳落山后开始喊。把竹梯搭在墙头上,站在梯子上喊。于是你母亲把一个青花海碗搁在墙头上,把一张黄裱纸覆在碗口上,一面朝黄裱纸洒清水,一面朝着暮色中的桂子山喊你的乳名,喊你的魂灵。那种拖声拖调的古怪,那种忽徐忽疾的诡异,全是山东佬老婆教你母亲的。可一连喊了三天,一连三天黄裱纸都有水往碗里滴,你却仍旧额头发烫高烧不退。
于是山东佬老婆亲自为你站筷子,不信治不好这个病。她在油灯下挑三根红木筷子,一根根检查,不能有疤痕,不能有长短。她面对卧床的你,两只手捏住这三根木筷,将筷头蘸了清水,往青花海碗里站。一面喊亡故者的名字,一面蘸水站。被喊到的亡故者有你的寿终正寝的祖父、得痨病去世的姑姑、不慎跌入池塘被淹死的弟弟,以及生前喜欢抱你逗你的聋子,以及指腹为婚给你做媳妇却不幸夭折的张家女孩,可筷子都往两边倒,不是朝左倒,就是朝右倒,怎么也站不住。
你二婶闻讯赶来,跟你母亲咬耳朵,接着你母亲跟山东佬老婆咬耳朵。于是下一轮的站筷子,就听到这个女人开始叫葛小妹的名字,一连叫了三声,筷子站住了。接着就跟葛小妹说话,央求他不要逗弄王先生家的小孩了,并许诺给他钱,马上就给。碗和筷一拿走,母亲就在大门外烧纸钱烧锡箔,给葛小妹烧,刻不容缓。奇怪的是,当晚你额头的烧就慢慢退了,到天亮就退净了,到白天就能下床了。山东佬老婆见你父亲不理解也莫明其妙:“退了烧怎么奇怪呵?不退烧才奇怪呢!”自此以后,你想到葛小妹的事情,眼睛里看到葛小妹的血脖子,就不再做噩梦了。
第二次看到杀头是在金华。当时你是六十三师的,已经当了副连长。背刀的那个人从你左边闪过来,扔下枪抽刀举刀手起刀落,就砍了鬼子的头。你已经看到那个鬼子朝你瞄准,可你的枪已没了子弹。本能中你意识到应该往左闪,让你的心脏躲过这颗子弹。结果你看到那个鬼子被大刀砍断脖颈,血脖子倏地涌出血柱来。鬼子的头骷髅落地后,才扣动手里的枪,子弹打断了你右手的大拇指。战斗并未结束,你是捡起鬼子打你的那把长枪,拿刺刀捅了另一个鬼子之后,才发现战场上已看不到一个活着的鬼子。这时你的拇指根还在流血,你扔下手里的枪,从衬衫上撕下一块布条,把受伤的手咬牙扎紧。一面扎一面奇怪,按理子弹不会打到大拇指,打到心脏也不会打到大拇指,可事情偏偏就这样发生。
你在战场上寻找那个背刀的人。起初你是在走动着的或站立着的士兵中找,结果走了好几圈没找到,于是你就在尸体中寻找。这山沟里到处是尸体,有完整的有残缺的,有鬼子的有我们的,有我们六十三师的也有其他师的。你之前之后经历过的大小战斗,就数金华那次最惨烈。你发现我们的尸体多,鬼子的尸体少,大致二比一。单单六十三师,就死了一百二十六名溧阳人,就你和史之光少数几个还活着。
后来你才知道,背刀的那个人也是溧阳人,以前是大刀会的,后来入了五十八师,姓许叫许福民,是溧阳深溪岕人。许福民躺在一个鬼子身上,脑袋被打了五个洞。他的那把大刀,就掉在他跟前的草丛里。刀把上的红穗子,已经被血浆粘得僵硬。你将那把刀拾起来,擦净刀上的血,洗净穗子上的血,把它插在背上,从金华到长沙,从衡阳到桂林,一直带着它。胜利后你回家探亲,便将那把刀送到深溪岕去,交到许福民妹妹手里。接着你给许福民的老母亲下跪磕头,一连磕三个头,你喊她娘,给他做寄子,留给她一笔钱。而遗憾的是,陵谷沧桑,世事多变,你能够再次去深溪岕的时候,已过了三十五个年头,许福民的老母亲已过世二十三年。
六十三师从溧阳到金华是分批走的。最后都走了,再也没回来。你走的时候,还有一个营在戴埠千华寺,并打过戴埠日军一次。金华战役之后,日本人还在溧阳找六十三师呢,以为还没走。日本人到丁山桥去过两次。第一次家里人是全都逃走的。你的瞎眼奶奶是山东佬背在背上逃到后山龙王庙的。你弟弟王平牵了一头母牛,那牛走得慢,一路上给王平拿鞭子打。跑到龙王庙跟前,把它拴到树上,不料牛屁股狠劲一歪,把王平撞了个狗趴。第二次日本人是悄悄进村的。保长敲门时,全家人还都没起床呢。瞎眼奶奶是母亲搀着她走到村口的。当时瞎眼奶奶眼睛没全瞎,右眼还看得见光亮。她看到王平被日本人拉走,就上前抱住一个日本军官的长统皮靴,嘴里直喊“洋先生,洋先生”,头点地给日本人磕头,求他放了你弟弟。日本人架了两挺机枪对着全村的男女老少,他们从人群中拉出三个人,老年人、中年人、小孩子各拉一个,小孩子就拉的是王平。他们把王平拉到房子背后,叫王平讲村上有没有六十三师的人,有没有新四军的人,有没有大刀会的人。日本人拿糖果哄他,拿军刀吓他,可王平始终摇头,一句话不说,好像给吓傻了。村里人谁都知道你是六十三师的,你姑夫是新四军的,你堂伯是大刀会的,却没人愿意给鬼子讲。大概鬼子没掌握具体情况,只是吓唬村民一下,见村民全傻乎乎的问不出名堂,就撤了机枪去后村了。这是胜利后王平给你讲的。
屋里发出藤椅的吱扭声音,王修知道李宗祥醒了,知道他在铺棋布摆棋子。李宗祥下棋稳扎稳打不慌不忙,所以赢得多输得少。王修喜欢出奇制胜出险招,有时候赢得快,有时候输得惨。这两位同乡老人都是高个子,但王修腰板挺得直,李宗祥略有佝偻,仿佛一个高许多,一个矮许多。王修留胡子精神矍铄,李宗祥却总是把下巴刮得光光的脸色苍白。王修比李宗祥大九岁呢,但看上去比李宗祥岁数小。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王修说得多,李宗祥说得少。王修使过好几个国家的长枪短枪,李宗祥做过二十五年钳工,所以王修讲枪械结构时,两个人都饶有兴致。王修讲不清楚的某个部件,李宗祥就随手拿铅笔画出来,于是两个人就撂下棋盘上的残局,反复修改这个部件图,直到彼此都无异议才作罢。
太阳还照在桌子上,照着半个棋盘。李宗祥给两个茶盅都斟了茶,王修执黑棋先走。“你是毛尖人,应该知道葛小妹的事。”说这话时,王修仿佛漫不经心,眼睛仍看着刚开局的棋盘。
“当然知道。”李宗祥一面落棋子一面说。
“为啥不给记者讲?”
“没给谁讲过。”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的那个受刑人,正是家父。”
“原来如此。”
“当年领我来大窑路的那个人,正是潘尧。”
“明白了。”
两个老人一面下棋一面讲这件事。
日本人打上海那年,葛正才母亲得病去世。按理讲,那个湖北佬潘尧和他老婆拿了葛正才分给他们的钱,应该往湖北湖南跑,跑得越远越好,可他们却去了邻省的杭州,做起了药材生意,还年年来溧阳一趟两趟,还跟溧阳的大刀会有联系。事过境迁,抓葛正才的那个朱县长早跑了,砍葛正才脑袋的那个刽子手也身首分离早死了,就连出主意给葛正才穿肩胛骨的那个刘科长也没了脑袋送了命,而葛正才在麻园的那伙人如鸟兽散早就散伙了;其实有的并没走远,一转身入了另一伙大刀会,有的警察局也知道,但费事抓一个小喽啰没啥意思。喝酒的时候,有人讲某某某那儿的某某某以前跟过葛小妹,若真的把那人抓起来,讲这话的就不肯给你作证,喝酒讲的话还当真,多没意思,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连那个抓葛正才的警察队长,隔了五六年,就跟潘尧坐一张桌子喝酒,心里明白这个药材商人就是葛正才的拜把子兄弟,竟然也装糊涂只当他是卖药材的一起碰杯喝酒。朋友叫你过来吃饭,你把朋友的朋友抓起来,以后谁还跟你做朋友?再说大刀会的人不好惹,结了仇就跟你没完没了,非搞你个家破人亡不可。再说谁跟葛正才有关系就抓谁,就要抓你这个警察队长,因为你娶了葛正才的女人当老婆。这种事情糊涂一点好,不然送了命也不知道咋死的。再说眼下日本人快来了,县政府跑乡下去了,警察局也散伙了,你这个警察队长没地方领薪水,天天待在家里上午喝茶皮包水下午泡澡水包皮坐吃山空。你知道潘尧是去泥面岗给葛正才的老母送葬,给葛正才烧纸,领走了葛正才的小孩,可你有心思管这件事么?当年葛正才破城放监是天大的事情,连省长也过问,现如今只是茶余饭后的闲讲碎谈,抓潘尧有啥意思?按理潘尧会把你干掉,因为是你把葛正才从床底下抓到的。有人讲报信的那个磨豆腐的歌岐佬是潘尧打死的,出事前潘尧来溧阳收药材,在溧阳待了好几天呢。可潘尧为何对你手下留情放你一马,让你活到溧阳解放,让共产党枪毙你,想了好多年仍想不明白。公审时你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开枪打你的那个周麻子是周城人你认识,周麻子先是跟葛正才,后是跟新四军,现在是人民警察,代表溧阳人民处决你,用是你用惯的那种驳壳枪……
李宗祥朝棋布上丢了一个卧槽马,顺手拿茶盅喝了一口茶,接着往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