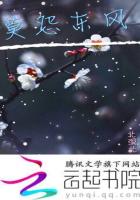中午,知了挣破嗓子叫,响亮的大合唱贯满耳朵。
到哪里听不到这种声音?去南极吗?去北极吗?去繁华的大城市吗?
城市车辆如梭,高楼林立。爸爸的家在城市就好了,我和天星姐姐也就是城市的小朋友了。星期日逛逛公园,转转书店,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踏着笔直的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
我们家住在城市就好了。
炙热的太阳光散发在大地上,蒸发掉地上的水分,烤得大地一片焦黄,水蒸气漫游在院子里,像夜晚的磷火。母鸡不敢赤脚踏在地面上,摊开翅膀躲在树荫底下,懒散地半闭着眼睛,对烦躁的知了喊叫充耳不闻。
一丝风也没有,让人心烦意乱。
我坐在窗前望着庭院外的树梢,那里是合唱精灵们的天堂。爷爷奶奶前年撒手人寰,留下了这片枝繁叶茂的树林。
爸爸说爷爷年年种树,从不舍得杀一棵树,高的矮的粗的细的笔挺挺地站满密集的林地。爸爸在林地西端空地上,栽满三十棵梧桐树苗。当年冬天把这些树苗从根部砍掉,在树根部位培满土,到第二年春天,每堆土上冒出几棵毛茸茸的绿芽,爸爸只留下长得胖壮的嫩芽,其余全部拔掉。到了夏天,三十棵笔挺的梧桐树齐刷刷地站在林地那儿,好像站岗放哨的士兵精神抖擞。让生产队里饲养员家建国折断一棵,剩下二十九棵梧桐树三年长成梁檩粗。爸爸用这些木料盖了四间房子。还剩下一根,至今躺在南院墙根闲着。
树林最南端是一个小水湾。下雨天,水从西边上游沟里缓缓流进小湾里,水流多了,再从湾里顺着下游沟里流进南河。不知何年月修建了一座石头流水坡,陡峭的水坡冲向深沟,哗哗瀑布直冲而下,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震耳欲聋的流水声。
树林里总是聚满了嬉闹的孩子和洗衣服的妇女。
小湾北岸一棵碗口粗的柳树,横倒在水面上,孩子把它当成独木桥,鸭子把它当成栖息地。孩子坐在树干上玩耍,把小脚丫伸进水里,撩起点点水花。大人发现了,就大呼小叫让孩子赶快下来。
“老天爷,还能在哪儿玩?小心!”
孩子们假装听不见,嘻嘻笑。大人只好一溜小跑回村叫来孩子的家长,孩子们老远听到骂声,早跑得无影无踪。
树林中央那棵最高的白杨树上住着一窝喜鹊,羽毛光光滑滑黑不溜秋,叫起来“喳!喳!喳!”好听极了。多数清晨我是被它们叫醒的。心心念念总想着这窝喜鹊到底有多少只呢?我试了几次想爬到树上数数,只因为树高又粗,终究没有成功。
村里人通常称呼我和姐是‘老学孢子’家的孩子。上完一年级,我才略微懂得一些这个称呼的大体意思。
爷爷在旧社会教私塾,爸爸如今在学校教书,被人称作‘老学孢子’。
这时,大门响动,我透过窗口向大门的方向望去,东屋五保户王奶奶来了,她一眼就发现我趴在窗台上。
“嗯。没睡晌午觉吗?粒儿。”她走在院子里问。语音不清,满嘴漏风,从她的嘴里已经找不出一颗牙齿。
我高兴地叫了一声“王奶奶”。总算有人和我玩了。除了知了的声音,没有别的声音,静得让人寂寞烦乱。也不管她唠叨些鸡毛蒜皮男娼女盗野狗不知羞耻地缠在一起的事情了。天星姐姐到同学爱丽家写作业去了,爸爸在东间午休。
王奶奶晃晃悠悠进了屋,慢腾腾的总比你预想的时间慢。大人总说旧社会如何如何,大概王奶奶就是个例子,好端端的一双活泼小脚硬缠断骨头和脚丫,残害人体,走路掌握不好平衡。
她进了屋随便坐在一个方凳上,习惯性地嗯了一声。
“你姐呢?粒儿。”她问。接着咳嗽一声,后面又加上一个嗯字,“嗯,这几天天气好,趁着暑假,该把被褥缝起来了,进了七月就不好缝了。”
“奶奶,为什么?人家不让缝了吗?”我不解地问。
“真是小孩子,单月不缝被的。嗯。”
我不屑地瞥瞥嘴巴,又是乌七八糟的迷信,天天破除迷信就是没有把这只老脑袋里的迷信破除掉。我爸就不信。
王奶奶是村里的五保户,哪“五保”我说不清楚。她住在我们家东边,两间麦草屋孤零零地座落在土坡中间,房子与她本人一样寒酸。屋子周围种满了蔬菜,院墙把蔬菜也围起来。院墙是用玉米秸圈成的,大门也是用玉米秸绑的,真像大户人家的鸡舍。不过不能说出来,爸爸听到会批评的,说是不尊重老人,不懂礼貌,嫌贫爱富。
王奶奶七十多岁,身边没有孩子,有一位干女儿在陕西,许多年没有回来过。她每天穿着一身黑色大襟褂子,黑色裤子,脚脖子上用黑色长布条带缠着,小脚穿在一双尖头布鞋里,那鞋连我的脚都装不下,脑袋后面挽着发髻,用黑网网住,总是几天梳理一次头发。
打我记事起她就是这身打扮,从她身上总是体味到一种迂腐的旧社会气息。遇到她问:“王奶奶,今天梳头了吗?”她不紧不慢地说,“前天才梳的呢。”
树林里有一棵圆菜板粗的树干,裸露在地表处的黑树干到了六月天,长出了一朵朵灰白色的小蘑菇,拥挤在树墩上,都说有毒不能吃,王奶奶不信,她采回家炖着吃。每次她采了蘑菇用草篮提回家,我望着她佝偻的身影,就替她提心吊胆。第二天就特别注意瞅瞅她家门口,看见她悠闲自在地出现在她家院子里时,我就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王奶奶每年都帮我们家缝被褥、棉衣。爸爸帮她干些力气活,提水、砍柴,还有非爸爸莫属的活,那就是给她念陕西干女儿的来信,念完之后还要给她的干女儿回信。我放学以后,远远望见她在我们家大门口踮着小脚徘徊的时候,就知道她干女儿来信了。爸爸会不做饭先给她念信,而且有的语句还要加以解释。
王奶奶坐了一会,不见天星姐姐回来就走了。我从简陋的旧书架上拿出一本图画书胡乱翻着看,看看这页,翻翻那页,没有记住一点儿内容。
妈妈要是活着就好了,妈妈会给我梳两条顺溜溜的小辫子,给我缝一个漂亮的六瓣花布毽子,比爱丽的还好看。王奶奶说妈妈长得很漂亮,身材苗条,讲着普通话。每到过年,爸爸帮人写对联,妈妈研墨,村里好多人都羡慕。
妈妈被洪水冲走了,从我记事起有人就这样对我说。我常想有妈妈就好了,放学回家,有妈妈抱抱。
面前模模糊糊是妈妈美丽的身影,妈妈站在大山脚下,我高兴地大声喊:“妈妈——”飞快地跑过去,无论怎样努力,怎样撒开大步,总不能近前,我拼命地喊叫,拼命地跑……忽然,一块巨石挡住去路,用尽全身力气,也推不动,只好放弃这条道。而别处乱草丛生,没路可走。我焦急地望着远方,一股浑浊的洪水冲着妈妈蜂拥而来,我全然不顾荆棘满地,奋力冲向妈妈的方向……
“粒儿……”
我睁开眼睛,又是一个梦。天星姐姐站在床前,见我醒了,转过身去把书包放在写字台上,拿起梳子梳理了一下黑黑的短发。
“刚才在门口王奶奶遇到我说,她马上过来帮咱家缝被子。”天星姐姐说着,从抽屉里找针线、顶针,还有妈妈的粉线盒。
姐姐九岁,比我大一岁,个子比我高出一头。她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年年班级第一名,是班长,是文艺委员,而我什么也不是。
“爸爸还午睡吗?粒儿。”
“快两点了,也好醒了。”
这时,东间响起动静。不一会儿,爸爸走过来,手里摇着一把大叶子蒲扇,看着我俩说:“我说孩子,今天还是这么炎热,立秋后这伏更闷热,我去菜地,顺便把兔子草捎些回来,你俩个就不要去了,要不过了这个夏天,你俩就变成两只黑毛兔子了。”
“爸,下午王奶奶帮咱家缝被子,你帮我把吊在墙上的草席拿下来?”天星姐姐指着北墙上吊着的草席说。
爸爸放下手中的蒲扇,动手把挂在墙上的高粱秸皮编织的草席拿下来。
“我说,不用爸爸加入你们的妇救会?”
“得了吧,爸爸,王奶奶说你在跟前手忙脚乱的样子就碍事,没有那么多长针让你的笨手折断。”姐姐仰着脸接过草席,放在地上,“我们在院子树荫底下缝,外面凉快。”
爸爸提着草席放在院内树荫底下。王奶奶从大门口走了进来。
“嗯。我正在琢磨呢,在什么地方缝合适呢。”王奶奶看着地上的草席说。
“我说大婶。不算我一个了?我可是壮劳力。”爸爸逗趣地说。此时王奶奶皱纹的脸真像一朵开放的金丝菊,细纹匀称地爬在脸上,满脸堆笑着。
“忙你的去吧,李老师,两个孩子帮我就行了。”王奶奶说。把掖下夹着的眼镜拿在手里,弯腰用一只手拉了拉地上的草席。
爸爸从院墙根抗起一把锄头,锄头柄上没有忘记挂上一只草篮,“那我走了。”慢腾腾地走出院子。
爸爸的名字李宇祥,村里人习惯叫他“李老师”。
爸爸走了,我们三人忙开了。王奶奶指挥着我拿干净的抹布抹草席上的灰尘,让姐姐拿出被套被表,她自己又亲自铺展一下草席,俨然像正在指挥打仗的将军,一会看看这边,一会动动那边,很认真,很严肃。看着她那专注的样子,我从不敢捣乱,一切行动听她指挥。
一切整理就序,王奶奶戴上那只断了一根腿的老花眼镜,从眼镜框上面瞅着平展的被面,自言自语道:“嗯,下手吧。”
只见她拿起针线,手指头蘸着唾沫捻着线头,弓着腰,眯着眼,把针伸向很远,嘴里嘟囔着,老了,眼花了,看不清了,针都纫不上了。看不清手还离眼睛那么远。我接过针纫上线给她。
“不如八岁的孩子了,老了。嗯。”
她打量着被表的长短,用剪刀剪断线,线尾打上一个小结,打结的时候没忘记指尖伸进嘴里蘸上一点唾沫。
王奶奶肚子里的故事永远讲不完,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瞒不过她的耳朵,一天学没上,说起话来文绉绉的,真像一本活村史。
纫完被边,有了心思,王奶奶又讲开了“古”,夹杂着早日的民俗村风古、今的新闻轶事,谁家祖宗八代干什么。
“嗯。你们家啊,”王奶奶扶了扶眼镜框,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说,“嗯。早些时候,在村里算是殷实人家,你们家的花园归了公,你爷爷硬在这片沼泽地里栽上树,树林又起来了,如今雨水小了,树林成了平地。“四清”那阵子,由于你爷爷诚恳老实,人缘又好,没被清着。你爷爷呀,不像别的教书先生。他富人、穷人的孩子都教,有时还贴上一些嚼食,咱们村里出去那么多识文解字的,都是你爷爷教出去的。还是解放了好啊,穷人也能念书,嗯。”
针上的线刚好缝到被头,王奶奶用剪刀剪断,把针递到我手里,让我纫上线,她接过去,把指尖伸进嘴里蘸了唾沫打了结,低头缝另一行。天星姐姐在一边也像个大人学着缝。
“嗯。不是你爷爷人缘好,也打成反革命地主四类分子里通国外的大特务了。你们家的人厚道,只可惜你妈妈走了,多好的人家啊……”
王奶奶摘下老花镜,用衣袖擦擦眼镜片,拭拭眼睛,把眼镜戴上,捏了一下鼻子又继续干针线活。
她总是把芝麻大的烂谷子说成镰刀长的谷穗,添枝加叶。从她嘴里说出的话就像发过的馒头膨胀。其实我爷爷的成份没有她说的那么严重。
“你爷爷是能人啊,懂占卜。周围十里八乡,谁家儿子结婚女儿出嫁,谁家盖屋上梁,孩子拜干爹干娘,甚至垒个猪圈搭个鸡窝他都能给查出好日子。你奶奶也了不起,别看她个头小,能着呢,不信,王家媳妇硬说自己怀上的女娃,村里的冯神仙算的,你奶奶说是男娃。你奶奶给婆娘接生孩子,孩子没出生就知道是男娃女娃,看十个九个准。”
看来她对爷爷奶奶崇拜得五体投地。
“还是不全准。”我坐在缝好了的这头,遗憾地说。
“嗯,不错了。村里人非常敬重你爷爷奶奶,谁家两口子吵架,谁家闹分家,谁家出了大事都把你爷爷请去。”王奶奶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的话不满,“那一年,你俩还小,唉,你奶奶春天去了,你爷爷一下子蔫了,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这么倒下了,秋天也跟着走了,一前一后,不出一年。唉,可怜你爸爸了,又当爹又当娘的。”
王奶奶又摘下眼镜,泪水打湿了镜片,人上了年纪容易动感情,无论什么事就好掉下几滴眼泪。
“什么好日子不好日子,我说那是迷信。”我说,我从来不考虑她的感受,“医生比我奶奶看的准,大医院有看病的机器,B超能照出人得了什么病,是男娃女娃更能照出来。”
“B超是哪里人?”王奶奶抬起头,从眼镜框上面瞅着我认真地问。
“哈哈哈……”我和天星姐姐同时笑起来。“奶奶!是看病的机器。”天星姐姐大声说。
“我还当是什么人呢,比你奶奶还厉害。”王奶奶扶了扶眼镜框说,也不笑,又低头缝。
缝完了一床被,王奶奶让天星姐姐和我一同把草席往东拖了拖,阴凉往东走了一大块。草席完全在阴凉地上,又开始缝第二床。
“嗯,你爸爸不给人家查日子,说是迷信。才不呢,真的有好日子呢,古书上都写着,你爷爷有本大书,你爸爸把它放在你爷爷的身旁埋在坟墓里了。你爸说‘这本书伴了你一生,下辈子也让它伴随你吧。’村里人求你爸查个好日子,你爸爸说五一、十一、元旦都是好日子。现在的年轻人多数用这些日子结婚。”
王奶奶停下手中的活,把针线放在头发上擦了几下又开始忙活。有时候切菜时刀不快了,她把刀放在缸沿上镗几下,爸爸用磨刀石磨刀。不知道爸爸用什么东西磨针,爸爸肯定不用头。
“你俩个长大了要好好孝顺爸爸,他不容易呐,天底下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爸爸了,想想看,大的刚蹒跚走路,小的才满月……你妈妈就走了,日子怎么过来的?……”王奶奶声音哽咽,捏捏鼻子,又把眼镜摘下来擦擦眼睛。
你不打断她的话,她会讲到天黑不觉累。她从早到晚也没有多少事做,没有土地种,闲得慌。她捉住你就说啊说啊,不管你感兴趣不感兴趣,我爷爷奶奶在人间的事情,我爸爸飘洋过海留过洋,不是我爷爷的一封封家书追回来就打成反革命等等,她不知讲过多少遍,我爸爸光屁股的事她还想着,可她就是不提我妈妈,隐隐约约感觉到村里人都忌讳提起我妈妈。爸爸说妈妈在一个暴雨天被洪水冲走了。
好奇与新鲜过后,我不愿再听王奶奶唠叨,一行一行地来回纫针,单调无聊的没有一点儿意思。我起身走到屋里,坐在写字台前,拿起蜡笔,摊开纸画画。
在知了的大合唱里,在王奶奶絮絮叨叨里,白纸上跃然显出一只美丽的大公鸡,昂着头,挺着胸,向着东方橘红色的太阳,仿佛这个世界只有它自己。
太阳偏西,阳光地和阴凉地的温度没有多大差别的时候,我又坐在草席上,第二床被子缝制接近尾声。王奶奶剪断最后一根线头,把针扎进线球,摘下老花眼镜,小心翼翼地放在褪了色的黑色眼镜盒里,拍拍身上的灰尘,站了起来。
“好了,今天的活就到这里。太阳没了,到做晚饭时间了。”王奶奶说着,又拍打身上的灰尘,拍打出来的不是刚粘上的,是早就在黑大襟褂子上焗着的。王奶奶不经常洗澡,衣服更不经常洗。
姐姐卷起草席,接过我递上前的线绳,捆牢绑紧。
爸爸抗着锄头推门进来,锄头柄上挂着盛满青草的草篮。
“大婶,一起吃晚饭吧。”爸爸放下草篮,把锄头倚在院墙根,回过头来看着奶奶爽快地说。
王奶奶眯着小眼睛,手里拿着眼镜盒,小脚向前挪了几步说:“不了,李老师,家里有现成的,一热就是。”
爸爸笑吟吟地跟在奶奶后面,送她走出大门口,又客气地说了一句,“大婶,走好。”
爸爸目送王奶奶一会儿,转身回院子关好大门。
爸爸看见床上新缝好的棉被,脸色和悦地说:“又难为她了,这么大年纪。”然后,把两床被子放在衣柜里。
“我说,孩子,今晚吃什么饭呢?玉米面饼子?还是地瓜面饼子?”爸爸问。他轻快地走进厨房。
我坐在客厅木椅上,把腿搭在木椅扶手上,没劲地说:“什么饼子都可以,反正又不是小麦面饼子。”
“这个愿望我看不久就要实现了,孩子们。不只我们家这个样子,全国人民都是这个样子。孩子,咱们这个国家还比较贫穷,今年吃玉米面饼子,我看再住上几年,1979年、1980年或者再摊上几年就能吃上小麦面饼子了。我们中国发展很快,专家研究多产粮食的化肥,研究高产粮种,慢慢地就人人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小麦面饼子了。”从厨房里传来爸爸的声音。
爸爸一旦打开话匣子就是通篇大论,要不是忙着往锅里贴玉米面饼子,他能绘声绘色地从夏朝讲到清朝,从蒋介石讲到毛泽东,从一点小事讲到民族精神。他在学校里教语文和历史。
他不在我和姐姐面前提起妈妈,当我和天星姐姐围在他身边让他告诉我们妈妈长得什么模样的时候,他总是说别的把话题岔开,眼睛里流露出忧郁。爸爸百般疼爱我和天星姐,他不让我们俩因失去妈妈而心灵受到伤害,不让这个家因失去妈妈而失去笑声,而爸爸让我们笑声不断,他用爸爸和妈妈双重爱,呵护着我们。
我和天星姐与小朋友玩耍,玩恼了爸爸从不介意,他每次总是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微笑着说:“羞!大姑娘了还掉眼泪,把泪水擦掉,女儿有泪不轻弹呢。”
就在刚放暑假的第一天下午,我和天星姐还有建国在林子里玩跳绳游戏,建国跳不过我和天星姐,每次不是天星姐姐第一,就是我第一,建国恼羞成怒,撒泼道:“你俩是野种,我妈说你俩是私生子,不是你爸爸生的,你俩是野种!你妈跟着野男人跑了,野种!……”
此时,爸爸下班回来,亲眼目睹这个场面,脸一下子拉长了,铁青的脸非常吓人,嘴唇哆嗦着,一把抓住建国的胳膊,像拖小鸡似的把建国擒到他妈面前。
建国的妈妈知道缘由慌忙道歉。几天后又送过来一把韭菜,让爸爸尝尝她家自己菜园里长的,比到集市上买的好吃。
村里人对我们家还是和善友好的,不因为我们家不吃生产队里分的粮食而孤立我们,我们家祖祖代代住在这个小村。我更愿意爸爸把房子卖掉搬到城里去住,天天吃油条,头发扎着红丝带,上学坐公交车,过舒服的生活。
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只想着享乐,过上安逸的生活就得到城市去,不知道爸爸这点微薄的工资养活三张嘴巴,把细粮换成粗粮,还有三个身体穿衣,已经力不从心。在我大一点的时候,我懂得了爸爸的艰辛,不再提到城里,但心却一直向往着。
爸爸做好晚饭,把玉米面饼子端到吃饭和待客并用的木质茶几上。
“我说孩子,洗洗手吃饭喽,爸爸贴的玉米面饼子焦黄酥软,吃起来可香了,可不准多吃,每人一个。”爸爸高声说。
我和天星姐洗洗手,坐在木椅上,玉米面饼子热气腾腾,玉米香味散满房间,还好,还有一盘炖扁豆。
“再加点肉就好了。”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