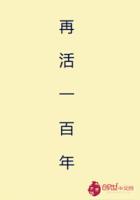云南乡间官道。
红日当空,秋风送爽。
乔仲、方永甫、乔禄三人布履微服,信步而行,说说笑笑来至路边一村落。
村街上,一花甲老者自村内缓缓走近。
乔禄上前躬身施礼道:“请问老丈,此间可有酒肆、茶坊?我等是外地来此经商的,还请老丈指点一、二。”
老者亲切道:“三位客官,敝村周近并无客店以供茶、食。往南再行十里有一东里镇,镇上有两家酒楼,若步行赶去少说也须半个多时辰。哎!依我看三位客官不如随小老儿去舍下一聚,小老儿也可略尽地主之谊,不过只是粗茶淡饭。”
乔仲上前一步拱手道:“不敢、不敢!多谢老丈美意,只是萍水相逢怎好打扰?”
老者:“哎!这位客官说哪里话。出门在外的有谁自己背着锅灶、柴米的?若看不起小老儿,三位请自便;若不嫌弃,就请三位去舍下用一便餐,不知三位尊意如何?”老者边说边抬头看了看天,又道:“再说,天色近午,正是用餐之时,若此时让客官走了,岂是壮家人待客之道?”
乔仲躬身施礼道:“如此在下等恭敬不如从命,就叨扰老丈一餐,容后重谢。”
四人说说笑笑一路进村。
小村院落。
老者引乔仲等三人进院。
客厅。众人就坐,老者敬茶毕,趋至门口呼道:“贤媳快来。”
一年约两旬的年轻女子款款走来,亲切地说道:“阿爹呼唤,不知有何事吩咐?”
老者道:“儿呀,方才三位客官错过了路头,前不逢村、后不着店,阿爹今日做东招呼客官一餐便饭,贤媳速去打理。”
年轻女子抬头往客厅里扫了一眼,遂低眉顺眼地应道:“阿爹少待,媳妇这就去。”
小院客厅。
老者与乔仲三人叙话、品茶。
小院北屋。
烟囱炊烟袅袅。
小院灶间。
年轻女子手脚麻利的切菜、淘米……
须臾间,饭菜已好。
年轻女子在灶间门口招呼一声:“阿爹阿爹。”
客厅里。
老者:“三位客官稍侯,饭菜已好,小老儿去去就来。”
老者步出客厅,乔仲等三人的眼神随老者移向北屋。
北屋灶间。
年轻女子用托盘将饭菜、杯筷端进里间。片刻转身出来,又用托盘将饭菜、杯筷端至客厅,老者随后手提一壶酒进来。
年轻女子将饭菜、杯筷摆放毕,敛身一福,低头退出。
主、客寒暄一番后,老者在主席坐定,乔仲上首、方永甫下首、乔禄打横里坐下。
四人边喝、边吃、边聊。
乔仲:“敢问老丈贵姓?府上尚有何宝眷?”
老者:“不敢当。小老儿免贵姓韦,舍下只有小老儿和儿子、儿媳,今日清晨小儿韦春套车进城粜米去了,日落时分方能回来。”
乔仲若有所思的“啊”了一声。
老者:“怎么?客官,有什么不妥当处?”
乔仲:“岂敢!岂敢!老丈请不要误会。”
边说话,便向北屋瞄去。
老者微微一愣,遂点了点头。
画面推出:北屋灶间,年轻女子端饭菜、杯筷去里间。
画面拉回:老者微微一笑:“客官莫不是认为舍下尚有长上在堂?”
乔仲笑着点点头:“老丈,难道在下走眼了吗?”
老者哈哈一笑:“还别说,客官真看走眼了。实话对客官们说吧,去岁此时我们南丹县遭了大灾,五个多月没下一滴雨,十多万亩地颗粒不收,县衙官仓的钱粮又不翼而飞,饥民打跑了知县,闹到了曲源府。正在知府杨大人焦头烂额,欲全家自戗于曲源城门楼下时,朝廷钦点礼部侍郎乔大人来曲源放粮赈灾、安抚百姓。这乔大人不光带来了赈灾的粮谷和朝廷对曲源六县黎民的关怀,还带来了春播的种子,俺曲源遭灾的百姓才有了今秋的好收成。要不是乔大人,曲源六县的百姓还不知能不能活到今天,所以俺曲源的百姓家家都供着乔大人的长生牌位。方才小老儿的儿媳往里间端去饭菜,其实是敬乔大人的,让各位客官见笑了。”
乔仲三人对视一眼后,乔仲郑重的说:“老丈,这乔仲当的是百姓的官,拿的是皇家的俸禄,吃的是百姓的饭,为老百姓做事是他份内的事,不值得……”
老者急抢过话头:“哎!客官,小老儿可要驳你的话了。你说咱老百姓整天价盼个啥?除了盼个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外,不就是盼个好官急难之时能给咱老百姓做主吗?有了心里惦记着老百姓,能给老百姓办事做主的好官,你说老百姓会不念着他、挂着他、敬着他?”
乔仲:“韦老丈,在下方才说过了,这都是他该做的事。”
老者:“客官,你怎么不想想,老百姓要是摊上个只知道刮地皮、捞好处、玩女人、祸害老百姓的浑官、赃官,老百姓不是就没盼头了吗?你说这样的官,老百姓怎能念他敬他?说句笑话,摊上这样的官,老百姓明地里不敢说什么,暗地里不骂他八辈祖宗才怪,谁会供他的长生牌位?”
乔仲三人默默地点了点头。
方永甫由衷的说:“韦老丈说得有理。老百姓摊不上个好官,是真没有盼头了。”
小村。村街上。
韦老丈陪同乔仲等三人边走边聊,一路而来。
乔仲:“韦老丈,今秋粮食丰收,不愁吃用,倘若再遇上灾荒年头,又该怎么办?”
韦老丈连连摆手道:“哎呀呀,客官你只管行路,请不要再提起这丧气话来,听着小老儿就浑身打颤。”
村前官道旁。
乔仲拉韦老丈在路边石头上坐定。
乔仲:“老丈,在下可以不说这丧气话,可是有丰年必会有灾年却是事实。”
韦老丈:“客官,话是这么说,虽说老百姓都盼年年丰收、岁岁温饱,可这灾荒年头不是咱老百姓不稀罕它就不来了!”
乔仲:“对啊,要是有了灾年怎么办?”
韦老丈沉思有顷,叹了口粗气道:“咳!还能怎么办?就盼能摊上个好官,老百姓还有个指望,要是摊上俺南丹县的那个被钦差砍了头的裴相铭那样的官,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言罢,又深叹了一口粗气,而后低头不语。
乔仲注视着韦老丈,默默地点了点头。
韦老丈抬起头来道:“客官,你们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经得多、见得广,曲源府去岁遭灾,官仓罄尽,这乔大人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粮食、种子?”
乔仲叹了一口气:“听说乔大人使了个没办法的办法,也叫权宜之计吧!”
韦老丈疑惑地:“没办法的办法?也叫权宜之计?”
乔仲:“嗯。他离京后,沿途从湖广的邵东、邵阳、东安、新宁一路进了广西、云南,先后征了三十几个县的粮食和种子,这才使曲源六县百姓有米果腹,安定下来。”
韦老丈:“真是难为乔钦差了。”
乔仲:“可是老丈你想,这朝廷也挺不容易的,一有灾荒年头就拨官银购粮赈灾,小小不然的还没有什么,要是受灾地方多了怎么办?官库空了怎么办?”
韦老丈:“客官说的是这么个理,可是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乔仲:“自救!”
韦老丈:“自救?怎么个自救法?”
乔仲:“灾荒年头,灾民不能设法自救,光靠朝廷放粮赈灾,总不是个章程。若是丰年时,官府敞开收储粮食,灾年时运往灾区,你看怎么样?”
韦老丈:“客官,这与乔大人沿途征集有什么不同?”
乔仲:“肯定不同,在外地征集,官府无法平抑粮价,只能随行就市,再者车、马、往返运费浩大,既增加了粮价成本,又给征集地方的官府、百姓添了不少麻烦。如果丰年年头由官府主持收储,既能把握行情,又节省开支,你看怎么样?”
韦老丈:“好是好,只是……”
乔仲:“老丈,有话但说无妨,只是什么?”
韦老丈:“这粮谷收储时若是价贱,种地的农户就要吃亏;要是收储时价高,销时价也高,大多数人吃不起。”
乔仲默默点头自语道:“粮贱伤农,粮贵伤民,粮贱伤农,粮贵伤民……”
韦老丈紧盯着乔仲问:“请问客官贵姓?”
乔仲沉思不答。
韦老丈遂又高声问道:“请问客官贵姓?”
乔仲从沉思中醒来:“啊!不好意思,敝姓乔。”
韦老丈一愣,沉思。
村口。
韦老丈儿媳呼唤道:“阿爹!阿爹!”
韦老丈闻声站起,乔仲等三人也站起。
乔仲双手一揖道:“多谢老丈食浆之恩,打扰了,后会有期。”
韦老丈也拱手:“客官太客气了,粗茶淡饭不值一提,后会有期。”
乡间官道上。
乔仲等三人渐行渐远。
村前官道旁。
韦老丈儿媳匆匆赶来。
韦老丈惊诧道:“儿媳,何事匆忙赶来?”
年轻女子道:“阿爹,您可知道方才这三人是谁?”
韦老丈:“是谁?”
年轻女子道:“就是放粮赈灾的钦差乔大人。”
韦老丈:“你怎知他是乔大人?”
年轻女子道:“今春赈灾时,儿媳去领粮,见过乔大人的,绝对没有错。”
韦老丈埋怨道:“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年轻女子道:“阿爹,当时孩儿也没想到,餐后去收拾碗筷,发现碗后有一锭小银,惊疑间想起这必定是乔大人微服私访,所以就匆匆赶了过来。”年轻女子边说边把一锭小银递给公爹。
韦老丈转身眺望远去的乔仲,动情的喊了一声:“乔大人。”双眼噙着泪花,踮起脚向乔仲等运去的身影眺望。
年轻女子:“阿爹,乔大人若能在咱这儿待上几年就好了!”
曲源府衙。客厅。
乔仲、杨广文分宾主而坐。方永甫坐于下首;乔禄侍立于乔仲侧后。
差役敬茶毕。
乔仲道:“杨大人,本钦差自入秋微服私访以来,所到之处民间粮谷盈余,官库仓溢廒满,让人心生愉悦之感!”
杨广文:“大人,这得感谢圣上和大人您呀。”
乔仲:“哎!杨大人,感谢圣上是对的,感谢我你这话可就说差了。这赈灾、安抚的差事换了你,不也是这样做吗?”
杨广文:“哎!卑职怎敢与大人相比?”
乔仲:“杨大人,不知你想过没有,若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自不必说;倘若再遇灾荒年份,当如何应对?”
杨广文:“大人,最好皇天保佑,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没有灾年才好,可这皇天保佑不保佑,咱又说了不算。卑职只是想,在其位、谋其政,干一年说一年,干一任说一任。只要咱心里有朝廷、心里有百姓,丰年、灾年让老天爷看着吧,谁有什么办法?”
乔仲笑着说:“杨大人,咱们就不能想个办法,让百姓躲过灾年?”
杨广文不解的说:“怎么?这灾年还能躲过?大人,请恕卑职没有东汉时九江太守宋均的德行,能令猛虎渡江东去,能让飞蝗不入九江。”
乔仲:“杨大人所说也只是先人所传,即或有之,恐亦属偶然……”
乔仲说着话慢慢地站起来,沉思着来回踱了几步:“杨大人,请问曲源城中可有名医?”
杨广文大惑不解地问:“卑职不知大人问医家何事?”
乔仲笑着说:“讨教讨教!”
杨文广一愣,遂喊一声:“来人!”
一听差公人应声而入:“大人,有何差遣?”
杨广文:“速去西关,把曲郎中请来,就说钦差钦差大人有话要问。”
乔仲:“嗯,不是有话要问,是讨教!”
差人应了一声:“遵命!”急下。
曲源府,客厅。
杨广文不解地问:“大人,您把郎中请来,要讨教何事?这些郎中即使医道如扁鹊、华佗再生,又有什么可讨教的?”
乔仲严肃地说:“杨大人,有道是:人有沉疴问病于医家,国有难事问计于大臣。西南一带汉夷杂居,地偏一隅,且天高皇帝远,倘若天公不作美,官吏不用心,再遇大灾却如何是好?”
杨广文仍不得要领地说:“大人,这治病与治国……”
客厅外。
差人进门:“大人,曲郎中来了。”言毕退下。
曲郎中进门躬身道:“见过大人!”
杨广文:“来!曲郎中,本官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钦差乔大人。”
曲郎中躬身一礼:“草民见过钦差大人。”
乔仲近前一把扶住曲郎中:“郎中是我请来的客人,何须多礼?”
曲郎中一头雾水地问:“不知钦差大人唤草民有何差遣?”
乔仲:“郎中请坐。说什么差遣?本官请郎中来,是有要事讨教。”
曲郎中仍一头雾水地问:“不敢当、不敢当,大人有话请讲?”遂在乔仲下首坐下。
乔仲:“郎中,本官近日心神恍惚似觉有疾,不知当如何医之?”
曲郎中取出脉枕放于桌上:“大人,请。”
乔仲把左手伸出放于枕上。
曲郎中并起三指轻轻地搭在乔仲的寸、关、尺处,又换右手。切品有顷,遂斟字酌句地说:“就大人脉象,似乎无疾,但却需汤药调理。”
乔仲点了点头:“就依郎中。”
杨广文好奇地说:“曲郎中,既然大人无疾,为何却要施药调理?”
曲郎中:“杨大人问得好。若是别的医家恐怕就不开方施治了,可学生却要拿着无疾当有疾。”
杨广文:“曲先生这是为何?”
乔仲饶有兴趣的听着二人对话。
曲郎中:“钦差大人眼下确实无疾,但大人近日肝气不舒,肝火时有上攻,若不调理,必然肝脾违和,不出仨月,大人必身疲神倦,四肢慵懒,厌食恶心,腹部痛疼。眼下调理,三剂汤药足够,若待三个月后,肝疾生发,恐三、五十剂也难以治愈。学生说句自捧的话,这叫做良医治未病,病重在防而不在治。”
乔仲忽的一下站了起来,朝曲郎中深施一礼:“多谢郎中教我,好个良医治未病,好、好!重在防而不在治!杨大人,听清楚了?良医治未病,重在防而不在治。”
杨广文无比感慨地说:“大人用心良苦,卑职永铭五内,治未病,重在防而不在治。”
曲郎中:“钦差大人,知府大人,若无教诲学生告退,待会儿遣人把药送来。”
乔仲拉住曲郎中的手,亲切的说:“郎中,多谢你的点拨,闲暇本官定去尊府拜会请教。”
几人寒暄辞别。
乔仲对方永甫道:“方百户,明日辛苦一趟赶往布政司衙门,传我口谕,让暂摄布政司事的董大人传下谕令,来年正月十八,云南行省各有司知亊,俱到布政司衙门议事,不得有误!”
方永甫躬身道:“卑职遵命。”
乔仲:“方百户记住,七日内定要赶回来。我在曲源府衙等你。”
方永甫:“大人放心。”
官道上,朔风呼啸,行人稀少。
乔仲三人骑马走走看看,一路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