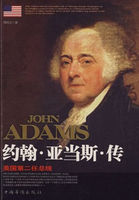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
【原典】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最足养福。
【译文】
“智、仁、勇”三项通透的德行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豪杰志士、才能特出之人都被称为英雄。英也就是明的意思。所谓明有两个方面,他人只看到近前的事物,我则可见更深远的事物,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显眼的东西,我则可看见细微的东西,叫精明。这里所说的高明,好比身处一室之中,人们只能看近处的景物,若登上高楼,看得就远了,再如登上高山,所见的就更远了。而精明,就如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照它,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又如满是粗糠的糙米,捣两遍就可除去粗糠,捣上三遍四遍,就精细白净到极点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资质,精明则全赖于后天钻研学问的程度。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身居高位,天赋资质都不算很高明,全靠勤学好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买显微镜,可深知极细微方面。好学如同捣熟透了的米,可去粗取精。总之,必须心中了如指掌,而后才可口中说出自己决断。对事物能了解明白再作决断,就叫英断。稀里糊涂就作决断,人们称之为武断。武断自身的一些事,产生的危害还不大;武断他人的事情,因此招致的怨恨就很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下决断,才足以保住福分。
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的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要警惕啊!
人们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捉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他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把他的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人们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对你会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曾国藩一再强调“强”字自“明”出。在智慧处求强,在自修处求强,这样才能使人挺进。他始终主张持之以恒,绝不灰心泄气,绝不矫揉造作,一如既往。然而在功名渐盛、地位渐高的时候,则其势不同,就需要持盈保泰,恬退谦谨了。他虽说“亦渐老于事,锋芒钝矣”,实则故乐谦德,“喜闻迂直之言”,而以贞固自守。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三日《致九弟书》云: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彼从丁巳(咸丰七年,1857年)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通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又同年三月初二日书云: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想心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贞),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元),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悔”“硬”二字诀,是曾国藩立身处世思想之化境。照一般的解释,总以为曾国藩悔悟其往日强矫之非,而毋认柔道行之了。其实是他“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对立一致之合。悔是“悟”的意思,“明”的意思,觉悟出真道的微妙处,知“自己全无本领”,正见得自己“本领甚大”。“能立”“能达”“不怨不尤”,方刚柔体用之极致。曾国藩还说他兄弟不明白悔字的奥妙,而趋于消极,乃用一硬字诀的“挺”字来救济。梁启超先生所谓“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龙梦荪先生所谓“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阴,亦不足以夺其志”,都见出一个硬字来。故曾国藩晚年仍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又说他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他虽衰老,“亦勃常有不可遏之候”。
这正是以挺(强硬)为体,以柔(廉悔)为用,合禹墨老庄为一途,以成中庸之道。
曾国藩在进攻太平军时,曾亲自率领在衡州组建的水师东征,想一举消灭太平军。不料,因刚训练出来的湘军水师作战不力,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后来,曾还带领在长沙的水师五个营晚上偷袭靖港,亦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灭。
以往,曾国藩曾多次讥笑清廷绿营兵不能打仗,如今看到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屡战屡败,感到“无脸见江东,一气之下,在船上滚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身边的人发觉,才把他打捞上来,护送回长沙大营。
在长沙,曾国藩灰心丧气,几天不吃不喝,弄得满城风雨。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上,有冷言冷语、幸灾乐祸的,有向上告状、弹劾曾国藩的,还有认为湘军不能作战,主张解散另建的。曾国藩听到这种种舆论,坐立不安,既有几分不服气,又有几分羞愧。
正在心灰意冷之时,曾国藩接到了父亲曾麟书的手谕,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其父的勉励下,曾国藩鼓起了勇气,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禀报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对岳州、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阅得此禀报,似乎说自己太无能了,便接过笔去,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改,被动变主动,消极转为积极,“败不馁”之气魄跃然纸上。皇上看了,对曾国藩虽未获胜,但仍表示满意,督令再战。
据说,曾国藩为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嘱弟在家代为准备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其幕僚便将他家备好棺材,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一奏折,对曾国藩忠君的决心倍加赞赏,原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后又收回,改赏给兵部侍郎衔,并催令迅速东下,进剿太平军。
处事不乱,不逞一时之强
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脆,以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着《挺经》,说他刚毅。”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
至于强毅之气,绝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自胜,也得克己,所以,刚强也是一种克己之学。克己,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即“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曾国藩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非就是暴虐,强矫而已;柔并非卑弱,谦退而已。”
为使“刚”得恰到好处,“柔”得也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均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致书诸弟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用后果证明它,又重新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师说的瞎闹。我也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力,终归都是害人害己。什么是“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同样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而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立业的。
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大概能持久恒常。”《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怕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败露;练就意志刚强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向清廷伸手要权,拒绝鲍超北上勤王,便是《挺经》“明强”法中最典型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