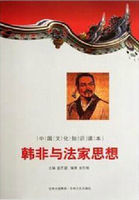他因冰如只管沉吟着,不知道她有什么话要说,未便冒昧着先开口去问,也就两手反背在身后,昂了头看天上的月亮。冰如也随着抬头望了月亮,轻轻地唱道:“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同庆团圆夜,几个飘零在外头。”江洪笑道:“歌本是好歌,在嫂嫂嘴里唱出来就格外的有意思。”冰如将头连摇了两下,哼道:“你这样称呼不好,谁见叔嫂两人这样交情深密的?其实,我们又何尝是什么叔嫂呢?现在男女社交公开的日子,本来不必介意。可是你左一句嫂嫂,右一句嫂嫂,叫得我倒不好意思同你一路走了。”江洪嘻嘻笑了一声道:“这话太奇怪了。我和志坚是极好的朋友,他的年纪比我大,我把他当兄长看待。他的夫人,我称呼为嫂嫂,有什么使不得呢?”冰如将头一偏道:“你这话我不爱听,难道没有孙志坚的关系,我们就成为陌路之人了吗?这样说,现在志坚的命运,还在未定之天,所以我们还有这点关系。设若志坚有个不幸的消息,你之所谓嫂嫂,已不存在,哪里还认得我呢?”江洪呵哟一声道:“这是什么话?无论志坚命运如何,我对嫂嫂,决计保护到底。
”冰如道:“别的话不用说,我最后问你一句话,仅仅我们两个人而论,我们有没有友谊存在?”江洪道:“你这话总问过我一百次了,而我也答复过一百次,我们是有友谊的,为什么还要问呢?”冰如道:“有你这一句话,那就好极了。我们既是有友谊存在的,你……”说到这里,她沉吟起来,把一个字拖得很长。最后她就道:“你应当明白我的意思。”江洪听着她说出这句话来,倒不由得心房连跳了两跳,低了头不敢做声。冰如道:“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但我觉得我的真心,是把你当了一个最知己的朋友。其实,你却对我最不知道。我不要成了错认朋友的尤三姐吧?”江洪呵哟了一声道:“那怎么能相比?”说着两手插在裤袋里,在路上来回地走了七八个转转。冰如道:“为什么不能比?我觉得我为人率直,热烈,一切不下于尤三姐。”江洪道:“你把一个大前提就弄错了。人家是一位小姐,名花无主,她可以把任何人做对象。你是一位有主的人呀。
”冰如淡笑道:“你还说你是一位有新思想的军人,可是由你这说话看起来,你的思想就很陈腐,你依然认为寡妇是不能嫁人的,而寡妇也不该有个对象的。”江洪道:“你不要过于绝望,自己把自己拟在一个最不幸的境遇里,也许志坚可以回来的。”冰如道:“你这就不是以诚实来待我了。一个当军官的人,半年多没有消息了,你还说他能够回来。我实对你说,我这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想自杀,终于想到还有你这样一个人在宇宙里,我是等着你能给予我一条光明的大道。在今天这清风明月之下,我望你给我一个答复,不要再装麻糊。假如你讨厌我是一个妇人,不是一位小姐,你也明说,可是你所追求的王玉,她不也是一个离婚的妇人吗?”江洪见她越是把话说明了,便站住了脚,从容地答道:“我可以答复的。实在的,我觉得志坚回来的希望,也并没有断绝。你又何妨再忍两个月,再等一等他的消息呢?”冰如道:“你那意思,假如志坚不回来了,我们的关系是在朋友上面可以再进一步吗?”江洪还是插了两只手在裤袋里来回地走着。
冰如道:“你怎么不答复我的话?难道你这几个月来所对付我的态度,完全是虚情假意吗?”说着,用力将手牵着柳条一扯,扭转身就走了。江洪站在路头上,倒是呆了一呆。然而她走得很快,转个弯就向街里面走去了。假使要跟着追了去必定追到她家。在这夜晚,追到她家里去,特显着自己恋恋不舍了,因之缓缓地在江边上放着步子,细想了一番,最后也还是回寓安歇。由汉口渡江到武昌,再经过几截街道的奔波,人也相当的疲倦了。到寓之后,和衣就倒在床上,他心里也就想着,薛冰如之为人,却是有点奇怪,她对丈夫原来是很好的,只几个月工夫的别离,何以就变了态度了?仰睡在床上,睁了两眼望着那粉墙,这就看到自己一张一尺二寸的半身相片,悬挂在墙上。二十八岁的人穿了笔挺的西服,面貌丰润,很英俊清秀向下俯视着。自己便转了一个念头道:是呵!她是一个青春少妇,遇到我这一个少年,不断地在她面前周旋,看到汉口花花世界有什么不动心?而况志坚之阵亡,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她要找个继任的丈夫,是没有比我再合适的了。几个月来,她只管浓妆艳抹,与王玉斗争,无非是为了我。我应该用好话安慰她,多少补偿她这一点苦心。
今晚这种态度,慢说是一个男子对付女子,就是一个女子对付男子,男子也有所不堪,那是很难怪她一怒而去的了。明天下午决计过江去一趟,向她表示一番好意,一个有家仇国难的女子,又何必让她过于难堪?他这样想了,就也蒙眬睡去,晚上倒做了几次梦。下午由办公室回到寓所的时候,身上照例是穿一身军服,腰间挂了佩剑。纵然是工作了一日,精神还是很好的,踏着夹了马刺的皮鞋,走着地板,啪嗒啪嗒地响。他想着,去看女人,那是软性生活。干软性生活,而穿着这笔挺的军服,那是用不着的,于是站到卧室墙前一面大镜下去松解皮带。偶然抬头,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的影子,却是一位少年英勇的军官。自己忽然叫起来道:“我是中华民国一个好男儿。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是什么人,我能脱了这身军服去看朋友之妻吗?笑话,我不去了。”他口里说这话时,脸上自然显露着十分坚强的颜色,同时,也就看到镜子里的影子,十分兴奋,便向镜子里点点头道:“对的!对的!”连说两声对的,他也就再不松皮带,依然穿了军服,走到寓所外的空地上散步了很久。经过了这一番严肃的散步,把冰如给予自己的那些影响,也就忘记了。
王玉那条路,自己是坚决地抛弃了,甚至提到这个名字,自己也就有些烦厌。冰如这条路,自己现又不愿去。那么,除了自己故意到汉口去消磨几个钟点,就不必离开武昌了。因此,约有三日的工夫,并未过江。这个时候的长江战争,胶着在下游芜湖一带,武汉的人心,大为镇定,而前方同后方的邮电交通,也随了这个关系,比以前便利得多,可是孙志坚的消息,依然石沉大海。这就是江洪自己想着,要说他还在人间,透着不近情理。那么,孤身在汉口的薛冰如,那是格外可怜了。在他这样一念生怜,意志转变的时候,冰如却寄来一封挂号信。她破了例,不是女人所用的那种玫瑰色洋信封,却是一个很长很大的中式信封,厚厚的里面盛着许多东西。当江洪接到这封信的时候,看到信封下署着的姓名,就不愿接受,想一下丢到字纸篓里去,但是捏着那信封厚厚的,里面软绵绵的,像不光是信笺,且拆开来,看她在里面放些什么。于是慢慢地将信封口拆开,向里张望,竟是塞得满满的,把信瓤子向外抽着,首先有一阵香气袭进鼻孔。开来看,是一副花绸手绢,一张四寸半身相片,另外还有一张信笺。心里暗想,她真会玩手段,看她信上说什么,自己又向门外张望了一下,然后将背朝外脸朝里,手托了信笺看,上写着:
洪,你接到了这封信,一定很是讶然,以为为什么还要写信来呢?我也本不想再写信给你。可是我想到我们共过一场患难,纵然那晚江边你让我太失望,我为了感谢你患难之中,对我种种恩惠,我依然认你是个好友。我相信,你大概不愿再见我了,我也无法要求你再来见我,寄来最近所摄相片一张,算代我亲身前来道歉,请恕我那晚上不告而别。另手绢一副,是我亲用的东西,上面虽不觉为残香剩粉弄脏了,但也有我不少的泪痕,留在你处,权当纪念吧。自那晚回来之后,我就病倒了,至今不能起床,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客地孤身,真是十分凄惨。我不敢望你来探望我。如果过江有便,请代买一点酱菜来。明天是星期六,这信上午可到,下午你必定渡江的,我当在枕上等候听那上楼梯的皮鞋声了。冰如扶枕上。
江洪拿了这封信在手上,先是呆了一呆,在出神的时候,那脂粉香味,不住地向鼻子里送来,让人感觉着这不是在军人寄寓的卧室里。睁眼看时,左手拿了冰如的那封信,右手就拿着她的手绢和相片,放下信,两手把手绢展开来看看,虽是她说这上面有眼泪,却丝毫找不出泪痕,倒是她说的残香剩粉,那是事实。除了香是很容易证明它存在,而这剩粉一物在将手帕抖上了两下之后,也就可以看出来。江洪把手绢随塞在衣袋里,将放在茶几上的相片,举着与自己的脸相齐,注意看了一看,见她那影子略偏,双眸微斜,嘴角上翘,露了半排牙齿,那要笑不笑的样子,实在风韵艳丽。江洪将相片看了一阵,也放到衣袋里,然后将冰如的信两手捧着,读了第二遍。最后江洪想到她希望发信的次日下午等我。这是昨晚上写的信,还正是写信的次日下午了,应当怎么样应付她这个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