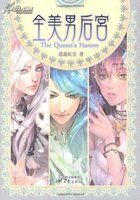一天早上,他在妻子身边醒来。由于妻子是面朝墙睡觉的,他只看到妻子浓密的披肩金发。睡裙盖住了丰满的臀部还有白皙的腿。其他什么也看不到。以前,哪怕是在他最大胆的梦里面,妻子也都总是穿着衣服的。这应该是什么病态心理吧。
习惯性的清晨神经疼痛的布莱里奥龇牙咧嘴,他踮着脚轻轻走向厨房去弄杯咖啡,服了两片阿司匹林。同时他也打开澡盆上的水龙头放着水,之后好洗澡。在洗脸池的镜子上,他看到了自己的面孔。这是一张筋疲力尽的男人的脸,黑眼圈很大,骨头棱角突出。
洗澡水太热,上面热气缭绕,像是一层雾一样。看着这水汽,布莱里奥躺进水中,伸开了双腿,又开始思考回来之后的娜拉那无法理解的举动。
要知道,他已经给她留了十几条短信,然而她是死是活自己都不知道——她一个字都没有回。
她会回话吗?她不会回话吗?
用脚趾打开冷水开关后,现在的布莱里奥准备祈祷她不会回话和他将失去一切。但是明天,他的惯性还是会让他往完全相反的方向想。刮完胡子之后,他穿上一件翼领白衬衣,配上牛仔裤。尽管天气很热,他还是系了一条黑色皮领带。这么仔细的装扮,如此考究的优雅,足以适合所有用一生来等待某个人的男人。
为了不过分的去想娜拉,他开始观察下面的女邻居——她正在院子中间。这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俄罗斯女人,几年来都从未出过门。他开始任意猜想——想到了积满灰尘的提花桌布的味道,还有大小便失禁的老猫的味道——因为她很明显决定看电视一直看到死。
看着她不急不慢地吃着自己的面包片,布莱里奥突然也开始羡慕起她来——至少再也不用等待什么人。
然后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闲逛,轻手轻脚地像个无足轻重的停职的小人物,尽量不吵醒妻子。同时也把百叶窗一扇一扇地打开,看着窗户外面明朗的天空。
他们住在这栋老楼的顶楼,窗外可以看到整个美丽城(中国城)。秋天有时会有白云飘过,这时的感觉还真有点像住在豪华旅馆里。
虽然他们的这套房子其实很丑,而且不舒适,但是还是有优点的:很大,而且是跃层,上下由一个螺旋形的楼梯相连,这样就总能避免两个人在家中擦肩而过。
由于是跃层,他们可以交替使用两层的空间。因此,当一个人在楼上听音乐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可以安静地在下面那层做自己的事情。
实际上,他们经常都是分别占据着自己的空间。尤其当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们会各自待在自己的楼层,在自己的角落里看电视——不用忍受另一个人的评论。
妻子和他基本上是住在同样的空间里,生活在同样的时间与节奏中,睡觉有时一起——在萨碧尼的卧室内,有时各睡各的楼层。然而,他们更像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而且两个世界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远,甚至无限远。
有楼梯,房子又大,又缺少家具,这些情况也许加重了彼此的空虚感。这种空虚感包围着他们两个人,即使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于,下午布莱里奥越来越经常性地像个孩子那样自忖:这个房子里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你已经起来了?”妻子突然在他身边出现,惊讶地说。她身上穿着浴袍,头上裹着毛巾。自从眼睛发炎之后,她一直戴着深色眼镜,几乎从早到晚从不离身。现在深色眼镜给了布莱里奥不同的感觉——似乎一个盲人在为他的欲望而来。直到他拥吻她的时候,感觉到她凉凉的脸颊,还有她那暗示拒绝的身体姿势,他才断了这个念头。
“你的旅行还好吧?”她以一种轻松的语气对他说,他却感到了一点不安。
“也许她已经知道了。”他这样想。然后赶快重新镇定了下来,还即席编造了一段话——主题是父亲的忧郁和萎靡。
“我还有几页没有弄完。”他临末加了一句,就从妻子旁边走开了,转身去自己的书房。书房长六米,宽五米,在楼上。那里严格意义上说虽然不是工作的地方,但是至少在那里他可以安静地思考,“宽敞”地思考。
为了不再忧虑,好尽快静下心来,他赶紧关上门,打开电脑。布莱里奥对工作计划向来不感兴趣,就像他不喜欢去了解这个社会一样。他做英语、法语自由译者已经有三四年了。然而与其说这是份工作,倒不如说只是给一些小老板、小作坊做廉价劳动力——所得的报酬寥寥无几。
由于是一个人单独工作,他不得不见活就接,无论什么东西都去翻译——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收入好一些。所翻译的东西有科技文献、有药剂说明书,还有一些家用电器的使用指南。工作顺利、收入良好的时候他一般是在给一些医疗会议做翻译。但是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就待在家里,等着人家联系他。
如果没有人联系他翻译东西,他就只能靠身边朋友的接济。
这种不得已的筹钱办法,最终使他在妻子和父母面前留下一个总是入不敷出的坏印象——他为此也深受折磨。
今天早上他几乎一直鼻尖贴着窗户往下看,就像娜拉在外面等他一样。现在他看到街上有一个穿衣服的男人,看样子很像一个做生意的中国人。这个人背着他儿子,身边还跟着一路小碎步快走的妻子。妻子不时地用一个玫瑰色的小水壶给孩子的脸上喷点水。
布莱里奥身体尽量往前倾,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直到他们在美丽城街道的拐角处消失。他们走后似乎留下了一串无限幸福的轨迹。
他是那个儿子吗?他是那个带着儿子走入另外一种生活的父亲吗?
他想这个问题想得出神,不知不觉地慢慢坐到了显示器前。最近这六天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活儿干。今天下午他一直在绞尽脑汁地翻译一篇医疗杂志上的文章。文章不仅离奇而且很复杂——有关如何治疗非洲被锁阴器残害过的女人。后来他终于放弃了,下楼去厨房找了一瓶啤酒喝。
再从楼梯上去的时候,他听到妻子在客厅里哼一首南茜·塞纳措的歌,于是僵住了,不由自主地听了下去。他竟然不知道她喜欢南茜·塞纳措。
“You shot me down,Bang bang,I hit the ground,Bang bang”(你开枪将我打倒,;我摔倒在地上,),她哼着歌词。嗓音是布莱里奥从未听过的,就像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这么美妙的声音让他禁不住战栗:好像在几年之后才发现妻子的美貌似的。
这首歌结束之后,他心中的一切忧愁与苦涩都不见了。似乎他们夫妻之间那种逐渐扩大的距离感突然被一种魔力遏制住了。不能再什么也不干了。他继续上楼,没有弄出一点声响,小心关上了房门。
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啤酒的同时,他将窗帘拉了下来,因为在黑暗中他的思路更清晰。之后,他在墙角的沙发上舒展开身体。现在的他尽量将自己放松。“一切都好。”他斜躺着,半眯着眼睛,就像一只在宁静的夜晚喘息片刻的野兽。“一切都好。”——他又重复了一遍。同时收腿,将膝盖顶住自己的胸。在这半昏半暗的暮色中,窗帘显得几乎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