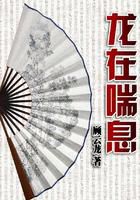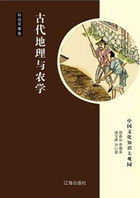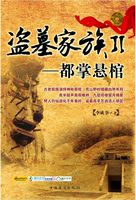4年前无意中填了中国一家航空公司的里程累计卡,听介绍说,当你累计到一定的里程以后,就可以换取免费机票,如果里程高了,还可以获得金卡,银卡,有了它们以后,好处就大大的啦。一年以后我就收到了一张银卡,随附里程明细单清楚地记录了我这一年的飞行里程和次数,那一年我飞了6万公里,飞行将近30次,绕了地球一圈半,这还不包括我乘火车和汽车的里程。旅途是艰辛的,无聊的,枯燥的。我不喜欢旅行,特别是长途旅行,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消耗生命。每当又要开始一次新的长途旅行时,就希望能有几个朋友一起旅行,或调侃,或打牌,总之时间会过的很快。如果一个人旅行,就要学会忍受寂寞,否则就要在旅途中寻找合适的‘旅友’了。如果你有幸再有一段艳遇,碰上个把帅哥美女,你的时间就穿梭如飞了。这时候我们那位爱因斯坦老爷爷的假设是最容易得到证明了,和美女聊天,时间就会比和一般人聊天过的快,更何况飞机本身还飞呢?几年来,我做了无数次旅行,当然有几次‘艳遇’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六年前的一天,我踏上了一列从北京去山东半岛的火车。山东半岛的最东部伸向黄渤海,从北京到胶东半岛的直线距离最多不超过600公里,而乘火车,由于绕道要多出一倍的距离,再加上中途什么站都停,火车要晃晃荡荡的17个小时才能到。我买的是中铺的票,火车一开动我就爬了上去,迷迷糊糊的不知睡了多久,醒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黑了,隐隐约约地感觉肚子开始叫了。下了中铺坐到了下铺,顺便泡上了一盒方便面。无聊之际四处打量了一圈,我这个隔段里一共有6张铺,最上面的两张铺上睡着两个人,由于蒙着头,呼呼大睡,也看不清是什么样的人。下铺是一对老两口,估计有60多岁。对面的下铺,还坐着一个年纪有28,29岁的女人。这对老两口也开始吃东西了,面包,香肠,水果,把小桌子都给摆满了。那位老大爷和蔼可亲,还很有文化的样子。他吃完了一些东西,便主动和我拉起了家常。老大爷声音洪亮,言语不失幽默感,有的时候逗得对面的那位女士也笑出了声。我这时才有机会把她仔细的端量一下。她留的是‘巧珍’头,四方型的脸,白白的皮肤,眼神多少有点忧郁,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贤惠的女人。很自然地她也加入了我们的聊天。不只不觉时间就过去了,老大爷说:你们接着聊,我们要睡了。
似乎我和她还都没有睡意,但是也不能坐在这对老人的铺上聊天,根据我的建议,我们就坐到了过道边上的小座位上。开始聊的还是比较泛泛,但是后来不直不觉就深了,从双方的工作到家庭,无所不聊。她已经结婚两年了,但是他的丈夫是一个酒鬼,经常到半夜才跌跌撞撞的回家。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她的丈夫还打她,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打她几下,到了后来就变本加厉,脾气一上来,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打。如果他提出离婚,他打的就更狠。男人打老婆,一般我只能在一些小报纸上才能看到的事情,而且也是半信半疑。而今在我前面的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实例。我感觉男人打女人是一种最为懦弱的表现了。首先说明他不能适应家外面的竞争,外面输了以后回家找平衡;其次,为了证明他在家里的地位,就采取武力的办法以强示弱,武力镇压。实际上,女人天生体力就不如男人,一生出来就宣告自己是属于受保护的种类。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就是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如果一个女人连在自己的庇护所里都没有安全感,那么她这一辈子的命就太差了。作为一个男人,保护自己的女人是天经地义的。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并且建议她应该采取那些手段才能完成离婚。她似乎已经接受了我,并把我当成了知己。她边说着还把袖子往上挽了一下,我一看,她那莲藕般细白的胳膊上有着一块快的淤血。我感觉她的说话的声音有些变了,眼睛也有些发红,长长的睫毛上挂着一滴马上就要掉下来的泪珠。一种怜香惜玉的感觉涌上心头,而且还产生了拥抱她的念头。接着是一阵沉默,我们两目相对,车厢的人都已经睡去,只有那火车的轮子轰隆隆的不断地重复着一种声音。我感觉她也在渴望着一种被人理解,被人拥抱的感觉。我记得有位作家曾经总结过如何判断一个女人什么时候接受了你,而你也可以采取行动了,那就是当她把自己的经历和隐私都向你全盘托出的时候。按照这位作家的建议,她这一点做到了,而且她的眼神已经告诉我她的防线已经崩溃了。但是理智告诉了,这样做不会有后果,而且不要乘人之危。
我们是中铺,她睡在那边,我睡在这边,中间是一米宽,两米深的空间。车厢里的灯已经全熄了,我们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对方的脸,即使是这样我依然看着她,我也感觉她也睁着眼睛看着我。我把手伸过去,她也把手伸了过来,两只手会意的紧紧地握了一下。我把手收回来,放进了被子里,眼睛依然看着感觉也在看我的那双眼睛。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列车服务员叫嚷着:“快到站了,换票了”的声音吵醒了,啊!天已经全亮了,对面的铺已经没人了。我急忙下了铺,问老大爷这个女的呢?他递给我一个纸条,说:她两个小时以前就到站下车了,这是他给你留的电话。我真后悔自己为什么睡的和猪一样,至少也应该跟她告别呀。到了站以后,我也没有给她打电话,因为我和她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前年的一天,我又踏上了那列火车,翻出了那张一直珍藏在我的笔记本里的那张纸条,用手机拨了那个号码,而电话里的声音却是:“您所拨的号码是空号,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NT EXIST”。我听着这不断重复的声音,心里一阵惆怅。我把那张小纸条,先是撕成了两半,然后是4份,8份。一直到了一把碎片。我的手伸到了窗外,一张手,碎纸片随风而去。
2005年3月13日星期日 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