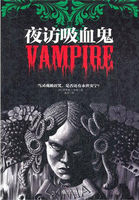狗剩说:“我干爹在那里和人家拉秧子哩!”
梅广济抓起刀来,剁掉自己的小手指。
还没等张卫东明白怎么回事,张二秃子撞在了碾盘上。
狗剩挨了苏秀的两巴掌,又挨了梅广济一顿训斥,心里有些窝火,心想: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何不挑个事看个热闹?他来到梅广济家,进门就叫:“干娘,快到场屋看看吧!”
李玉芬说:“下着个雨,我到场屋干什么?”
狗剩说:“我干爹在那里和人家拉秧子哩!”
李玉芬说:“跟谁?”
狗剩面带神秘地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上次梅广济给苏秀下种的事,李玉芬气还没完全消,这次他竟敢又和女人好上了!狗剩的话对李玉芬来说简直就是如雷轰顶。她跑到伙房抄了把菜刀揣在怀里,就往场院奔去。
李玉芬疯般地往场屋跑,两只鞋跑掉了一双。快到场屋的时候,她却放慢了脚步,把刀从怀里抽出来,慢慢往门口靠。她像一个非常老练的公安,到了门口猛地一脚把门跺开,提着刀闯了进去。
外面的雨下得一片混沌。也许在这样的场景里,人会变得特别单纯。梅广济、苏秀经过谈判,达成了互不干涉的口头协议。就像合同要签字画押,两个人竟用了儿时拉钩的游戏:“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当两个人手紧紧勾在一起,一起发誓的时候,李玉芬提着菜刀闯了进来,两个人吓得赶紧分开。
“你们两个狗男女,竟干出这种乱伦的勾当,我把你们这两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劈了喂狗!”李玉芬一边骂,一边挥刀朝梅广济劈去。
梅广济一把抓住李玉芬的手脖子,把刀夺过来,扔在地上,说:“闹什么闹?”
但无论他怎么解释,李玉芬就是不信。梅广济抓起刀来,剁掉了自己的小手指。
苏秀看到那截手指精灵般在屋里飞,飞到她的头顶,一滴血落下,落在了前额上。小手指空中打了一个旋,飞向李玉芬。李玉芬下意识伸出手,小手指正好落在她的手心里。“广济——”李玉芬一声大叫,晕倒在地上。
张卫东来找狗剩,狗剩竟不在家,张卫东生气地骂道:“真是个靠不住的主。”于是他又来到梅有福家,找梅有福商议批斗梅琴的事。梅有福因为梅尚德家发生的一串不幸的事,本来生发出些许恻隐之心,不想再折腾可怜兮兮的梅琴,但是自己是民兵连长,再加上张卫东的策动,最终还是加入了张卫东的行列。
他们把棒子队集合起来,来到梅琴家。结果只有赵诗文一个人坐在地上发呆。
“诗文,我知道你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要么拿结婚证,要么把梅琴交出来。”
“结婚证没有,人也没有。”赵诗文抬起头来。
“给我搜。”张卫东一声令,队员把个小院里里外外寻了个遍,结果,就是不见梅琴的人影。
“好啊,赵诗文,你窝藏、包庇地主羔子,你已经走上了人民的反面。绑起来,送到公社去。”
几个青年把赵诗文绑了起来,赵诗文竟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没有豪情、没有义愤、没有伤心、没有悲哀,满脸的麻木。
梅婷见爹愁眉苦脸,就问:“爹,你怎么了?”
梅广慧好久才叹了口气:“婷儿,诗文被抓走了。”
“抓走就抓走呗!”
梅婷一副毫不在乎的口气,让梅广慧大吃一惊:“你说什么?他和你不、不已经、已经那样了吗?”
“爹,女儿没那么傻,让他赵诗文白白占我的便宜。那是女儿瞎编的。既然他那么不在乎我,我何必又那么在乎他?我就是要他看看什么叫一步走错步步错,叫他后悔都来不及。”
听了梅婷的话,梅广慧虽然不满女儿的做法,但知道女儿还是清白的,心里就踏实多了。他又叹口气说:“诗文也是自作自受。”摇摇了头,然后往家走了。
赵诗文的举动让梅花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她的感情像一团正剧烈燃烧的火,猛然遭遇疾风迅雨,连那冷冷的灰烬都没有了。
因为梅广元家吃饭的多,干活的少,本想留梅花在家多干几年活再出嫁,现在,他完全改变了主意。梅广元说:“女儿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他决定让女儿早订婚、快结婚。
薛蓉托于莲给梅花说媒,男方就是柳庄的梅琴原来的男友柳永青。柳永青的父亲也是大队里的革委会主任,日子过得自然比梅家好。更主要是小伙子长得帅,现在乡里当文书。梅广元对这门亲事很满意。
梅花把她精心绣制的鞋垫拿出来,正看看,反看看,然后拿起剪子,把鞋垫铰成条,最后又把一根根的鞋条铰成丁。
薛蓉偷偷地抹一把泪,那一堆的布丁就是女儿破碎的心啊!薛蓉没有劝阻女儿,她知道,只有时间才能医治女儿心灵上的创伤。
张二秃子让张卫东气得连头上最后几根毛发也脱光了。老婆高英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只要一从梅尚德的坟前走过,回到家就必然大哭一次。每当哭的时候,她就和梅尚德发生了角色置换,哭诉张卫东的不是,骂张卫东不是人。
这天,小麦冬灌,高英去浇麦子,不得已又来到梅尚德的坟前,她看到一个小旋风从坟头上刮起,直向自己刮来,她扔下铁锨就往回跑,跑到家就哭开了,一边哭一边诉说:“张卫东,你没良心,你缺德,你没人性,你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你不得好报,你不得好死。”
郭兰听了“不得好死”的话,感到毛骨悚然。
张卫东听了并不在意,对郭兰说:“娘得的是内心恐惧症,是对革命不太适应造成的。等革命成功,拿下了梅广慧,我坐上梅庄大队的第一把交椅,娘就会为我骄傲。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梅广慧是名副其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时候了!”
郭兰挺着个大肚子,眼看就要分娩了,一方面希望张卫东守在自己身边,另一方面怕张卫东作孽太多遭报应,就力劝张卫东不要再做得罪人、丧良心的事。张卫东一听就火了:“我的事,你少管。要革命就要有牺牲,怕牺牲就不革命了!”
梅花穿着一身崭新的碎花棉衣,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柳永青身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胸前佩着大红花,满面红光。他牵着马缰,回头对锣鼓队说:“弟兄们,打响点!”
对面也过来一队人,也是锣鼓喧天。赵诗文被公安押解着在接受游斗。两队人马相遇,都停下来,锣鼓摞着劲地打。
梅花掀开红蒙头,看了一眼面容憔悴的赵诗文,又把蒙头落下来。两队人马各自前行,当赵诗文和梅花一错身,布丁像雪一样落在赵诗文的面前。赵诗文停下来,拣起一块布丁,放在眼前仔细端详,他的心怦地一跳。他站起身,看看渐去渐远的梅花,两颗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快走!”押解的人用力推着赵诗文。赵诗文不动,另一个给了赵诗文一枪托。眼看着梅花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赵诗文使足了气力,大叫一声“梅花——”
“诗文哥——”赵诗文停住了脚步,竖起了耳朵,是,没错,又一声“诗文哥”传进了他的耳鼓。他回头一看,梅花正向自己奔来。那红红的盖头被风吹起,挂在一株光秃秃的杨树上。
上级要求各大队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张卫东就到供销社买了一桶红漆,和狗剩一起挨家挨户往门上印领袖像。当全大队都印完时,狗剩悄悄地把像模和剩下的油漆拿走了。
回到家,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热爱,狗剩把领袖头像印得到处都是,最后看到还有两个水罐,就又把像印到上面。
狗剩挑着水罐去井上打水,一边走一边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
梅广济走过来,看到狗剩水罐上竟有领袖像,就严肃地说:“狗剩,你他娘的,你想让伟大领袖跳井啊?”
狗剩一听,胆都吓破了,赶紧把水罐一撂,跪下来,对着水罐磕起了响头。
梅广济说:“你给我听着,要想得到伟大领袖的原谅,你必须把水罐放到大桌子上,每天早晚一次,向伟大领袖汇报你一天的所作所为!”
狗剩挑着水罐回到家,把水罐放在八仙桌上,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心里这才有些踏实了。可是,心里踏实了,肚子却饿了。不但是饿,一种想吃肉的欲望空前强烈。不知谁家的一只母鸡觅食觅到狗剩家里,狗剩就把鸡轰到屋里,关上门,要来个瓮中捉鳖。狗剩来了个饿虎扑食,直向老母鸡扑去,鸡没有抓到,头却被墙撞了个疙瘩。狗剩揉揉头,心想“我就不信抓不到你”。狗剩又是一个鱼跃,向鸡扑去。鸡惊魂失魄,四处乱飞,一下子飞到桌子上。狗剩再一扑,结果鸡没有抓到,桌子倒了,水罐碎了。
这回轮到狗剩失魂丧魄了。他跪在地上,一个劲地对着一地瓦片鸡啄米似的磕头,直把头磕出殷红的血。
狗剩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深的坑,把水罐悄悄地埋了。
鸡肉没有吃到,只得再用地瓜充饥。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狗剩扛起红缨枪就往外走,走到街上突然感到有些内急,就跑到街边的一个茅房里解手,顺手把红缨枪立在茅房的墙上。
梅朵放学回来,看到狗剩的红缨枪立在茅房墙上,就过去拿起来扛在自己的肩上,学着狗剩的样子在街上走。
狗剩从茅房出来,不见了红缨枪,就四下里找,见梅朵扛着,就跑过来要:“梅朵,把枪还给我。”
“不给。”梅朵把头一歪,把嘴一撅,“这是我捡的,为什么给你?”
狗剩说:“这是我的武器,是保护集体财产用的。你要是不给我,集体丢了东西你赔啊?”
梅朵说:“给你也行,你得学三声狗叫。学得像,我就给你!”
“真的?”
“骗你小狗。”
狗剩就学了三声狗叫。
梅朵说:“不行!这样不算。你得像狗一样趴到地上叫!”
狗剩就趴到地上,又汪汪汪地叫了三声。“还我吧!”狗剩把手伸了过来。
“我说过了。骗你小狗。就是骗你这个小狗。”梅朵指着狗剩一字一顿地说。
狗剩一听上了当,爬起来上去就要抢,梅朵扛着红缨枪就跑。
梅朵在前边跑,狗剩在后面追。眼看就要追上了,梅朵就把红缨枪扔了。这时,一个男孩跑过来,拣起红缨枪就跑,狗剩放过梅朵,去追男孩。男孩跑到玉带河边站住,对狗剩说:“过来,给你的枪!”
狗剩走过去,想接过他的红缨枪,没想到那个男孩一下子把红缨枪扔到了河里。
狗剩站在河边一看,红缨枪就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漂着。他就拉着河边的一根树枝试图把红缨枪捞上来。他的手离红缨枪三拃、两拃、一拃,眼看就要够到了,树枝突然断了,狗剩一下子掉进了河里。红缨枪受到水浪的冲击,向河里漂了几米。狗剩是有些水性的,他没有忙着上岸,而是努力去够他的红缨枪。
冬天的水面结着似有似无的一层冰,水里的寒气像一个吸血鬼拼命地吸取着狗剩身上不多的热量。眼看就要够到他的红缨枪了,可是他的腿似乎不能打弯了,他感到水下有人在狠力地拽他,而红缨枪和他的手指始终若即若离。红缨枪像一个女鬼招引着他,始终给他希望,可就是抓不到。这时,狗剩只感到透心的冷,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他想喊救命,张张嘴,但没有发出声来。河水在他面前消失了,天空在他眼前消失了,大脑一片黑暗。他听到呼呼的风声,听到隆隆的雷声,听到鬼在哭狼在嚎,他的身体向无底的深渊坠去。
狗剩在惊恐万状中看到他的老婆吕凤英、老丈人吕瑞清从眼前走过。他想叫住他们,但就是发不出声音,眼看着父女俩拉着四弦越走越远。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了大油袖。大油袖披头散发,头上滴着淋漓的血,舌头长长地吊在嘴外,活像一个女鬼。狗剩惊恐地看着大油袖,不敢发声。大油袖眼一斜,却看到了狗剩,于是她便龇着獠牙、伸着长爪向他扑来。狗剩吓得魂飞魄散。正在这危急关头,梅花出现了,像观音菩萨,左手拿一个玉瓶、右手拿一个柳枝,看到大油袖,用柳枝对着大油袖轻轻一洒,大油袖就不见了。梅花脸润红润红的,仿佛三月的桃花;眼睛亮亮的,仿佛冬夜里的星星;嘴角挂着微笑,像秋天里的阳光。在梅花面前,狗剩没有恐惧、没有欲望、没有邪念,所有的细胞在分解,所有的理念在消融,所有的善恶在融化,融入了风,融入了光,融入了空气,他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天蓝蓝,水清清,天地一片纯净。
连绵的冬雨过后,万里长空如洗。人们的心情也像这晴空一样晴朗了起来。太阳红红的光芒像是女孩子的手指,温柔地抚摸着远山近树,像是给万物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更为奇特的是,在透明的瓦蓝色的天空中,竟出现了一道绚烂的彩虹。
世界显得格外的美丽,梅广元家的小院里更显出一种安详和温馨。梅广元把旧被套铺在炕席子上,用一张巨大的棉弓弹棉套。在有节奏的敲打下,棉弓发出清脆的乐声。
薛蓉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把白色的手套破开,缠成一个个的线球,梅花坐在小凳子上织毛衣,梅蕾在一个蚂蚁窝边用窝头一点点地喂蚂蚁,梅朵则站在院中一棵椿树下把上上下下的蚂蚁一个个消灭。梅艳躺在一个柳条筐里,安静得像一只小猫咪,把手指含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咂着。那只母羊又怀了羔,肚子圆圆的,吃着晒好的干草,不时咩咩地叫几声。圈中的猪安静地躺着,肚子对着阳光,几只苟延残喘的苍蝇落在肚皮上,猪肚皮时而显出一丝丝的波动。树上的鸟也兴奋起来,声声鸟鸣,如珠落玉盘,此起彼伏,给人春天的感觉。
喂过了蚂蚁,梅蕾走过来,蹲到梅花身边,问:“姐,给谁的毛衣?”
梅花说:“姐姐就不告诉你。”
梅朵一听,扭过头来:“笨丫头,还用问,给你将来的姐夫织的。”
梅蕾说:“谁是将来的姐夫?”
梅朵大声说:“赵诗文——”
梅花白了一眼梅朵:“叫什么?现在还不是呢!”
梅朵说:“正因为现在还不是,所以我说将来嘛!”
大家的说话声惊动了梅艳,她啊啊地叫了起来,似乎也想参与到大家的谈话中。薛蓉摇摇柳条筐,唱着儿歌逗梅艳:“小蚂蚱,草里藏,饿了就吃路旁草,渴了就喝露水浆。七月八月还较好,九月十月下了霜。伸手抓着谷草草,不多一时见阎王。”
梅朵跑过来:“娘,你教我唱。”
梅蕾也跟着说:“娘,您教一个吧!”
梅花说:“过来,我教你们唱一个《苦命的女人》。”
大队里有个小姑娘,
起了个名字叫海棠。
自从海棠出了嫁,
天天晚上哭一场。
大锅添上一筲水,
小锅添上水一瓢。
叫声妹妹你烧锅,
我到堂房问婆婆。
问得头声她不听,
问得二声装睡着。
海棠要问第三声,
起来骂你个小老婆。
人家坐着咱站着,
人家吃饭咱看着。
人家吃的白馍馍,
让咱吃的糠窝窝。
咬一口,糠沙沙,
脖子一勒死了吧。
柏木板,杨木料,
问问娘家要不要,
闺女嫁了人家的人,
是死是活人家的魂。
梳梳头,洗洗脸,
一根绳子梁上拴。
小姑子说:
针线筐子是我的,
涮锅下灶咱娘的,
什么活难为得你?
梅蕾掉了泪,说:“海棠的命咋这么苦?”
梅朵说:“要是他们吃白馍馍,叫我吃黑窝窝,我就把他们家的锅给砸了。”
薛蓉一听,扑哧笑了:“谁家要摊上梅朵这小姑奶奶就倒了霉了。”
说到命苦,梅花突然想起梅琴来。她的命最苦了。她去哪里了,哪里才是她的安身之处?想到这里,梅花的泪水就要落下来,她抬起头,看看天,她看到了一只孤雁在努力地飞。
“啪”,一声枪响,孤雁在空中翻了几个滚,就直落下来。梅花泪水终于没有止住,随着孤雁滚下来。
张卫东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小梅庄的大队革委会主任。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揪斗梅庄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梅广慧。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张卫东把公社的头头都请来了,他自行宣读了梅广慧保护地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罪状。梅广慧站在梅尚德曾多次站过的地方,低垂着头,因为腿有点不一样长,肩一个高一个低,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宣布完罪状,张卫东蹦上碾盘,一脚就把梅广慧踢了下来。梅广慧没有准备,头直接撞到地面,血流了一地。张二秃子疯一样跑过来,箭一般蹿到碾盘上,一头把张卫东撞下去。还没等张卫东明白怎么回事,张二秃子撞在了碾盘上。
寒冷的北风像是一群野狼从北往南扑了过来,所到之处,龇牙咧嘴地抖着威风。草木吓得瑟瑟发抖,枯枝败叶惊得晕头转向地漫天飞舞。一群麻雀失魂似的呜叫着,一起一落乱飞。黄色的沙雾在风的作用下像垂天垂地的帷幕,把天空罩个严严实实。
天地一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