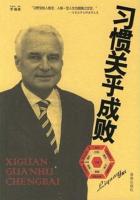(二)托多罗夫的结构主义诗学
兹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39—)1965年将俄国形式派著作翻译成法语,以《文学理论》为名发表,他结合俄国形式主义进行的研究对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以及叙述学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
诗学是托多罗夫进行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方法之一,他的《如何阅读》,将文学研究与批评方法分成三种:投射、评论和诗学。“投射”是批评家通过文学作品对作者、社会或对他感兴趣的其他某个批评对象进行研究的一种阅读方法;“评论”是对投射的补充。投射竭力贯穿作品并超越作品,评论则自始至终在作品内部进行;评论的极限是释义——释义的终极则是作品本身的重复。“诗学”是探寻特定作品中所体现的一般原则。这些都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完成的,而阅读与这些方法的关系既相辅相成,又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托多罗夫认为,阅读是一种有系统的评论,而评论本身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至于阅读与诗学的关系,托多罗夫认为诗学为阅读提供了理论,但阅读的目的并不在于在个别作品中寻求普遍的概念以证明诗学的正确性,其目的在于作品本身的内在联系。所以,诗学在他看来是一种普遍、一般的文学研究方法,是寻找作品中体现出的一般原则的研究理路。他的叙述学研究以及后期的文化研究都属于诗学研究的范畴。
托多罗夫的《诗学》是《何谓结构主义》丛书中的一部,他以简练清晰的文笔系统地阐述了结构主义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托多罗夫而言,建立新的诗学意味着对文学的功能和意义的再认识。他将历史上对文学的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归结为两种:“第一种是将文学作品本身视为认识的对象;第二种则认为每一部个别作品都是某种抽象结构的具体表现。”第一种认识是对作品而且仅仅只是对作品本身的解释,作品只是解释的客体。这种做法的目的只在于寻找出作品的意义,但却很难理解作品的全部意义。第二种认识范围比第一种广,它不再是描述一部部具体的作品,而是在分析作品中寻找创作的总原则。这是现代诗学研究方法,托多罗夫认为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态度,也就是说,诗学不在于说出个别作品的意义,而在于辨认出作品创作的法则。当然,诗学不限于研究诗歌作品,而是指所有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学。正如托多罗夫所言:“诗学的客体并不是经验事实的总体(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抽象的结构(文学)。”托多罗夫将诗学归属到结构主义的范畴,认为诗学研究是把一种科学的观点引入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引入本身就属于结构范畴。另外,他还考察了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诗学与语言学的联系主要是深受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影响;与文学史的关系表现在文学的演变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层次;与美学的关系表现在只有先对作品进行诗学研究,然后才能探讨美学价值。这种关于文学作品价值的论述,托多罗夫认为是通过阅读加以实现的,阅读既展示作品又评价作品。通过阅读,诗学与美学建立了联系。托多罗夫在专门研究诗学的《诗学》一书中,强调了诗学的对象是自身的方法,既肯定了诗学作为一种文学科学的建设性作用,也将诗学本身看成一种开放性的学科,即托多罗夫所言:“文学是一种中介,一种语言,而诗学用它来表现自己。”
既然诗学是一种结构研究,那么,叙事学就是在结构范畴中对文学作品的科学认识。托多罗夫的叙述学,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实际上,叙述学是对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专门研究,它是伴随结构主义的兴起而形成的一种文学理论,主要是在对神话、民间故事以及后来的小说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叙述学是法国结构主义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因而也显示了种种不同。托多罗夫的叙述学偏重于语法方面,他的《叙事语法》对薄伽丘《十日谈》中的四篇故事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提出了叙事语法理论。他认为人类有着共同的经验基础,所有的信息系统都受这种经验基础的影响。“不仅一切语言,而且所有的指示系统都对应着同一种语法。这语法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不仅因为它决定着世上一切语言,而且因为它和世界本身的结构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人类语言的这种普遍语法的存在,才有语言的被理解。语言总是因一定的方式而存在,这种存在促进了人类的认识的深入与延续。因为人类对语法的深入了解,所以语言的语法也是叙事语法研究的模式。托多罗夫把叙事作品按照类似语言的结构分成三个层面进行讨论:“语义学(semantic aspect)”、“句法(syntactical aspect)”和“动词体(verbal aspect)”。托多罗夫侧重于“语法”层面,他把构成作品深层组织的两个单位称为“命题”(propositions)和“序列”(sequences)。前者是句法的基本单位,是深层的叙事句,是由人物(名词)和特征(形容词)或行动(动词)组合而成,表现为状态(states)、特质(properties)与身份(conditions/status);后者是相关命题系列或叙事句的汇集与排列,它的结构由时间关系、逻辑关系、空间关系来决定的。比如在命题中,动词通常代表故事中人物的“行动”或“活动”。托多罗夫将《十日谈》中的人物行为归纳成三个基本动词:更动、触犯、惩罚。另外还将它们的属性用符号进行了代替,比如以Y表示受害者,以X表示侵害者,于是他将《十日谈》中的四个故事(第一天的第四个,第九天的第二个,第七天的第二个,第七天的第一个)用这些符号进行了演示:
X犯法Y应该惩罚XX试图逃避惩罚Y犯了法
Y相信X没有犯法Y没惩罚X
这其中,“”符号表示两种活动之间限定继承的关系,X、Y表示专有名词,分别作主语或宾语,犯法、逃避、惩罚等是表示行为的谓语。托多罗夫总结道:“通过对《十日谈》的各个故事的研究,我们发现所有故事只归结为两大类。第一类可以称为‘避免惩罚’型。……在这类故事中,有一个完整的过渡,即平衡——不平衡——平衡。而不平衡总是由该受惩罚的违背法规的行为引起的。第二类可叫‘转变型’,……这类故事只有第二部分,即从不平衡到最终的平衡。另外,这个不平衡并不是某个特殊的行动引起的(一个动词),而是由人物的品性决定的(一个形容词)。”所以托多罗夫并不是对作品进行文本的解释,而是从结构认识,即要辨认出作品,特别是通过叙事作品的语法,辨认出结构来。只有先对结构进行认识才能进一步理解作品,在他看来叙述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的普遍规律,也就是作品的叙事结构。
托多罗夫的叙述学主要借鉴了结构主义的观点,同时深受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他的叙事学集中于叙事时间、叙事体态以及叙事的语式,如用转瞬即逝表示叙事时间的过去,故事中的“他”和叙事话语中的“我”的叙事体态是否一致,以及表现为叙述者陈述方式的叙事语式等都是叙述学的重要观点。托多罗夫对叙述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是符合历史分析的方法的,他是法国率先通过结构方法研究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学者,紧随他之后的热奈特坚持了他的观点。托多罗夫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进行结构分析,热奈特的不同在于对叙事性作品的范围进行了限制,比如他认为大众传媒就不属叙事性文学的研究。托多罗夫的结构主义诗学给20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他唯结构而研究文学的方法也反映了他的局限。
(三)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美学家、符号学家。他的诗学思想是从探讨写作开始的。以往时代的作家们都认为写作是一种表达,一种交流的工具,而巴特认为写作是独立自主的。在成名作《写作的零度》里,巴特写道:“一切写作都呈现出被言说的语言所没有的封闭性。写作绝不是交流的工具,它也不是一条只有语言的意图性在其上来来去去的敞开大道。……写作是一种硬化的语言,它独立自主,从来也未想赋予它自己的延存以一系列变动的近似态,而是通过其记号的同一性和阴影部分,强行表现出一种在被说出以前已被构成的言语形象。……写作永远根植于语言之外的地方,它像一粒种子而不像一条直线似的发展,它表现出一种本质和一种隐秘力量的威胁,它是一种反交流,它使人们不知所措。因此在一切写作中我们都发现一种既是语言又是强制性的对象的含混性。”巴特提出了“零度”介入写作的观点,他所谓的零度即零度风格的写作,体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这正是结构主义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观点。其实,他的零度相当于一种中性的写作,比如说创作介乎两者的折中之处。当然,巴特也不是一味地去除作者的创作主体地位,他同时也否定了写作的“零度”,认为创作须凭借一定的言语(parole)来表达,借助一定的文体形式(风格)加以组织,作者的创作正是受到言语和文体风格两个维度制约的,言语和风格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一旦作者以零度介入写作,并不意味着作品的支离破碎,一俟作品形成,本身就是一种结构的生成。巴特运用结构主义的观点解释道:“风格其实是一种发生学的现象,是一种性情的蜕变。因此,风格的泛音回荡于深处;而言语却有一个水平的结构,它的奥秘和字词存于同一水平上,言语所隐藏的东西为言语流的绵延本身所揭示。在言语中一切都被呈现,都注定要立即加以耗用,而语词、沉默的间隙以及二者的运动都被抛入一种废弃的意义之中,后者则是一种不落痕迹、从不迟误的转换过程。反之,风格只有一个垂直面,它浸入个人的封闭的回忆之中,它从某种对事物的经验中积成了它的密度。风格永远只是隐喻,即作者的文学意向和躯体结构之间的一种等阶关系(应当记住,结构是一种时延的沉积)。”因此,写作不是个人的行为,应该是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特定的表达方式,是结构的完形,高于个别元素。巴特的观点使得作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写作不再是作者的心理释放,而是与多种因素的结合。巴特从多种文体形式进行了论述,比如古典的散文和诗,他认为,古典的散文和诗尽管存在量值的区别,但它们仍然是语言的表达,不会损害语言的统一性,反映了精神的永恒范畴。它们使字词尽可能抽象,以便表达关系。它是一种表达的艺术,而非创新的艺术。现代诗也不是关系引领着字词,字词本身就是一切。
巴特的《写作的零度》主要是为了体现他的符号学思想,他的这篇成名作就选自《符号学原理》一书。实际上,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早在《神话学》一书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符号学是一种形式科学,因为它研究意指而撇开其内容。”巴特在对神话进行研究时认为,神话是一种言语,是一种传播的系统,一种信息,一种形式,因而不能是一种客体、概念或观念。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他按照结构语言学将符号学原理分成四类:语言与言语,所指与能指,系统和组合段,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前两类显然深受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巴特认为第三类是语言的两根轴,他专门写过分析服装的《时装系统》,将服装分为书写的服装、被拍摄出来的服装以及穿在身上的服装,说明符号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意指。由于西方符号学的流派众多,观点不一,因而很难断定巴特的抑或其他的符号学理论的合理性。但是巴特从结构语言学发展而来的符号学理论,可谓符号学理论的源头,以后的符号学理论大多建立在他的基础之上。
叙事研究是结构主义的传统,巴特的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是叙述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结构主义的标志。1966年他发表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点出发,在托多罗夫等的基础上,为叙事理论开辟了新的方向。与前人相比,巴特的叙事理论更具开创性。他认为叙事具有普遍性,形式、数量和种类繁多。如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画面、手势等形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小说、诗、戏剧、绘画、电影、社会杂闻等都有叙事,所以研究叙事是诗学的重要内容,叙事理论是诗学的重要方面。既然叙事是这样的繁杂,那么为叙事作品提供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必要的。他借鉴语言学的层次描述法,将叙事作品分成:功能层,研究基本的叙述单位及其相互关系;行动层,研究人物的分类;叙述层,研究叙述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巴特认为它们共同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原则上,“这三个层次是按照逐渐归并的方式互相连接起来的:一种功能只有当它在一个行动元的全部行为中占有地位时才具有意义;而这一行为本身又因为交给一个自身具有代码的话语、得到叙述才获得最终意义。”功能是叙事最小的或基本的单位,也是讨论叙事文体的最基本的方面。巴特一反通常的做法(比如以往对神话中神话素的界定),对功能作了更为严密的描述,认为艺术品里的所有因素都有某种作用,都有存在的理由,尽管这些因素发生作用的方式和角度可能不同。这样,不同因素的组合规则就是功能句法方面的问题,所有的功能问题就组合成功能系列,它们是功能层的重要内容。行动层主要处理人物关系的结构模式,巴特认为他之前的结构主义对叙事作品人物的分类问题尚未解决或存在欠缺,更远的比如亚里士多德重视情节而轻视人物,托多罗夫等人尽管重视人物,但偏向于人物间关系的研究,都是不充分的。巴特认为应该从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人物。当然对人物的研究主要是在叙述层,这是专门研究叙述人、作者、读者间关系的层次,比如叙事作品中的主角、行为者、叙述人、作者等是叙述的同一主体还是全不相同?巴特认为,在叙事作品中,说话的人未必就是写作的人,而写作的人又不是存在的人。同样,读者的地位也是极为重要的,读者符号有时候比叙述者符号更为复杂。这点已经接近现代读者反应理论的观点,是巴特的先见先识。当然巴特对作品人物的分类还是建立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他认为语法上的人称分类与小说中的人物分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巴特的叙事理论可谓周详,但他忽视了叙事体式的各种各样的结构关系,因而很难全面分析文学现象,他的局限是将复杂的文学现象仅仅归为语言学研究。当然这也是他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标志,他的关于作品完成、作者消失的观点直接成了后结构主义的圭臬。
结构主义曾经风靡一时,但是到巴特走向了尽头。轰轰烈烈的结构主义运动为20世纪的诗学提供过丰富的养料,可以说,没有结构主义影响,20世纪诗学将延缓前进的步伐,尽管我们现在感觉到了它的许多不足。结构主义诗学开创了一个诗学的新时代,它为现代诗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