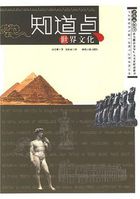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境界中。是什么境界?自己知道。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间,都有消息。若再问,要那个境界有什么用?答曰,一无所用。
坐在湖边,看一个早在此处的老者垂钓。我不说话,因为他丝毫没有和我聊天的意思,就这么半天过去了。他收拾钓竿和鱼篓,鱼篓是空的。
我很同情地问:“一条也没钓到?”
他收拾好,离开时才回答:“钓鱼不是为了鱼。”说完就自顾自地走了。
就因为老头的这句回答,我在他身后大声问:“老先生是干什么的?”他头也没回说:“钓鱼的。”一无所得却乐在其中,难得。世风浮躁,这样的人不多了。
钓鱼不为鱼,这道理我当然知道。
还有垂钓不为鱼,而别有用心的。历史上名气最大的,大概是西周的姜太公了。此人是个野心家,他要钓的是商纣王的天下。他不是等鱼上钩,而是在等周文王上钩。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作秀。
真的不为钓鱼,一叶扁舟一钓竿,风流潇洒,名满天下的,当数大唐年间的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不过,别错会了意。以为他真的冒着漫天大雪在垂钓。
还有人读此诗,说柳宗元在玩情调。要说玩情调,今天的人谁玩得过他?有人说他在发牢骚。因为他想得到的没有得到,心里不平衡。其实不然。
同是大唐年间,有个大名鼎鼎的禅宗居士庞蕴。这位庞居士,散尽家产,躬耕垅亩,粗茶淡饭,参禅悟道,常与大禅师们谈禅说佛。禅僧们都很尊敬他,向他请教。
一年冬季,他去拜访一位大禅师后,一个禅僧送他出山门。恰是大雪漫天,千山素洁。
庞蕴站在山门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送他出门的禅僧问:“落在何处?”
这庞居士转身给了他一耳光问:“落在何处?”
那禅僧忽然有悟。
那一巴掌意在截断禅僧思路,不再漫无边际的去想“落在何处”。无处可落,只落感受耳光之处。不是巴掌不是脸,心在感受。雪只落在心里。
十方世界都在心中,你说大雪还能落在何处?
柳老先生蓑衣斗笠,独坐船头,溶化在漫天大雪,一江寒流中。“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表相是说环境,实相直指人心,垂钓者清净的自性真心。“独钓寒江雪”,雪可以钓吗?当然不是钓雪。这一句“独钓”两个字大有讲究。这里的“独”不是“独自”的“独”,而是“特立独行”的“独”。钓者,追求也。“独钓”就是只追求漫无边际,晶莹洁白,一尘不染的真心。禅宗意旨,明心见性。禅者所作所为,终其一生,只为此事,别无所求。
不说什么禅意,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冬季早起,拉开窗帘一看,昨夜下雪了。极目所见,一片明亮雪白,刹那间,心也跟着明亮雪白起来。
有唐一代,柳宗元算得上是个禅境甚深的诗人。否则,禅宗六祖惠能的徒孙们,也不会请他为六祖写碑文了。他的禅诗很棒,不在“诗佛”王维之下。王维年长七十三岁,是他爷爷或太公辈,撰写六祖碑文第一人。王维成了“诗佛”,当然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诗佛”了。
一无所得,就是有所得,精神层面的所得。是无染的心境或清澈的心源。
有朋友说:“如今是个很实际的社会,或者说是个很实用的社会,你说的那个境界有什么用?”这一问,很实际,很有分量。还真说不出有什么实用价值。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倘若问孔子,早上学了晚上就死,学它干吗?夫子只有目瞪口呆。
心源如流,见诸文字即为诗文。清浊高下自现,这就是“文如其人”的本意。
一张白纸才能画最新最美的画,才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污秽不堪的一张纸,没法写,也没法画。写画出来,也是污秽。
南朝陈后主陈叔宝,是个天才诗人,文学修养极高但人格极俗,淫糜奢侈,没什么佳作传世。一首《玉树后庭花》,仅因是亡国昏君的代表作,才有不少人知道。许多人还是从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略有所闻。
全诗如下:
丽宇芳林对高阁,
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
出帏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
玉树流光照后庭。
技巧很高,诗句雅丽,诗格俗不可耐。所谓诗格,也就是人格境界,人格境界如此,诗文只能如此。
诗文如此,做人也情同此理。你能指望内心邪恶的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吗?
读柳宗元《江雪》,如见高洁其人。
看似一无所得,一无所得几有所得。得到的是什么?谁也看不见,得者也说不出。但肯定不是一条鱼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实相无相。柳宗元所钓到的那个“实相”,不可以言辞诉说,也无法用色彩绘画。
一无所获的实相,就是原本清净的真心。
华亭船子和尚,有一首月夜垂钓的诗:
千尺丝纶直下垂,
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深水寒鱼不食,
满船空载月明归。
和尚当然不可能去钓鱼,他在钓清纯的月色。净若虚空的内心世界,满是皎洁的月光。
再拖个古人出来热闹一下——
《世说新语》载,东晋王徽之(书圣王羲之第五子)弃官隐居绍兴,雪夜读书,突然思念隐居剡溪的好友戴逵,极想一见。便雪夜乘小船溯溪而上,去拜访戴逵。天亮时,戴逵院墙已遥遥在望,王徽之却掉转船头回去了。随从问:“你怎么不见面就回去呢?”王徽之答:“乘兴而行,兴尽而归,何必见戴!”
一夜风雪,一叶孤舟,同样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雪夜所得,深心自知。是否和柳宗元的《江雪》殊途同归,不得而知。只觉得到此为止最好,若弃舟登门拜访戴逵,反成涂染。“何必见戴”,恰是禅境。
《江雪》是诗,“雪夜访戴”,也可说是一幅《雪夜行舟图》,实际意旨,都在诗画之外。只能以心感受,无法以色相呈现。
文学艺术所追求的,也就是这个。说是“表现”,其实什么也表现不了。能感受所表现的“实相”的,不是作者,而是读者。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境界中。是什么境界?自己知道。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间,都有消息。
若再有人问,要那个境界有什么用?
答曰,一无所用。无用之用,是为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