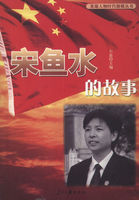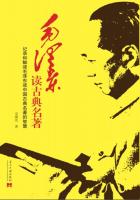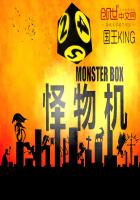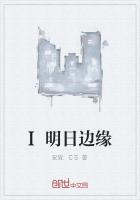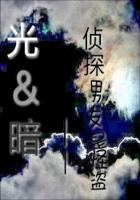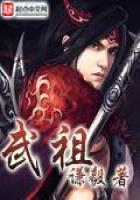因此,海波对自己和同仁们有两点要求:一是倡导当作家型的编辑,二是在编辑过程中要舍得“卖血卖骨头”。对于前者,海波身体力行,1982年即以短篇小说《母亲与遗像》夺得全国奖,是新军旅作家中的先锋人物,作家的名头大于编辑(其实此一特点并非海波独有,实乃《昆仑》编辑部的集体传统,譬如袁厚春、张俊南之于报告文学;程步涛、李晓桦之于诗歌;黄柯、叶鹏之于评论等等)。对于后者,海波是真舍得,只要你需要,他就舍得给,从思想到故事到人物直至人物对话,他都为你如琢如磨出谋划策,直至最后操刀上阵越俎代庖,甚至把你的东西改得面目全非,整个儿散发出一股“海味”。我就亲耳听海波本人说过这样的事情:作者看到清样后给编辑部打电话,拒绝署上自己的名字而要求改署海波的名字,因为他不认识这篇小说,那里面已经没有几句自己的话了——对于这种情况,我的态度比较复杂。坦率地说,过于强加作者的编辑作风我是不大赞成的,《昆仑》小说的过于“海波化”也未见得是一件好事。它对刊物风格的多样化可能是一种限制,而对作者的生长也有削足适履之嫌疑。如果要推举一位同仁刊物的主编,我首选海波;否则的话,我真心希望他能更加宽容、兼容和包容一些。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一个编辑如此认真、负责、投入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把每一篇作品都视如己出,愿意倾其所有帮助其提高与完善,这样一种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和甘于为人作嫁的职业道德,让我们除了钦佩之外,还能够再说什么呢?
事实上,海渡的两点自我要求也是自相矛盾的,“卖血卖骨头”——卖生活,卖情节、卖细节、卖点子、卖构思,什么都卖完了,那你自己还写什么呢?还怎么继续当作家呢?海波在自己创作的巅峰期戛然而止,以《黑革》作为小说的封刀之作金盆洗手,是否与此有关?
昨天,我为少了一个海波这样的优秀小说家而惋惜;今天,我为海波这样敬业的编辑家越来越少而怅然。
一个座谈会和一组文章
其实,上面说了这么多海波的“事迹”,大都是我读来的和听来的,没有一件是我亲历。确实,虽然对海波认识很早闻名更早,但由于彼此各色的个性再加之没有适当的机缘,所以,尽管我对他以“诤言”著称的鲜明风格甚为欣赏,也时常在一些会议上为他犀利到位甚至“越位”的“辩锋”暗中称快,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作过一次个人的沟通,彼此间始终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消除这种距离乃应了那句老话,叫“不打不相识”。关于那次由“打”而“识”的始末,前后迁延两年时间,从唇枪舌剑到化剑为犁,其间充满了精彩的戏剧性,充分反映了双方的典型性格,有机会我要单独撰文一篇以为纪念。在此暂且割爱。就在我们握手言和和相互沟通之后不久,我们之间“亲历”了一次“合作”。因为这次合作不仅关涉到海波个人,更关涉到《昆仑》,关涉到《昆仑》在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姿态,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略记于此。
1992年秋,我先应邀去广东沿海讲学并参观,再折回到武汉参加一个当代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最后又和王朔一行去了青岛。此番一月余的行程,使我大开眼界大受震动,到处不乏对商风商潮的惊呼,对严肃文学的哀叹,对快餐文化的暧昧态度乃至“狐狸心理”。有感于此,回京后我赶写了《1993:卷入市场以后的文学流变》等文章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和《作家报》。对文学现状进行了描述与分析,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但也坚定地认为:“滔滔商海中,文学之舟将受到猛烈地摇撼乃至摔打,但决不可能被彻底颠覆。浪高一尺,船高一丈,真正的文学之舟永不沉没,它将载着人类的希望与追求,永远驶向精神家园的彼岸。”
很快就接到了海波的声援电话,并说编辑部同仁近期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如何抗击商潮,使军旅作家振作起来,顽强坚持严肃的理想的军事文学写作。具体措施就是想先策划一个讨论会,后续举动相机酌定。考虑到当时传媒的声音纷纭多元,上面的导向还不甚明了,知识界的“人文精神”讨论亦尚未展开,在这种没有“参数”的情况下,一家军队刊物的“单独行动”是需要谨慎的。因此,关于会议议题的界定、会议规模和与会人员的范围等技术问题,我们又进行了多次电话磋商,等到编辑部最后确定方案,已经到五月份了。我翻阅日记查到:《昆仑》“关于商潮中的军事文学讨论会”于1993年5月6日上午在北太平庄书库会议室召开,有驻京部队评论家和编辑部全体约十余人与会。首先由程步涛和海波阐明讨论会宗旨和编辑部立场,继而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热烈讨论。我因为此前不久刚在文学系针对“一把剪刀闹革命”的“畅销书现象”作过反对“下海”的专题讲座,在讨论会上也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发言,颇为编辑部同志所认同。此后不久又接海波电话,说编辑部最后决定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准备组织几篇文章一起发表,希望我将讨论会发言尽快整理成文章。由于我当时手头正在进行《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收尾工作,略微延宕了一些时日。转过手来完成海波的任务,已经是六月底七月初了,记得最后是赶了一个通宵才完稿,次日一早即通知殷实来把稿子取走了。这就是那篇《我为什么反对“下海”》。
文章以集束形式在1993年第5期《昆仑》的首要位置刊出,这种做法在一家以发表作品为主的大型期刊上也是罕见的。头题是由当时的编辑部主任程步涛亲自撰写的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使命的张扬与责任的再树》,文章在严厉抨击了商风商潮对作家的侵蚀之后,断言“今天的这种拜金主义导致的价值观念错位、道德水准下降,必将给新世纪的交响带来不谐和的噪音”,因此,“在这种时候,作家的使命与责任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加以强调。以呼唤人类崇高圣洁的灵魂,以鼓舞人类为进步为理想而斗争的意志,以指出人类的尊严、正义与光明”。文章最后大声疾呼:“真正致力文学追求,甘愿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个人生存的作家们,高举起自己的旗帜来!”
殿后文章是殷实的《结束,或者开始》,我的文章居中。我的文章副题是“关于当前文人、文学、军旅文学的答问”。实际上也是一次自问。在文章的结束,我借用已故著名老评论家冯牧先生针对文人“下海”提出的一个口号“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来忠告全军作家——“中国的军旅文学作家们究竟是‘下海’还是‘登山’,这将从根本上决定未来军旅文学的命运:跌落还是起飞”。
刊物出来后,在军队文坛激起一些反响。9月份,中央反对拜金主义的力度加大,“导向”已经鲜明。而且,由同年第6期《上海文学》的一篇批评家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所引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逸出了文学圈,开始蔓延波及到整个知识界,一片群情汹汹众志成城之态势。相形之下,《昆仑》这一组文章所包含的锋芒和锐气反而被淡化被稀释乃至被淹没了。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在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一度“失语”、文学理想似曾“失落”的特定时期,《昆仑》作为军事文学的重镇,它并没有犹豫更没有沉默,它是敏锐而坚定的,果决而勇敢的,它及时地发出了正义的呼喊,有力地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一群人和三代人
我们可以把《使命的张扬和责任的再树》看成是《昆仑》抗击商潮的一篇战斗檄文,也可以读作“昆仑人”一次集体心声的夫子自道或精神写照。前面所说的海渡的个人风格也许不能代表“昆仑人”的全体,但他强烈执著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却与全体“昆仑人”如出一辙,海波仅仅是其中的一分子。在今天纪念《昆仑》创刊百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个群体,这就是曾经在《昆仑》工作过和至今仍然在《昆仑》工作的全体“昆仑人”。他们是——
张忠、凌行正、李大我、袁厚春、程步涛、海波、黄柯、佘开国、张俊南、冯抗胜、刘成华、罗来勇、江宛柳、李晓桦、叶鹏、郭米克、丁临一、殷实、张鹰、余戈……
这其中,有的人已经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更多的人却是因为工作需要先后调离到了新的岗位。但是不管人员如何变动,一种“昆仑人”的精神却有如薪尽火传,程程相递。这是一种为繁荣军事文学而披荆斩棘的开路精神,这是一群为部队作家尤其是青年作者攀登文学“昆仑”而甘于奉献的铺路人。
屈指细数,《昆仑》百期十五年,在这个阵地上坚持最久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海波,他从1981年筹备创刊到1994年调离,前后达十四年;另一个是张俊南,他从1982年加盟《昆仑》直到如今,中间扣除两年在军艺文学系读书,前后也是十四年。他们是一种巧合(时间),两种典型——如果说《昆仑》长期以来以中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为两大“支柱产业”的话,那么,海波就是小说类的“掌门”,而张俊南则是报告文学类的“领军”。对于海波的功绩,我们已在前面作过概略的评述,在此,我们想把张俊南作为“昆仑人”的又一个代表和另一种类型再作简要介绍。
说来惭愧,我和俊南虽然在首届军艺文学系同学两年,但却对他知之甚少。只是近年来随着和他的作者(主要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接触增多,才逐渐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尤其是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而重新查找《昆仑》目录,于不经意间偶然发现,多年来,俊南以基本放弃自己的创作为代价,在不哼不哈之中,为扶植和荐举部队报告文学的新人新作方面已做出了一番显赫的成绩。自1987年他接手主抓《昆仑》的报告文学以来,大部分精品力作都是被他“抓”出来的,比如:《南京大屠杀》(徐志耕),《毛泽东以后的岁月》(王立新),《江西苏区悲喜录》(何晓鲁),《侨乡步兵师》、《大势》(中夙),《跨越苍茫》(咏慷),《瘦虎雄风》(杜守林),《余秋里与中国石油》(陈道阔),《星辉》(张嵩山),《中华之门》(李荃),以及王苏红、王玉彬的历史题材系列作品等等。
为什么不用“编”、“编发”、“编辑”而单用一个“抓”字呢?因为难就难在一个“抓”字,高也高在一个“抓”字,特点全在于一个“抓”宇。它与《昆仑》的小说不同,小说多产自于笔会,通常是(主要指80年代)以集群方式运作;而报告文学则基本与笔会无涉,主要是以编辑和作者“一对一”的形式进行“跑单帮”。先是编辑从大量的信息或少量的来稿中“抓”准一个选题,然后“抓”来作者,再一块儿下去“抓”素材。俊南平均每年要陪三四个作者下去跑素材,每次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动辄跑遍大半个中国。在陪同采访过程中,一路帮助作者分析材料、清理思路、提炼主题、研究结构,待到将一部报告文学的整体框架乃至细部处理都“抓”出来之后,他这才回到编辑部去坐等“编辑”。说起来,最后的案头编辑工作只是这“抓”的过程中微不足道的尾声了。所以说,这如何不是“抓”呢?别的报告文学编辑怎么当的我不知道,反正张俊南是这么“抓”的。
我们的老同学李荃在《中华之门.后记》(昆仑出版社1990年1月版)中的一段话,道出了张俊南“抓”稿的三分情形二分艰苦和五分作用——“由于我不是一个有经验的采访者,他在《昆仑》编辑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陪同我采访了整整五十天,并得到了编辑部领导的支持。切磋。分析。选择采访对象。把握结构。在云南,我们一同乘车在路旁一侧就是万仞峭壁的山路上疾驰,汗透衣背;在广州,采访之初不顺时,他焦虑得一个喷嚏竟流出一大摊鲜红的鼻血……在文学系时,他是个沉默寡言、不显山露水的人,五十天的朝夕相处,我才知道这位同学的实力,他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位好编辑。在分手前的长谈中,他最后说:‘只有把边防放在历史、社会的大背景中,才能写出一种大气来!’他给我在后期的单独采访奠定了一个好的经验基础,他分别时留下的话也是我始终力图把握住的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