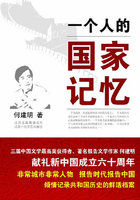音乐较之绘画,前者诉诸于听觉,形象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后者诉诸于视觉,形象是鲜明而确定的,前者似乎处于不可克服的劣势。然而,当我们充分考虑到人们的想象能力的时候,就会发现,正是音乐这种劣势,造成了它为绘画等姊妹艺术羡慕而又不可企及的优势。譬如一组琶音,你可以理解为春天走过窗前的一缕和风,又可以想象为夏夜月光下的一湾溪流;你闻到了初恋的花香,他看见了失恋的落叶……就像贝多芬说的,怎么理解都行。正是音乐形象的这种模糊和不确定性,带来了读者想象的丰富和多样性。所以,它最抽象,也就最形象。它比任何艺术都更宜于唤起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骚乱不宁的情绪,飘浮不定的思想,甚至最微妙的波动,最隐蔽的心情等等。有人把音乐称为艺术的皇冠,不是毫无道理的。
文学形象是通过语言中介来实现的,为大脑的第二信号系统所接受,它所提供的形象的不确定性,与音乐极其近似。一千个人看过《红楼梦》,就有一千个林黛玉,但一经改编为电影、戏剧,搬上银幕、舞台,也就随之取消了每个人的想象自由,无数个林黛玉统一为一个。人们不满足于电影、戏剧,反而觉得看小说还更过瘾,道理也就在此。心理活动愈趋细腻,想象能力更加丰富,审美趣味日益高雅的读者们,正在向我们的作家要求越来越多的共同创造的机遇。这种要求,必将对当代小说创作产生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再谈作家方面。
多年以来,我国文艺界流行一种简单理解,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现代派才表现自我,追求自我个性;而革命现实主义是排斥自我,反对自我个性的。殊不知,人正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的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己”。丹纳认为产生伟大作品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之一便是“自发的、独特的感情必须非常强烈,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海明威也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必须出自作家自己经过深化了的经验,出自他的知识,出自他的头脑,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我们只有积极鼓励作家们充分表现他们自我个性、主观情境的千差万别,才能形成风姿各异的艺术风格和流派。否则,充其量只能产生以地域、题材为特色的作家群体。这是因为人的心灵的差异比之生活现象的外部形式的差异,总是要丰富、复杂、无限得多。又由于作家主观色彩的差异,从同一事物中感受的印象也不尽相同,人们从中辨别出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个特征便刺激作家将事物重新思索、改造、再现。例如同样是日出,在古典主义写实画派的笔下,一般只有角度、色彩抑或笔触等的不同,而一当到了莫奈笔下,画的就完全是作家独特的印象了。又例如同样是白夜,俄罗斯巡回画派大师罗马丁由于长期观察,体验深刻,捕捉到一种静谧之后的生命的律动,画出了似昼似夜的幽光中的骚动与不安;而日本山水画大师东山魁夷的白夜,则是一个没有白夜的民族的人眼中的白夜,他突出一种新鲜感,一种诗的宁静。鲜红的太阳到了肖洛霍夫笔下的葛利高里眼中,竟然会变成黑色的太阳,更是令人不可思议而又过目难忘。独特的观念、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审美意趣,使真正的天才永远不落窠臼,另辟蹊径。
三
那么,什么叫小说写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要弄清什么是意,这就不能不涉及意境这个中国古典文论中的重要美学概念。诚然,今天人们解释意境,多沿用宋以来“情景交融”之说。其实,最早从理论上提出意境说的是庸人王昌龄,他认为“诗有三境”、“一曰物镜;二曰情境;三曰意境”。除物境以客观物象的加入而“得其形似”外,情境、意境都是与客观物境相对存在的心情境界。所以,意境并非一定如宋人所说的“情景交融”。近人王国维就正确地指出:“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如果取二王的说法,那么,这个意境与我们所说的意境就比较贴近了。简言之,所谓小说写意,就是用一枝饱蘸作家强烈情感和主观色彩的画笔,去描绘出一个经过作家心灵浸泡的脱胎于客观世界的艺术世界,描绘出这个世界中人的心理、意绪、潜意识等等。至于用什么手法写意,那就难以一言蔽之了。既有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象征,卡夫卡《变形记》的荒诞,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又有王蒙《布礼》、《蝴蝶》的时空错位,邓刚《迷人的海》的隐喻、暗示,张承志《北方的河》的情绪流贯、《黑骏马》的音乐结构。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写意的层次电是随着文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入与递进的。单说心理描写吧,昨天是间接表现,今天是直接解剖;昨天的心理描写置于情节结构之中,今天的情节结构置于心理结构之内。曹雪芹的心理描写精于通过对话、动作、气氛烘托来表现,托尔斯泰则巧于以细节暗示,而海明威则擅长用几乎与情节毫不相干的简短对话来传达。如海明威在著名短篇《白象似的群山》中,写一个男人带一位姑娘去做一次流产手术,可小说自始至终没提这件事。就写他俩在车站候车、喝酒,不断进行一些如下对话:
“它们看上去像一群白象”(指群山。笔者注)。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头象。”
“你是不会见过的。”
“我也许见过的,光凭你说我不会见过,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然而,我们正是通过整个氛围的渲染和暗示,从这些莫名其妙的对话中,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微妙矛盾。就像英国小说评论家贝茨指出的:“一切语调和情绪都隐含在似乎偶然之间仓促作出的字句安排中(‘我觉得挺好’她说,‘我没什么不舒服,觉得挺好’)。海明威对读者惟一的请求,就是,同他合作,把握住这些语调和情绪。”正由于如此,海明威的海上冰山式的小说,只让读者看到浮在水上的七分之一,而将其七分之六隐藏不露,从而显示出内涵的无限深广。就像法国雕塑大师罗丹以“一个女人的半身像”等缺臂少头的雕像来获取完美一样,运用的都是类似中国写意画的“留白”手法:计白为墨,在无象中打动人。著名作家老舍曾以“十里蛙声出山泉”为题请白石老人作画,白石老人仅抹一泓清泉,勾几点蝌蚪便画出了深山幽涧的象外之象,蛙声盈耳的画外之音。今天中国写意画这种“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辩证法,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作家所运用。
最近,朱苏进、海波分别发表的中篇《凝眸》长篇《铁床》等作品,在艺术手法上作出了新探求,标志着新小说观念对军事文学的影响和冲击。他们都有意采用放射型结构或心理结构,打破时空界限,立体刻画人物心理,解剖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写出“圆形”人物。他们或追求情节的淡化(这一淡化与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淡化密不可分),并不着重描述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并以此吸引读者,而只凸出一种情绪的氛围流贯。他们或故意制造一些“哑谜”(如《凝眸》中那个古怪“悬洞”;《铁床》中那个蒙面女人等);给读者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神秘朦胧的感觉,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他们的小说语言也不再仅仅是情节和人物的运载工具,而力求每一句话都传达出作者某个独特感觉(如海波这样写滚到地上的苹果:“它们用挤出的乳白色的果汁,愤怒地证明自己完全是上等货”),从而使语言本身就成为较高层次意义上的审美对象。这种渗透全篇的感觉美,意绪美和语言美,使你根本无须了解小说的前因后果,只要随手翻开任何一页,读任何几行,都能体会出一点味道。他们或者还通过某些局部的“缺憾”来达到整体上的完美,甚至干脆将诗歌、音乐、绘画等多种艺术手段调动起来。
如《凝眸》开篇写一个战士初上前沿小岛的感受:“踏上岛便感到四周充满威胁”,看石头:“每道石缝都在咬牙切齿,晶亮的口涎嘀嗒着。”听声响:“呼地一声响。我整个人往下一沉,什么声音,像放枪。岛上任何声响都像放枪。”就这样,作者不写上岛过程,也不经意描摹小岛环境,而是把笔触伸入人物内心,一笔写出一个“感觉”(当然,这种“感觉”过多,塞得太满,也给人一种刻意追求的斧痕,如果适当地加以节制,可能反而显得自然,更见空灵)。这儿虽无情节又无悬念,可那“无数吓人而又迷人的念头”却牢牢抓住了我们,只能是跟着作者,“一步踩着一个念头往上攀”。
又比如,海波在《铁床》中写他的落日:“傍晚的太阳,像个没煮熟的鸭蛋黄。薄薄的膜勉强裹着一包成了胶质的流体,橘红、鲜嫩,微微颤动。它小心翼冀地向西面的海湾里沉降着,尽量使自己完好地摆在一盆碧绿的汤里。遗憾得很,快沾上水的一刹那,性急的海嘬了它一口,结果它下沿的膜被吮漏了,金色的流体四处溢散,海也变得粘稠了。”甚至,“天空一下聚敛了颜色,世界一下子失去了味道。”在海波这枝想象瑰丽而又才情洋溢的画笔下,落日成了“没煮熟的鸭蛋黄”,大海则成了“一盆碧绿的汤”,而世界居然还有了“味道”。一幅多么美妙独特的“落日印象图”!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小说写意的随意性,它显得何等自由。就譬如曾给诗人带来抒情的广阔天空的艺术通感,在写意小说中就加倍灵巧活泼了:它抛除一切中间环节,根本无须说出哪是听觉,哪是味觉,随笔所至,天马行空来去如风,呈放射性传导,其广度、速度都不可限量。从而使这种感觉更高、更精、更密,也给小说艺术开了新生面。
写意小说家们又究竟是怎样获取这种艺术魅力的呢?如能弄清一二,那对于作家的产生,和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恐怕也未必是不无裨益的。
许久以来,无数文艺理论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探询:为什么伏尔加河那么多流浪汉,惟独高尔基成了一代文豪?为什么无数穷困潦倒的贵族后裔,只有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答案成百上千,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即创作决不是靠传授公式、技艺和口诀所能学会的。因为文学首先要表现生活中的美,而“美是不可言喻的”。作家们的神秘和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做着一种言“不可言传”之言的特殊工作。如果说,过去的创作多少还有根有据,有法可循(如西方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中国文论的“起、承、转、台”等)的话,那么,小说发展到了写意的今天,已是无法之法了。因为小说所写之意,就是一种游移在人的理性与感性、情绪与理智之间,大脑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之间的不确定物。而这种不确定性又来源于人本身的某些不确定性和生活本身的“二律背反”。可以说,即便是作家本人也是难以把握和驾驭的,就像持保皇党观点的巴尔扎克却向人们奉献了一部抨击现世的《人间喜剧》一样。这就提醒我们在发现、培养今天和未来的作家时,要加倍地重视发现发挥他们身上的作家素质和天赋。
朱苏进的《凝眸》原计划写一个五千余字的短篇,不料情感的闸门一经启开便奔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结果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一个五万余字的中篇。据笔者所知,作家们创作中的这种“失控”现象并不少见。丹纳在分析比较哲学家、政治家与艺术家的特征时,谈到“在艺术家身上,有益的特征是微妙的感觉。”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青年女作家王安忆就是一个凭艺术感觉写作并取得相当成功的典型。她在一篇体会文章中这样说道:我认为在世界上要干成任何事情都得付出代价,惟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写作。她的得意,应该归功于她天才的禀赋,正是她那细嫩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成全了她。我们可以相信,在她的艺术的眼睛里,到处是人物,到处是小说。
别林斯基认为:“文学不是数学,越模糊就越美。”黑格尔也说过:“情感是心灵中的不确定的模糊隐约的部分。”这都是真知灼见。因为只有概念才不模糊,而文学的任务恰恰就是揭示那些概念概括不了的意绪、情感等。如意识流小说就是专揭人的第七层面纱,即潜意识、梦幻、本能等等。一个太清醒、太理智的人可能就缺乏这种意识流。由此可见,对于作家们来说,有时候的模糊并非是一件坏事,相反,过多的明晰与理智正是艺术创作的天敌。歌德就曾注意到德国人的思辨对他们的艺术的不利影响,他说:“总的来说,哲学思辨对德国人是有害的……他们愈醉心于某一哲学派别,也就写得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