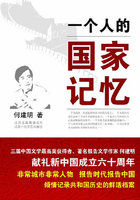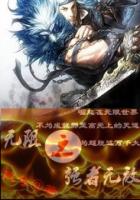明年会怎样
朋友劝我请领导写序,或请名家和大师写序,思考再三,还是自己“聒噪”几句,最为简洁和合适,反正对错、好坏都是自己所为。
风住了,天晴了,月明了,人也静了。好难得的一刻。几个小时之前还和同事们说:“大家可以回家了,这三天没有特殊情况,就全部属于你们自己了,可以不必再悬着心,可以不必再想着这里的事,可以不必像我一样,大家都自由了。”
不知咋的,意识刚刚到这里,鼻子就酸酸的,眼泪止不住就淌下来了,哗哗的,竟然扯也扯不断。在这暗暗的深夜里,在这平日里喧闹无比、几乎天天都人声鼎沸、异常繁忙、此刻却静得几乎没有任何声响的办公楼里,竟然是警卫老王那咚、咚、咚巡夜的脚步声,将我从一种突如其来的酸楚中惊醒。
多么不情愿呀,深知此乃多年难改的书生气,吃尽了苦头的文人气,但书桌上摆着的书稿告诉我,惟有此时,可以拿起那支属于自己的笔。
啊,好无情的光阴呀。新的一年又将开始了,转眼间人生就要逼近知天命的年龄了,仿佛见着黄土似的,心里空空的,眼前便只有了苍凉和惆怅。
还好,尚有思维。记得年轻时,每每心血来潮,便有一些“过人”的举动,甚至有一回剃成了光头,朋友们赞不绝口:“好,好,像个‘大和尚’”,那时心里不知有多美。可惜好景不长,正赶上三伏天,两天下来晒起了满头的红疮。无奈,只好天天顶着个大草帽,好惨痛的教训呀。
这序,想来有如人的毛发一般,自然有其特殊的用项,没有,自然不好。于是,渐渐打消了这“坚决不写序”的初衷,依然人乡随俗,胡乱涂抹上几笔,权当是对读者的一点交待,或言一种情理吧。
记不清是新闻界哪位朋友的“高论”了,但这段话的内容在我脑海中印象却很深:“新闻和政治、文学、社会、经济等学科都关系密切,交叉甚多,和哲学、科学、艺术也有渊源,新闻是一棵由许多不同的学科和行业所供养的大树。”本来,我此生的追求,乃文学艺术,这是从孩提时便开始的。参加工作后,无论岗位发生过多少变化,这种追求从未动摇。我曾不止一次地写下了许多断语,尤其十几年以前开始,那几本散文集、报告文学集相继问世时,曾写道:“我知道,真正属于我心灵的仍是那些与我血肉之躯共存的散文与艺术,它们确是我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和载体。我十分喜爱这种形式和栽体,有它的存在,有它与我为伴,我生命的里程便不能中断。”还记得在《梦里千回》出版时,于自序的中间部分,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生法自然会有千变万化,工作岗位安排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靠文学与艺术谋生,去荣华富责,顼养天年。或能坐下来专门从事创作,不可能的,除非也到了耳顺、从心所欲的年龄,仅仅是一种追求而已,只是如同追求阳光、水分、泥土,如了生命似的,便造就出几十万字、几百万字的作品来。于是,就这般亲人、儿女似的,宁愿与它们日日相伴,一旦有一天离开了人世,也权当是对这个世界留下的几许依恋。纵然那些个被我爱过的人,或者是曾经也爱我的人,会因为有了这些许的依恋,便想到也曾有一颗真诚的心,也就足够了。”
这确实是我的一段真实心迹。从整体看,我还是很侥幸的。这些年,尽管生活经历了诸多变迁,但最终还是涉猎于大文化这个圈子里。屈指可数30多年了,单单在人口新闻这个行当里也转悠了十几年。人生苦短呀,回首往事,尽管生命和事业有如一支燃尽了大半截的蜡烛,眼瞅着要红颜泪尽。但我毕竟在做着一件与文化有关,自己肯下功夫、善下功夫,并也愿意为其献身的事业,也可算做对我文学事业的一种拓展吧。
朋友劝我改改行当,我都不无感激。但自己深知,文化也好,艺术也好,新闻也罢,其实都是一项沉重的事业。1984年,当我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获取金奖时,我便写下过一段话:“我不敢说自己的作品如何,初时,我的确是为了自慰,但很快便发现,这实在是一副可怜相了。”1993年,我的《人生启示录》出版,我在总结人生的得与失时又写道:“写作到了今天,作品获了几十个奖,年龄已近不惑,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自慰或辉煌一番吗?实际上,我创作的真正本质,乃是要觉悟人生,表现世事沧桑的。为此,就是要用尽毕生的心血,即使清贫终生也认了。”2000年,我获取了全国报纸副刊最高奖——金奖,它既是文学在媒体的最高奖,也是新闻的最高奖。应该说,我确确实实是幸运的。不久前,那个管理新闻的最高部门,为了建立新闻与文学高级人才数据库,粗略统计了一下,我突然发现,那些获奖数据确实让人为之一振。尽管那些数据显示,那些个奖项大部分来自我当记者、当部门主任、当副总编辑的那个年代,许多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但一个人的总量、质量、层次,几乎超过了整个集体。虽说人生无限,也实在应该聊以自慰了。
然而,整整6年了,新的一年此时又要开始。一个搞创作、搞文化的人,停止了写作,停止了创作,这是何等的残忍呀。记得当作家、当记者时,走南闯北,见百种人,吃百家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时间自己支配,情绪自己安排,无牵无挂,无怨无悔,好不潇洒。可这些年,天天都在琐琐碎碎中度过。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成天为如何办好报纸,如何搞好经营,如何搞好管理,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抓好新闻而奔忙、而彻夜不眠、而寝食难安。具体到乃至一个思路、一项改革,一个主题、一项策划,一个标题、一篇稿件,一张图片、一幅版式,成天为别人做嫁衣裳。心里想着的既有宏观思维,又有微观操作,甚至天天要追求平安着陆。也忘不了新闻要创新,要出彩,要有规模,要立于潮头,要敢于领率社会,如此这般琐碎却又如此“骄狂”的工作。
悲哀呀,这一幕幕轰轰烈烈的场面,早已成了过往。每每是一篇篇稿件见报,一次次惊险场面渡过,一期期合格样报出版,一个个记者、编辑出彩,一批批新闻人才造就而成,一项项改革获得成功,一次次新闻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人才效益大获丰收。而自己,却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十足的“万金油”,一个所谓的管理者。何曾再想过出几本书,想过在我的前面,竟然还会有一本新闻的书在等着。
不可想像,不可思议。或许,这就是一种责任,管理者作为设计者,也作为幕后人,只有牺牲和奉献。或许也叫做一种分工吧,乃一种社会分工吧。如同有的人来到这个世上,早已有了明确的分工,就是为了拥有和享受;而有的人来到这个世上,则注定要忙碌,就是要为那些能够安心地、自如地、尽情地享受和拥有的人去创造一切。这或许便是那个不够准确,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辩证法”所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