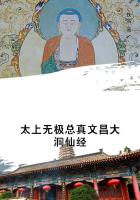拉姆抬头一看,啊,一片闪闪烁烁的亮光。蓝莹莹,绿森森,不像空中流下来,也不像从地面平射出来,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层下钻出来的。噢,看久了,你会觉得那光其实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总之,你很难确切地说出它是什么颜色。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可能是灯光。按说在这无人的旷野,看见任何一点亮光,哪怕是极微弱的一豆之光,都会使人十分亲切。可是,这一片荧光让李湘和拉姆有一种透骨刺心的恐惧之感。
他们让骆驼停下,静观前方。谁也不说话。
原来,前面是一片凹地。
忽然,骆驼大声吼叫着向前奔去。那蓝、绿难辨的光一动,像流星似的散窜而去。
啊!狼!狼眼!
那次,他们意外地得到了一只狼崽。
如今狼崽已经三岁半了!
这朋友意义上的狼崽,亲人意义上的狼崽,卫士意义上的狼崽,三年中,活跃了这个孤独的三口之家,给了他们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安全感。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狼崽,他们是很难熬过这三年的。
那夜,多亏了心爱的骆驼一声怒吼,把聚集在凹地过夜的狼群吓跑了。但是,拉姆也被吓瘫了。她从骆驼上摔下来,坐在地上,一步也不敢挪了。李湘陪她坐了一会儿,她突然像遭咬了一样,大叫起来:“妈呀,有狼!”她像弹簧一样,从地上弹射而起。
李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上前一看,朦胧月色下,地上蜷缩着一团毛茸茸的东西。
这就是那狼崽。它的父母受惊逃走时顾不得拖着它,它只好当了俘虏。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便宜。就在拉姆和李湘带着狼崽走出没有半里地时,那群狼掉转头追回来了。很明显,它们要夺走狼崽。
又是骆驼大声吼叫着吓跑了狼群。
从此,狼就成了他们三口之家的编外成员。家里添了一张吃饭的嘴,日子自然就过得紧巴了。本来就不富裕,肚里少一点油水并不觉得什么,完全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乐于为之的艰辛。一句话,有他们一家人吃的一口饭,就绝不会让狼崽饿着。
最初,狼崽夜里睡在他们脚下的一个专门为它做的小木板暖房里。后来,他们索性就让狼崽紧挨着他们的睡铺睡觉了。这样,他们夜里睡下后身上总有毛茸茸的透心暖。
从这时候起,狼崽就有了名字:甲巴。藏话是胖子的意思。狼崽确实很胖,名副其实。
甲巴极为聪明,或者说很通人性。
这几乎成了一个“定格”的图像:每天,夫妻俩赶着羊出牧后,在一面向阳坡上,要么李湘和拉姆并排坐着,懒洋洋地晒着阳光,甲巴蹲在面前,亲呢地看主人;要么李湘怀抱甲巴,呆望着在草滩上赶羊追羊或者一边看羊群一边捻毛线的拉姆。拉姆见他看自己看久了,就会很不好意思地喊一声:
“湘子,你倒来啊!”
说罢,她格格格笑得好亮。
于是他们钻进出牧时临时搭的帐篷里亲热一番后,又出来照看羊群。
这时,太阳好红!
日子就这么酸酸苦苦、甜甜蜜蜜地过着。甲巴是一粒盐,给他们的日子增添着滋味。“可是,它太小,什么时候能长大呢?”拉姆呆望着天边的落山日头这么想。其实,她是嫌自己的生活太寂寞,盼着儿子和甲巴一起长大。
甲巴的变化很有意思,出乎人们的意料。它越长越不像狼了,尤其是尾巴的变化,很耐人寻味。开初,狼崽的尾巴像一般狼尾一样,长长地拖在地上,毛紧裹着尾骨。不久,那尾上的毛就渐渐地松散开来,一松再松,一散再散,呈出扇面状。小多吉特喜欢这“扇子”,便拽着狼崽的尾巴,那毛便立即收缩起来,他赖在地上,让狼崽拖着滑行。狼崽一点也不怒,任凭小主人戏耍它。
小多吉就这样拖着狼崽的尾巴玩着,玩着,狼崽被他拖长了,拖大了。狼崽变成了大狼,小多吉却……
小多吉死得真惨!
拉姆和李湘认定那是狼们的恶性报复。
当时,刚刚吃罢早饭,李湘到远地打冬草去了,拉姆上草滩时第一次没带小多吉同行。夜里他跟着阿妈打酥油茶熬过了夜,眼下睡得正酣,阿妈不忍心捅醒他。
后来,大约没过一个小时,甲巴就满身血迹地跑到草场,撕拽着拉姆的裙摆,让她回家。拉姆感觉到情况不妙,便跟着甲巴回到了帐篷。一看,小多吉不见了。帐篷里外都不见人影,她疯了一般哭喊着:“我的多吉呢,他哪里去了?”
甲巴引着她到了离帐篷约五百米的一个沟坎下,她看到一堆血淋淋的白骨……她和李湘,还有甲巴,整整守了这堆白骨三天三夜。
藏家女人和汉家男人混在一起的二重哭声,震得坡地上的帐篷都在发颤。
后来,据他们分析判断,事情的经过很可能是这样:狼群趁主人外出放牧的空当儿,来到帐篷里抢夺狼崽。没想,狼崽不仅不认它的同类(包括它的父母),还与它们厮拼了一番。狼崽毕竟力小身弱,斗不过狼们,只好跑来“报案”。
小多吉死了,甲巴成了拉姆唯一的“儿子”。
她紧紧地搂抱着甲巴,甲巴舔着她的手。她觉得那是多吉在爱抚着她……
终于有一天,甲巴可以独当一面地在这个家庭里显示它的谁也不可替代的地位。那是在它的狼性完全消失、而又绝对不像狗的情况下,一只羊被它赶着从险路回来,然后,拉姆跪倒在它面前不住地说“你真的长大了”那句话之后。
说起来,活该那只羊倒霉,谁让它在主人拉姆回帐篷喝水的空儿,一转眼就溜得无踪无影了呢?
其实,不是那只羊贪玩,而是它看见了一只狼才悄悄躲开的。
这样,狼便追了上去。那狼已经在旁边寻谋好久了。离群的羊被狼紧追不放。羊走得慢,狼也走得慢。羊快走,狼也加速走着。一直走了大约一公里地的时候,羊才在一片开着格桑花的草地上站住,狼也在十步开外站住了。
直到后来这只羊安全地摆脱了狼的纠缠以后,拉姆才明白过来,那只羊实在聪明过人,它很可能是为了把狼引开,才有意离开了羊群。
还有一个情况必须交代:当时甲巴看到了草场上发生的一切。
从一开始它就一直监视着那只闯进来的狼。当狼尾随羊而去时,它便跟了上去。
羊在前面;狼随其后;甲巴在最后压阵。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说它们三者都是心中有数的。羊是引火烧身。狼是寻找美餐。甲巴显然是为保卫羊而出动的。
当羊与狼对峙起来后,甲巴悄悄地隐身于一个草坎后面,竖起耳朵,瞪着双眼,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狼终于按捺不住肉欲的诱惑了。它先是倒退了几步,然后一个凌空飞跃,冷不丁地向羊扑去。
大概狼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它快接近羊时,甲巴突然出现在羊身边。甲巴怒目瞪视着狼,两只前爪还不时地跃起来,完全是一副决斗、且如不获胜决不罢休的架势。一切都是始料不及的。狼还没弄清这只活物是什么,不像猎犬,也不像它的同类,只感到它高大,壮实,于是,它倒退几步,夹着长长的尾巴溜之乎也了……也就在这时候,寻找羊的拉姆气喘吁吁地赶了来。一切化险为夷!
次丹堆古喇嘛微闭双眼,不讲了。
我问,狼崽的故事讲完了吗?我这样问的意思非常明显,故事我还要听下去。谁知,他既不说完也不说没完。只是微闭着双眼。
我没有打搅他。他一定很累,因为我也听得很累。狼吃掉了人,狼又帮人救了羊,谁听了心里都会沉重。
这时,次丹堆古很可能为了改变沉闷的气氛,有意转了话题。
他给我讲了一个听起来绝对与狼无关的故事。野兔、岩鸽、地鼠和雪鸡的故事。
他怎么知道那么多无人区的事情?
他是以亲身经历者的口吻给我绘声绘色地描绘这个奇特的故事的——一个雪后天气朗晴的中午,次丹堆古在草滩上闲走着,他眼睁睁地看到一只岩鸽从空中落到一个洞穴前,伸着脑袋张望了一下,便钻进了洞里。那洞很小,刚刚能容纳岩鸽的身子。
鸟儿进洞?太稀罕了!
他在那个洞穴前站了好久,希望岩鸽能出来。可是洞口静悄悄的,很像一个遗弃了多年的死洞,没有丝毫的动感。他是眼瞅着飞进去了一只鸟呀!
他不由自主地伸手在洞上面拍了拍,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拍,从洞里出来了一只野兔。那兔显然受了惊,一出洞就撒腿跑了。
他不甘心只见到这只兔子,也是担心那岩鸽的命运,便又拍了拍洞,扑棱一下飞出来了,不是岩鸽,而是一只雪鸡。接着又一只地鼠蹿了出来……
他完全惊呆了。鸟进洞穴,奇事!鸟与兔、地鼠同住一起,更是奇事中的奇事。
听到这里,我问次丹堆古:“你也是第一次见到鸟儿在洞穴?难道在你过去几十年的生涯中一次也没见过这种现象?”
这时候,我倒好像成了一个比次丹堆古还经得多见得广的高原通了,在这个喇嘛面前也摆起了老资格。他根本不理我这种盛气凌人的架势,只是说:“是的,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
我告诉他,这叫鸟兽同穴。他惊疑地望着我,显然对“鸟兽同穴”这四个字感到很新鲜,希望我继续讲下去。我便对他解释说:
“由于高原上无树少崖,鸟儿无法筑巢,只好借兽们的洞穴为家了。说是借,其实是强占。强者为王嘛,鸟兽也如此。最初,鸟兽住在一起当然会发生争斗,这种争斗非常强烈、残酷,或一方败阵,或两败俱伤。时间长了,同居的生活习惯了,洞内无形中形成了各自的天地,谁也就不管谁了。直到和睦相处。”
次丹堆古点点头,表示他懂得我讲的道理。
这时,他反问了我一句:“拉姆、李湘与狼共处,这回你也该明白了吧?”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给我张开了一个网,套我进网了。
他真会讲故事!
我马上想到了拉姆的“三口之家”……
如果他们早知道这里是如此美丽而富饶的“野生动物王国”,当初的第一个定居点就会毫不犹豫地选在这里。
这夫妻俩不知不觉来到这儿“定居”已经两年有余了。
这里叫什么地名,属于哪州哪县管辖,他们一概不知。只有偶尔遇到零零落落的几个赶着牛羊在荒凉草原上跋涉的游牧人,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仍然还生活在人类生息繁衍的地球上。
结痂着岁月烟尘的帐篷撑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一根木杆直直地竖立在地上,系于杆上的两条绳子分别牵着帐篷的两个角,一条绳上晾晒着准备贮存的已经风干了的牦牛肉,另一条绳上缀满了各种颜色的经幡。
帐篷前面一箭地之外,就是两个湖泊,一大一小,水面清澈,明镜一般。很像一副眼镜片。
这就是他们的家以及家附近的环境。
夏天,他们总是把帐篷搬到山顶上去,在山上放牧,把山下的草留给羊过冬天。在山上住的日子里,山下的帐篷地依然竖着木杆,依然有经幡和晾晒的衣物什么的,以示这里是有主的草场,免得别人占去。
两个无名湖里自生自灭着西藏特有的无鳞鱼。这些鱼耐寒冷,抗盐碱,生长期慢,寿命却很长。祖辈千年不吃鱼的藏家人是从来不捕鱼的,因为鱼在藏家人的意识里是很神圣的,就连许多高原上的食肉动物看到鱼也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漠然神态。这样,湖里的鱼就可以不受干扰的自由自在地长着,有的长到几十斤,上百斤,等到老死了那一天,不少鱼像一条小船滞留水底直至腐烂。
那是来到这儿安家后的第一个蚊虫、瞎虻乱飞的夏日的一个中午,正在草滩上看管羊羔的拉姆突然惊诧万分地对丈夫说:
“快来看,有人!”
李湘赶忙从帐篷里跑出来,一看,对面靠湖边的水面上露出了一大片西瓜似的好像人脑壳样的东西。他睁大眼睛盯了半天,也没有辨清是何物,便对拉姆说:
“不像是人。”
“那又会是什么呢?”
当然,他们最终还是弄清楚了,确实不是人,而是一群藏羚羊在“避热”哩!
这么多藏羚羊集中在一堆,还真是少见,拉姆和李湘贪婪地看着,心里好痒痒。
藏羚羊是珍稀动物,濒临灭绝。它十分善跑,每小时可以跑八十公里,汽车加足油门也不一定能追上它。它跑快的奥秘全在胯下的那个“风袋”里,牧人称之为风翅膀。它跑起来时“风袋”便鼓胀,产生张力、风力。藏羚羊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是夏季。原来它身上的皮下寄生着一种虫,叫背虫。这种虫在隆冬寒天化为油脂,融入羊体内,营养着藏羚羊。春天就变成了虫子,在藏羚羊的皮层下频繁地活动。它很像冬虫夏草。背虫在毛皮下日夜不停地活动,使藏羚羊奇痒难耐。于是,藏羚羊在虫子活动的夏季便不由自主地寻找凉爽清冷的地方“避热”,好使虫子处于“冬眠”状态,以减轻奇痒。
拉姆领着李湘来到了羊们“避热”的水边。这里的水中伏卧着上百只藏羚羊,它们很坦然,一点也不怯生,只是抬起头望望岸上的两个牧羊人,望望跟随主人身后的甲巴,又埋下头。
甲巴跑出去几步远,冲着天空嗥叫了几声。它为什么这般嗥叫,主人不得而知,藏羚羊却抬头望着甲巴,显然它们觉得这叫声很熟悉,先是表现得有几分惊恐,随后很快又泰然处之地卧于水中,了。
拉姆夫妻俩就这样和这些“避热”的藏羚羊们做了邻居。生活平添了几分热闹,几分向往!
在这些藏羚羊面前,善良的拉姆变得更加善良。她把自己为羊儿准备的“食品”匀出一部分,撒到水面上,喂藏羚羊。藏羚羊开始总是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个藏家女人的殷勤,有些胆怯,不敢张嘴。可是,拉姆来湖边的次数多了,它们便打消了疑虑,很香甜地吃起了她送来的“食品”。
从此,拉姆就多了一项额外的任务:负责喂藏羚羊吃草,有时还从不算太远的清水泉里打来干净水给它们喝。
当然,藏羚羊也会设法回报它的主人的。
那是在藏羚羊发情交配的季节: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