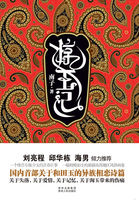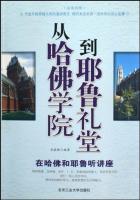八月下旬,王子浩专程从上海赶往沧州,护送云云回沈阳。这次他不单单是送云云,同时,他还要带走吴欢,让他去上海接受最好的教育。他答应过弟弟,要替他照顾好云云和吴欢,他不能食言。
在王子浩住宿的宾馆里,王子浩和相约而来的水生、张健、吴欢还有云云再次相聚在一起。当初是王子明将他们这些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时,却独独少了王子明。那种悲伤的情绪和对王子明的刻骨思念始终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
临分手时,王子浩留住了水生,说有话要和他说。待他们两个送走了其他人回到房间以后,王子浩便从随身携带的密码箱里拿出厚厚的几叠百元钞票推到水生的面前,很郑重地说:“我是小明让我还给你的,他想让你早一点把婚事办了。”
水生看了看王子浩又看了看那钱,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这钱我不能收。”
“你必须得收,这是小明的意思,要不他会怪我的。”王子浩看着水生,没有一点想收回去的意思。
两个男人为了这钱的归属互相推辞着,争执着,几个回合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心情都悲伤到了极点。
“你是不是想让小明在天之灵不得安宁?”最后,王子浩竟铁青着脸冲水生吼道。然后,就转身快步冲入卫生间,并关上了卫生间的门,屋子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泪水从两个互相看不见的男人的脸上流淌下来……
水生最终还是收下了那钱。用这些钱他把小娟父母、哥哥还有长江的钱都还了回去。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把从其它人手中借来的钱都退完了。最后,他的手里还剩下四万多元,这个数目与他和小娟当初积攒的钱数差不多。可水生却觉得重新拥有这钱心中有愧,经过与小娟商量,他把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万多元全部以王子明的名义捐给了正遭受洪水袭击的受灾地区。
当时,正是南方水患刚刚过去,北方嫩江、松花江正洪水泛滥的时节。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正以迅猛之势威胁着江河两岸的城市和乡村。
沈阳城虽然远离江河,但全市上下也都在紧急动员,号召各单位、各部门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支援灾区。
那些天,只要一打开电视,看到最多的就是关于抗洪救灾、抢险护堤之类的新闻报道,同时配有画面。也说不清为什么,只要一看到这种场面,水生便忍不住心潮澎湃,胸中似有一股激情在涌动。特别是看到抗洪官兵用身体去阻挡洪水的画面时,他的心便会狂跳不止,仿佛自己也正和他们一样置身于汹涌的波涛之中,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一种潜藏在心底的直觉告诉他,他和洪水和这些官兵们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可惜,他失去了以前的所有记忆。他只记得王子明对他说过,他是他们从江水里救上来的,当时,他不但生命垂危,而且表情木讷,后来又高烧不退,是在医院里昏迷了几天几夜才活过来的。而他自己却连和王子明他们最初相处时的情形都记得模模糊糊,仿佛只有几个支离破碎的片断似梦非梦地留在了他的脑子里,构成了他那段时间的全部记忆。他的头脑是在和王子明他们一起踏上打工之路后才逐渐清醒、灵活起来的。也许只有奔腾的洪水才可以冲开自己记忆的闸门,他这样想着,并努力地回想以前的事,希望能有奇迹发生。可是,不等奇迹发生,他的头脑中就开始有浑浊的水在涌动,继而奔腾咆哮,冲击……头又开始炸裂般的疼。
头疼的重新发作,并没有影响他大脑的正常思维,想恢复以前记忆的想法倒越发强烈起来。
虽然小娟和长江给他讲过许多足以唤起他记忆的往事,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无法唤起他的任何记忆。可小娟和长江手里的那些照片又在时刻提醒着他,自己和江浩确确实实是同一个人。只有当他站在母亲坟前的时候,只有当他和母亲那关注的目光相对的时候,他才会真的相信,自己就是她的儿子。
仿佛是被一种神圣的力量所驱使,水生决定亲自前往灾区,到抗洪的最前沿。
正好,长江他们公司准备向战斗在抗洪一线的官兵们捐献一批食品和饮料,并决定由长江亲自押车送过去。听到这个消息,水生立刻找到长江,声明要和他一起去,而且越快越好。
对于水生的决定,小娟并没有阻拦,她知道自己无法左右水生的决定,她也不想那样做。她只是暗地里嘱咐长江多辛苦一些照顾好水生。
长江他们的汽车刚一驶入黑龙江省境内,就感觉到了一种别样的气氛,一辆辆挂着不同省市牌照的汽车正满载着救灾物资和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向这里汇集过来。许多路段上都排起了长龙。还有一些由外省市抗洪自愿者组成的突击队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的车上大多挂着醒目的旗帜,旗帜上印着:“某某市党员突击队”,“某某市某某乡农民突击队”。另外还有大学生突击队、复员军人突击队等等。
看着他们,水生才感到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的平常。
随着汽车的不断行驶,越来越多的解放军官兵跃入了他们的视野,虽然他们神情疲惫,却个个步履匆匆,让人感觉到前方正发生着紧急的情况。
经过有关部门的安排,长江他们直接把汽车开到了松花江下游月儿湾地区的干堤上。
月儿湾地区是松花江历年来防洪的重点堤段,面对今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形势更显严峻。所以,抗洪指挥部在这一地区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
长江和水生他们把食品和饮料交给接待他们的官兵时,已时傍晚时分。此时,江面被夕阳的余辉妆点得波光闪闪,近处的庄稼和远处的村镇在江水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葱绿和怡然。如果不是即将到来的洪水,这将是怎样一个平静而祥和的傍晚啊!而现在,大堤内外依然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许多只穿着背心短裤的官兵们站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打桩筑坝,加固堤防。不时可以听见他们嘿嘿的喊声。堤外是成百上千的军民在没膝深的积水中来回奔跑,背运沙包……
这种场面,这种气势让水生的心又激荡起来。他觉得这种场面他曾非常非常的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但他可以肯定地对自己说,这绝对是他经历过的场面。
在长江和一位接待他们的连长说话时,水生就已经挽起了裤腿加入到背运沙包的行列。那个负责装袋的小战士大概是从他整洁的衣裤上看出了他是新来的,对他报以友好的一笑,两颗虎牙和一对浅浅的酒窝便从小战士那张稚气的脸上显露出来。几趟下来,水生就已经有些喜欢这个动作麻利、神态中透出一种孩子气的小战士了。
此时,正有几位电视台的记者在堤上录制新闻,也许是因为水生无可挑剔的长相,那位摄影记者竟把镜头锁定了水生,对他进行了两三分钟的跟踪拍摄。
天擦黑时,长江才在背运沙包的人流中找到水生。此时,水生也和其他人一样,胸部以下满是泥水,而且由于身体刚刚恢复,他看起来有些狼狈,气喘吁吁的。长江把他从人群中拽出来,劈头就问:“你背它干嘛?这么多人也不缺你一个。再说你病刚好,累坏了怎么办?”长江的口气里有责怪,但更多的还是关切。
“干这点儿活累不坏,我身体好着哪。”水生边说边把身板直了直,显出很精神的样子。
“得了,别跟我装了,你还是快跟我走吧!我们上城里住一宿,明早再往回赶。”长江说着,转过身向堤下走去,水生站在原地没有动,长江回过头疑惑地问:“你不走?”
“我不走了,我想留在这儿。”水生边说边把目光投向那些依然在忙碌的官兵们。
“留在这儿?你不是开玩笑吧?要知道你要留在这,我压根就不能让你来。”
“我就怕你不让我来,才压根就没说。”水生狡黠地一笑。
“不行。你必须跟我回去。要不我没法向小娟交待。”
“不用你跟她交待,等我自己跟她讲。”
“那也不行,你怎么跟我来的,就怎么跟我回去。”长江摆出一副兄长的派头命令着。
“反正我不想马上回去,你看他们不都在干吗?我又不比他们老,干嘛不能为抗洪出份力?”
“你不是捐了那么多的钱吗?”长江反问道。按他的想法,抗洪是大家的事不假,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既然水生已经捐了那么多的钱,就没必要再耗费力气。
“捐钱是捐钱,和这两码事。总不能因为捐了钱,就光看着别人出力冒险,自己袖手旁观吧?”水生分辨着。
“这要是在咱们家边上,你怎么的都行,可这是在黑龙江,离咱们沈阳有一千多里地,你要逞英雄也没必要非在这里逞啊。”长江的话难听起来。
见长江真的生气了,水生也就没再说什么,不过心里早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留在这儿。这是他临来时就已经打算好了的,特别是看到那些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的自愿者后,他就更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
见水生不说话,长江知道是自己刚才说话说过了头,也就没再往下说。两个人站在原地默默地僵持了好一会儿,见水生没有丝毫要妥协的意思,长江只好作罢。不过最后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你到底回不回去?”
“不回去!”水生回答得比较干脆。
长江看了看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他,就说:“那好吧。我也陪你留在这儿,要不我也不放心。”
“真的?”水生乐了。
“真的。”长江回答得既勉强又无奈。
当晚,他们和几十名外地的自愿者被安排住在临时搭起的帐蓬里,因为帐篷有限,不少官兵只得住在大堤上。
夜里,水生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好悄悄走出帐篷。站在帐篷外,他可以看见堤上仍旧有许多官兵在守护寻查,不时可以听见他们在互相提醒说话的声音。
水生重新回到帐篷里时,更加没有了一点睡意,到这以后,他所见到的一切,依然萦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那种似曾相识的场面和气氛让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无法不想下去,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思绪……直到头脑中又有浑浊的水在涌动,继而,翻腾,冲击,咆哮……头又开始炸裂般的疼……
那一夜,水生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长江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水生的变化,只一夜的工夫,水生就黑了眼圈,脸也好像瘦了。
“怎么样?吃不消了吧!还是跟我回去歇着吧。我可不愿意看你遭这份罪。”长江边说边凑过来,看着水生的眼睛,十分心疼地样子。水生把头扭向一边,倔强地说:“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反正我不会跟你走。”
长江见劝不动水生,只好打发走了司机,自己陪水生留了下来。
匆匆吃了一点东西后,大家就都自动奔上大堤,重复前一天的劳动。长江也不好意思只当观众,也就和水生一起背起了沙袋,可惜他那一身名牌的衣裤,没多大一会就溅满了泥水。
长江已经发福,加上平时享受惯了,这会冷丁一干活,哪里吃得消,气得他一边背一边咬牙切齿的抱怨:“这哪是人干的活呀?下回打死我也不来了。”不过,说归说,他照样一趟也没拉下,始终跟在水生的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