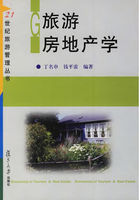刘蓓返回客厅,拿起手机轻轻擦着屏幕,她的屏保图片是当年她戴的那个面具的照片,一只幼黄的小鸭子。她又拨了五遍,每一次,自动回复都像只手一样拧着她的心脏,她感觉自己真被抛弃了。她想,从这一刻开始,她不是原来的刘蓓了,原来那个丰富有念想的刘蓓死了。明天的刘蓓也就是具行尸走肉了。
这种感觉,和那年她刚到西安学校里时一模一样。
第一个学期,她是看着地图上南京到西安之间的千山万水过的。她买了张地图,一遍遍用红蓝各色笔从西安开始,向斜下方,一丝一乎一毫一厘,南京,渐渐地近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紫金山顶,看到了雨花台,看到了南京火车站,看到校园里或在打球,或在听课,或在偶尔走一下神也想着她的杜卫东。那时节,在南京的仿佛已经不是杜卫东,而是她,西安的街道建筑和各处的地名她没认识几个,但南京,对于她,却已经像呆过多少年的老地方了。玄武湖、紫金山、秦淮、鼓楼、聚宝山,每处的一草一树一砖一瓦,连街角铺的花砖,路灯杆的形状和颜色——都在她的想像中生气活现。那时候,她才明白,心,原来是可以和身体分开的,并且能分得很远。心不需要眼睛,也可以将她所爱所关心的一切看个清清楚楚;或者从南京开始,往斜上方,每一次,手都在抖。一段时间后,那张地图从南京到西安——她常走的那条路已经裂开了,像她等待他的消息心里裂开的口子。
像她现在盼着拨打的号码那端突然传来杜卫东的话一样,那时候,她天天在盼着突然有一天,会收到杜卫东的信,哪怕只言片语呢。可是,没有,从来没有。走投无路的她在那段时间常常向一位高她一年的同乡诉说。他们是在学校不远处的公园滑冰场认识的。后来,一般是他滑,她看,渐渐地,话越来越多,他说,我当你一哥们儿吧。天真的刘蓓就真拿他当哥们儿了。将对杜卫东的思念、怨一股脑地倒给他。起先,他还点着头,说句自己认为得力其实又安慰不了她的话。后来,就什么也不说了,每次神色凝重地看着前方,等她说完,或者重复一遍,又一遍,看她眼泪一次次流下来,干了,再流下来。
大学四年,在校时想起来,仿佛长得漫无边际。那么多悠长难耐的时间要打发,有时候他们一起到西安城外,看那一橉橉的山,西北的山绵长浑厚,同她心里对杜卫东的思念一样。有一次,他们看到一架飞机从头顶的高天上飞过,拖着老长老长的轰隆隆的声音。他说:
“你猜,这飞机是去哪里的?”
“是去南京吧!”
她悠悠地说。说完看看他,他还看着飞机已经消失的天空,眯着眼,看不出心里想什么。她又问:
“你没有女朋友吗?或者,心仪的女孩子?”
这样的问题,刘蓓已经问过他多次,但他都没说话。后来一次,刘蓓问他时他们正走在从公园回学校的路上。街两边人来车往,熙熙攘攘,有心急的餐馆和店铺已经亮起霓红灯,闪闪烁烁。他们俩朝前走着,刘蓓一棵一棵地数着退到身后的绿化树,树那么多,她数不完。他呢,则只是朝前走着,神色平静悠然,也看不出在注意什么。
“我请你吃饭吧!”
他突然说,并没有回答刘蓓的问题。
“好啊,回答我,先。”
刘蓓将手在后面拧搅着,晃着身子。他低下头:
“有。”
“就是嘛,你好鬼呀,我一个劲儿说我的事儿,你一个字都不提你自己的,鬼死啦!”
刘倍返过身后退着嚷嚷。他没有回应刘蓓的话,后来,在一个小餐馆坐下了,他一边递给刘蓓筷子一边说:
“有什么好说的,你说,我听,也好,干嘛非得两个人都说,有爱说的,有爱听的,才和谐嘛。”
说完冲刘蓓笑笑,刘蓓也乐了。
刘蓓又拨了七遍,每一次,都让她心里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