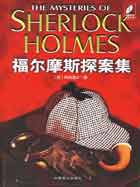我最终决定,用最最简单的叙述方式,说说老根,还有我们之间的那个秘密。这个曾经三个人知道的秘密现在只有两人知道了,因为老根已经故去多年。我坚信。当时只有三个人知道:老根、我、老天。只所以把老天也算作一个人,实在是我想对老根好一些―――想让老根,一个真实的老根,被更多人知道。你也许会说,这个“知道”的事,我大可以对许多人去说。实则不然。耐心,请听我讲完。
对了,如果你真听我把老根的故事讲完的话,请闭上眼睛,就一会儿,用这种方式,向老根,怎么说呢,致敬,好像不太妥,悼念,也不妥,就算是用这种方式,感谢他的这个故事吧。
老根如果活到现在,七十一周岁。他不知道自己具体的生辰年月,这是因为他娘把生他的日子忘了,只对人说,也对老根说,是“雨打番瓜叶的一个头晌”,这样想来应该是夏天,因为我们处于北方,是北温带季风气候吧,一个产妇,在阵痛中还能听到雨打番瓜叶的声音,说明这雨有些大。这么大的雨,也只能在夏天了,想必番瓜叶也已经是茁壮的了。这样分析,就是仲夏吧。这样被说来想去,老根的生日就产生出些许诗意,茅屋、雨、婴孩、叮叮咚咚。
我和老根是光屁股长大的。我们两家前后邻,都没上完小学,老根后来参了军,我则辍学在家务农。后来老根回家,我在另一篇有关老根归来的文章里是这样描写的:“一个火烧云的傍晚,无风,静得听得到自己行走间身体划开空气的声音,陈麦穗坐在屋山上,直呆呆地望着陈谷子家屋顶上笔直升起的炊烟,这缕炊烟缓缓地从陈谷子家屋顶上升起,不急不缓地向上爬升,一边漫无目的地扩散开来,将望洋坡,不,向阳大队上空的一角氤氲成一幅莫名其妙的水墨。陈麦穗叹口声,拉着自己的目光从天空间下移,左转,一泄而平铺到通向村西的路上。她感觉有个东西妨碍了她目光的流动?两根绿凄凄的柱子蛮不讲理地直杵在路中间,将陈麦穗的目光无情地堵住,使麦穗的眼睛胀得生疼。麦穗背靠在山墙上,双脚蹬住面前的老榆树,死劲让自己的目光往上爬,以漫过障碍物顺利通行。”老根归来时是个傍晚,当然,文中的陈麦穗,就是我了。我感觉与老根,有着千思万缕,撕扯不开的因缘。
接下来我抢了他的军用水壶:“陈麦穗跑过去说,哎呀,你这个水壶真实实地好啊,能盛开三大海碗水吧,你在路上我就看见它了。说着就想把它拽下来,可三摘两摘,怎么也弄不下来,急得拽着翻来复去地看,拽得陈麦根三摇两摆。陈麦根拿不准该管她叫姑姑还是姐姐,也不知道他走了这几年是不是乡风已经朴实到了这种程度——”我那时也就是个半大孩子的心智,不经事,不长智。见笑了。
我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还写过这样一段话:“它们都让我感觉生命本是一场闹剧,都是闹剧,什么都是闹剧。
可是,我现在,却宁愿放弃宁静与清醒,回到那五彩缤纷的闹剧中去,做一个不想明天与未来、不想生活与人生的傻瓜。
我要无限接近它!
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原来是多么喜欢闹剧,我要拥抱每一个剧中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突然想起了老根,真的,我要特别热烈地拥抱他。”
我还写道:“一个人,与所有人为敌不要紧,最坏孤独点;与自己为敌也不要紧,最糟糕分裂点,但是,千万不要创造机会与自己对众人对我们的感觉的感觉为敌,这句话很拗口,想起来就像一面镜子斜对着一面面镜子一样,将实质性的东西折射来折射去。但是,这是句实话。我不幸有机会拿走了这堆镜子中的一面,也许,老根从倒掉了一大堆正在胡乱折射的光中看到了真相。我的手很罪恶。我现在看着它,感觉上面满是老根淋淋的鲜血,那种撕心裂肺的血腥味,让镜子前的老根比我更早地体会了刚才所说的一切,或许,我的体会,只是他体会的九牛一毛。不管怎样,我得将它说明白---我尽力说得明白点。”
想起这些,想起老根,回忆是片段的,零落的。我得把那些小的碎片整合起来,组成大一些的。但怎样努力,这条断流多年的河,任雨水再大,水源再足,它也不按原来的河道流淌了。它恣意横流,分出许多支支叉叉,绝不顺着老河道按部就班,让人平白生出很多宿命感―――生了叉的宿命。
是这样的,老根回来后,我娘赵小朵就拼了老命搓合我们,一来她认为让自己的闺女嫁这么个浓眉大眼、身板绷直、走过路见过世面的退伍兵,是件很有面子的事;二来这桩亲事挺划算,因为老根回来前,其双亲已经下世,这样我嫁了他,赵小朵就可以多出半个,也许是一整个儿子。所以,赵小朵经常叫老根来我们家吃饭,有时候她自己去叫,有时候打发我或者是陈麦苗(我弟弟)。一叫即到,到了后规规矩矩坐上小板凳,有板有眼地吃饭。他活该在我们家这样的,因为他叫陈麦根。我是麦穗,我弟是麦苗,都在麦根上边,他活该“忍气吞声”,这样过了一年多,依照赵小朵的意思,老根就该托个媒人说媒了。但一直没有。赵小朵说:麦根成了“炼钢英雄”,不认识我们家麦穗了。
说以上话时赵小朵无限悲哀,我猜她悲哀不只是因为老根“不认识”我了,而是因为在她在心里度量了一个“炼钢英雄”与她女儿的距离。当然,这个距离不是他家到我家的一步之遥,而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在她的盘算之内的。她据此认为她的女儿完了,或许还像一个弃妇,被大好光明一下子扔进黑暗里。好在这个“黑暗”是渐进的,如若不然,赵小朵一定会喊着嚷着到老根家房楣框上上吊——当然,这只是我的度量,和赵小朵度量老根与我的距离后否定了我一样,我也否定了她,不过,我的否定是早先就否定了,没有很明确的理由。
老根怎么成为了的炼钢英雄我倒忘了。反正他成了“炼钢英雄”后,整天与陈艳花、陈艳玲、陈小珍在一起,不大和我说知了,也彻底不再来我家了。因为一炼铁,各家的锅啊盆的,凡是沾了钢的铁的,几乎都拿去炼了,虽然从没见炼出块像样子的好铁来——这话是任谁也不敢说的。为此,赵小朵很着急,她不好意思托别人问,就自己去问,问完了回家将门“哐铛”一声甩上,趴在炕上哭。我问:咋了?赵小朵说:还能咋,麦根不要你了,你没人要了!啊哈,呜——我一边外往走,一边拿眼斜她一下说:你哭吧,如果你哭哭老根就来娶我,那你哭死,我们就幸福死了。你再到大队部哭哭、到地里哭哭、到会上哭哭,咱们高粱粒子比球大、半年赶英超美、提早进入共产主义了。那不但我们向阳大队,整个县,全国人民都得感谢你。将你的照片弄个框子,挂在墙上,冲你背语录。
赵小朵闻言顾不得哭,跳起来捂着我的嘴将我摁到墙上,说:死妮子,你不要命啦。我打开她的手:反正不是不要命,就是不要脸。
怎么会,他不要我,自然有别人要,连后街上麻脸歪嘴的大麦娘都有大麦爹要,我就没人要了?我甩开赵小朵,步出家门。那时候人人求上进,个个争英雄。这个英雄、那个模范层出不穷,到处一派热火朝天,一会儿亩产高梁一万二,一会儿亩产棉花一座山,不过,这个,离我很远。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反正,没想当英雄,也没想嫁给老根,当然,赵小朵要我嫁,我也嫁,无所谓。
可赵小朵几乎天天冲我说一遍或几遍“麦根不要你了,你没人要了”,说得我突然想起,我还有自尊心这么回事儿。于是有一天,晚饭后,在赵小朵一边说我没人要一边一只腿踩在灶台上涮碗时,我大声喊:别喳呼了,我去问老根,他是不是不要我了,他不要,有人要!赵小朵看我真要出去,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喊:哪儿去,别出去丢人现眼了,人家不要你啦。
我往东走,一会儿就走到大炼钢铁的炉院,老根正在同陈小珍说话,我拢起嘴,大声喊:老根,过来,我有话问你。老根朝我这儿看了看,又跟陈小珍说了些什么,而后朝我走来。我拉着他胳膊出了院门,一直拉到牛棚南边儿。我问他:老根,你为什么不要我?老根眯起眼,朝远处看。我推了他一把:说,你为什么不要我?我有什么不好?再说,你在我们家吃了那么长时间饭。老根低下头,看着脚尖:不是我不要你――― 我说:你是不是嫌我长是不好看,不如陈小珍脸白?老根红了脸:不,不是。我说:不是就好,模样嘛,其实一厘一厘(渐渐)地就看顺眼了。老根:不是,不是。我说:好啊,不是好。走。我重新拉起他:走,到我家跟我娘说去,就说你愿意娶我,要不就说不是你不要我,是我不喜地跟你。老根被我拽着,滴里卜楞往前跄,走到我们家门口。老根说:我不能进去。我问他为啥,老根说:我不娶你,也不娶陈小珍,我是“炼钢英雄”、“种田能手”、“养牛先锋(忘了,老根早已不在家住了,住牛棚,养着队里的牛马)”,我不想娶媳妇,娶了媳妇拖后腿,让我啥也干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