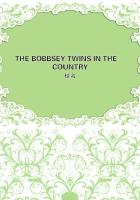尽说多才侬第一,第一多才,却是终身疾。
作赋吟诗俱不必,何如守拙存诚实。恰怪今人无见识,文理粗通,自道生花笔。那见功名唾手拾,矜骄便没三分值。
右调《蝶恋花》
天下最易动人钦服的是那才子二字,殊不知最易惹人妒忌的也是那才子二字。这为什么缘故?要晓得才有两等,有大才,有小才。那大才除却圣贤,没人敢及。如今只不过有几个小才的人,却自己认做了一个大才。那些有耳无目的,也道他是天下第一个才子,他便全无忌惮把那才子的身分使出来。倘遇着拙的,或者受他笼络了;若遇着不相上下的,不惟不肯受他笼络,还要笼络他起来。这个还是小事。万一两不相容,这个争强,那个夸胜,免不得别生计较,安排网罗,侭有家破身亡的。
这等看起来,那才字竟是起祸的根脚,送命的病源。常记古人说得好:“恃才妄作,所以取祸。”怎么世上的人再不肯把这八个字体贴一番。假如有十分才的,藏了五分的作用,有五分才的藏了四分的作用,把那骄人的念头,放荡的情怀,一一收拾起来,那见得便不是个才子。即看古人,那虚心的,便受了许多用;那弄聪明的,便受了许多累。可笑今世略做得几句歪诗,便道是个才子。终不然圣人说个才难二字,古时竟没一个吟诗作赋的人么?在下这段说话,看官不要认做小说的引子,直是进学问保身家的劝世明言。看官若不信时,听在下细细讲出一段故事来,便见得才是不足恃的,不要十分看重了。
话说明朝景泰年间,山东兖州府有一个秀才,姓吕名辉,表字彩生,年纪六旬左右。妻室卞氏,早已亡过。单生一子,取名文栋,表字云奇,年方十四岁。论他丰姿,虽不比潘安、卫筁,还在清秀一边;独有资性,却是愚钝不过。莫说作文不能够成篇,若念起书来,也有许多期期艾艾的光景。彩生因是晚年所得,珍爱非常,把他附在一个邻馆读书。
那馆中有两个同窗,一个大文栋两岁,名唤曾杰,一个小文栋两岁,名唤曾修,是个同胞兄弟。父亲曾士彦,与彩生最相契的朋友,彩生知曾氏兄弟好学不倦,要文栋去做个切磋琢磨的良友。谁知甚不相得。这是什么缘故?原来曾杰却是个才子,那曾修又是个神童,不消说举业精工,就是诗词歌赋,件件皆妙,只因自己聪明,再不肯轻易与人相处。他道”我们这样才情,就是颜回子贡,也不肯多让,怎么如今那些卑卑不足数的,要与我们做起朋友来?只是来者不拒,便是我的度量宽宏了。”更有一件,最喜戏谑。总是先生,也要让他三分,那文栋不消说是他们取乐的东西了。文栋识时达务,并不作声。
一日先生不在,偶然到间壁三元阁游玩,只见壁上粘着一张斗斋图,图上刻着斗母心咒,下面注云:“不时念之,求聪明得聪明,求富贵得富贵。”文栋腹中,虽是有限,料想这几个字还解说得出。当下见了,十分得意。那富贵二字,到是缓着,聪明二字,却是目前的急务,怎好当面错过。忙去寻个道士,取讨图式,又叫他教会心咒。
遂到家向父亲说了,请〔了画师〕绘起一尊斗母,朝斗焚香礼拜。如〔缺七个字〕然有些应验。虽不能胸罗锦绣,那记诵之功却颇来得。
其年正是科举的年分,宗师发牌考试童生。彩生初叫文栋应应故事,早已不肯高标了。独曾氏兄弟,双双得意。文栋却也有些志气,恐被曾氏兄弟笑话,不肯再到馆中,止在自己家里发愤读书。过了一年,渐渐笔底有些活动,可以成篇。恰考期将近,彩生又叫他去应试。这番不敢浪战,府县里俱用个小小分上,便也搭上一名宗师。宗师那里虽不是个长鎗手,万一图个侥幸,也未可知。忙忙的买了进场糕果之类。那包糕纸上,却是抄写的一篇文字。文栋看去,圈得甚是热闹。他也不管好歹,暗暗的记在心上。到明日进场,那第一题恰好就是包糕纸上的题目。他便不劳费心,一笔挥就。那第二题,又是平日读过几篇文字的,也就东凑西补,竟做了倚马之才,不消过午,交卷上去。宗师看见,遂叫取来面阅,大加赞赏。以后众人陆续交卷,候齐一牌,出院归家。把此话述与父亲知道,十分欢喜。又过了四、五日发案出来,果然取在第五名。到谒圣这日,那些备酒拜客一应事体,俱不必细述。
且说曾家弟兄知道文栋进学,心中甚是疑惑。曾杰道:“不信吕家儿子学问这样好了,想必是夤缘来的。”曾修道:“明日且拉几个朋友,叫他面会,其胸中有无,便可瞭然。”
曾杰道:“此言有理。”遂写帖订期,明日面课。谁知文栋却有个藏拙之法,因立出三件主意来。那三件,第一件就是:不与文社他道:“文社虽是以文会友,极正经的事,然而终究是有损无益。假如几个朋友相聚一堂,闲谈戏笑的时节多,吟哦动笔的时节少。纵使做得一两篇文字,不过是应故事而已,到不如窗下息心静虑,还有些奇思幻想。这个尚算是完篇极好的了,更有不完篇的,鬼混终日,到散场时候,却道容明日补来,依旧窗下去抄撮哄人。又有一件,朋友本来是互相参考,是非得失务要大家指点出来,独有一辈刻薄的人,面前极口赞扬,背后又换了一副口舌,竟做笑柄传播。依我看起来,那些朋友互相饮啖一日,名为文社,其实是个酒会。何苦费了钱财,买人的轻保因此立意不与文社。”那第二件,却是:不拜门生他道:“拜门生是个挂名读书的勾当。若真正读书的,却也不消。怎么是挂名读书的勾当?只因自己学问荒疏,惟恐考试出丑,要借公书揭帖做个护身灵符。偶然钻刺,考在前列,便好做个名士模样。还有一等好事的,打听人家有些词讼,便去揽与老师讲个分上,他就做个居间,得些抽头谢仪,以为养身之法。就是那做老师的收门生,也未必是一概相待。倘然收个富门生,平日奉承周到,或者还肯用个名帖,印个图记,到那里荐扬一番。若遇穷门生,平日没有交际,凭你真正才同子建,总不在他心上,可不是有名无实的事,因此也不拜门生。”
那第三件,却是:
不应小试
那不应小试又是为何?他道:“观风季考,总是套子,那有真正怜才的意思!况考试未定日期,这些乡绅的书帖已是挨挤不开。及至发案,少不得照依书帖,胡乱填〔去〕,那有学问的,未必列在前面。况我腹中又极是平常,怎夺得人过,越见得本事低。伴人过世了,到不如不去,也还藏拙些。因此又不应小试。”他有这三个主意,一切外事不管,只是自己用功而已。有一首《勉学诗》为证:夜半邻家织未休,梦回明月照床头。
披衣更起挑灯读,莫使男儿让女流。
且说曾杰弟兄,见他不肯来,只得央别个朋友去拉他。
他便把三件的短处,虽不敢尽说,却也微露其意。那朋友见他立意不肯,遂别去,述与曾氏弟兄知道。曾杰便大怒道:“这样不堪抬举的,你自己做不出文字,不来也罢,怎么背后谈人是非!”原来曾杰弟兄,这三件事是极喜做的,只为自己是个才子,要与人较量长短的意思。当下文栋这几句,也是大概论的,曾杰认做讥诮他,便要寻事与他计较。遂细细打听,知道抄写文字的缘故,连忙报与学师。
大凡人家子弟进学之后,就要备贽仪相见学师。那贽仪多寡,却有规则,分为五等。那五等,却是:超户上户中户下户贫户那超上二户,不消说要用几十两银子,就是中下两户,也要费几金。只有贫户,不惟没有使费,还要向库上领着几两银子,名为助贫。这通是要学役报的。文栋家事本是平常,那下等户却是可以报得的。彩生要便宜,竟报在贫户里。那助贫银子,虽然尚未到手,眼见得学师的贽仪,已做了乌有先生。那学师正要缉探文栋的家事,忽听曾杰之言,十分中意。等曾杰别过,忙唤学役,道:“吕文栋却是大富之家,场里文字也是买人代笔的。你这大胆奴才得他多少银子,却来朦胧我?”责骂一场,遂叫他立刻拘来,当面作文。若有推托,就要参到宗师那里去。
那学役忙到吕家,与文栋相见,把此话一一述与他知道。
文栋大惊,与父亲商议。已知学师要贽仪的话头,只是不好搪突。遂再三央及学役,求他在学师面前婉转致意:“秀才作文,也不是什么奇事,只求略宽几日,就当面会课,尽自不妨。总望老丈周旋了。待事完之后,我自重重相谢就是。”那学役无可奈何,只得回复学师。学师大怒,明日又差人去拘唤。文栋推脱不得,勉强随去。是日出了三个题目,文栋只做得一篇文字,却又不成个片段。学师看见,知曾杰的话一些不差,便要做角文〔书〕,参与宗师。
到亏学役再三解劝,方息了这个念头,只是要报在超户里边才祝彩生思想,料来货不正路,必然强不到底的,只得变卖家伙,向亲友抵借,完这一件事体。那些杂费,比着众人报超户的,反多一倍,方得了事。
谁知事便完了,彩生为这恶气,又急了一急,生起病来。
不上几日,竟凑了令郎之趣,已是丁忧。文栋大哭一场,买办棺木,开丧断七。忙过月余,这边才得完局,那边讨债的又是接踵而至。他们见彩生已死,惟恐淹在后边,没处取讨,因此急急催促。文栋受逼不过,只得把棺木权厝祖茔,卖了住房,清还众人,自己到三元阁借祝一日,在阁上读书,正读得有兴,忽见一人身穿阔服,走来和文栋相见。叙罢姓名,又仔细看了一回,竟自作别。
原来那人姓卜名升,表字君辅,是本地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哥哥,名唤卜昊,已是去世两年,遗下一个女儿,小字淑仪。
临终的时节,托在卜升,要择个快婿,以配此女。
那卜升善于风鉴,凭着这双铜睛铁眼,做个的当媒人。是时,偶到三元阁烧香,看见文栋,知道不是落寞之人品,便十分中意,就托道士,要他撮合。道士领命,随将此意向文栋说知。文栋辞道:“极承美意,但我在丧中,此事不好行得。况且囊中乏钞,无物可聘。即烦老师为我道达。”谁知卜升的意思,甚是不然,道:“虽是丧中,只要聘定,我侄女年纪尚小,还可待得一两年。等他服满之后成亲,极是得宜的了。若说无物可聘,一发不消虑得。一应使费,都是我出,一毫不消费心。”
道士听罢,却把此言再三劝文栋成就。文栋也不敢过辞,惟恐推脱,没有这般好主顾,便自应承。那卜升见说允诺,随即择日行聘,不题。
且说卜昊就是曾杰的姑夫,知表妹是卜升做主,定下文栋,急把文栋的短处,去诉与姑娘知道。那姑娘听得,竟与卜升大闹起来,道:“你哥哥怎样托你,你却寻个穷人来搪塞。你道我是个寡妇好欺负的么?”卜升道:“嫂嫂,你不要疑心坏了。
我为侄女十分在意。难道自家骨肉,到要他不好?那吕生眼前虽穷,人品尽好,决有功名之分,不是终身落寞的。我这双眼睛断不看错。”曾氏道:“你的话越颠倒了。那吕家儿子,有名是个蠢东西。你说功名两字,天下若有不要做文字的举人进士,半空里有顶纱帽挂将下来,只要把头接上去,或者轮着他了。总使这等,还恐他没福消受哩!你自夸眼睛看得准,怎么再不见有个举人进士,是你相过来的?你这话就哄三岁的孩子,也哄不过。在我跟前捣鬼做什么!如今我总不愿举人进士做女婿,须怪我得。”卜升受闹不过,只得道:“嫂嫂,何须闹得。
待我退了,另择个人家就是。”曾氏听了此言,方才住口。
卜升思想:“我起先再三情愿,如今怎好改得。除非目下不要说起,日后竟把我的女儿配他罢!”原来卜升也有个女儿,小字琼枝,与淑仪同年,只小得两月。其姿容态度,女工针指,淑仪是万不及一的。卜升正要择个佳婿,因记哥哥嘱咐,欲先完侄女之事,然后轮到自己。谁想嫂嫂不愿,正凑他的便了。
当下卜升只得又择个富家,替侄女完姻。不料那家为了官事,费得一空,已是穷到极处,就〔是〕岳母的私蓄,也渐渐弄去大半。后来无处说骗,思量本地不好居住,逃到别府,求乞度日。此是后话。
正是:
昔年事事话风流,肯信莲花唱未休。
独是豪华心不死,梦中犹到旧门楼。
且说文栋,倏忽过了三年,已是服满,便该应试了。
适值科举的年时,免不得又要图个侥幸,只是包糕纸上今番没有文字,却要句句出自己裁,早是稳稳的无望。独有曾杰弟兄,依旧双双前列。文栋甚是气闷。他的意思,没科举到是安分守己,也不指望举人进士,也不以为意。惟恐遇着岁考,把个前程做了完璧归赵。那时不惟被人耻笑,可惜一个家事为这秀才已弄得干净,况父亲的性命又送在里头,倘或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怎处?心上正是忧愁未了,忽见道士同着卜升走来,文栋遂上前相见。那卜升知道没科举,便安慰两句。又道:“足下可有兴考遗才么?”文栋道:“正科举尚且艰难,何况遗才,一发是海中摸针了。”卜升道:“读书人莫要惰了志气。你若这等畏缩,怎得个出头日子?你还去考,我与你央个分上,必然取出来的。”文栋本无此意,见卜升说话谆谆,便道:“极承指教,怎敢违命。”卜升又劝勉几句,一同道士出来,遂去打点寻分上的事,癩候考期了。那文栋也便发愤读书。
到了考试这日,竭尽心力,做完文字,出场到寓,静听好音。这番果然不虚所望,炔上〕一名。文栋大喜,知是卜升的缘故,遂央道士去致谢一番。原来卜升的意思,一来得阿坦有个进步,女儿便终身有靠;二来要在尊嫂面前好夸眼力高强,应了不落寞的说话。因此,望中的念头,文栋只有五分,卜升到有十二分。随又取出三、二十两银子,托道士送与文栋为进场盘缠使费。文栋十分感激,因自想道:“我虽是他侄婿,却怎么这等周到?我晓得都是岳母教他送的,终不然做叔翁的肯如此用心么?”再不晓得其中缘故。
当下即便收拾起身,来到省中,寻个寓所。一眼瞧去,那贡院间壁有个道院。文栋道:“到是道院幽雅些,况我又没个仆从,连饭也吃了他的,一总送他几两银子罢!”遂走进去。
恰好有个道士看见。施礼已毕,文栋就把要租寓的意思说了。
那道士道:“小房俱有相公们住着,惟恐不便。只有斗母阁上,尚空一间在那里。”文栋听说斗母阁,先是喜欢,朝夕拜祷,有许多便当。遂叫他引去一看,十分中意。把行李搬上去,又将寄膳之意说知。道士也自应承。从此在内读书,颇觉自适。
一日,出来朝礼斗母,只见有两人走来,劈面相见,各吃一惊。这两人不是别个,就是曾杰、曾修。他的寓所也在斗母阁上,怎么两日不曾看见?这有个缘故。那斗母阁有五间,中三间供着斗母,东西两间却是把板隔断,望不见的。文栋又是闭户默坐,不十分出来。曾杰弟兄又是时常访友,不十分在寓。
以此连日不相闻问。当下相见,虽是大说几句寒温套话,却是各有一个意思。在文栋知道先前这些事体,俱是曾杰做的首尾,因畏他是个奸险人,不敢发作。在曾杰不惟欺他无用人物,未免良心发现,也有些腼腆。故此淡淡相叙,不甚密切。
自后,文栋每出朝斗,曾杰即便窃听,惟恐有诅咒他的言语。谁知文栋祷告不过是保佑弟子场中得意,预示题目这几句,更无别说。曾杰道:“左右如此,我且耍那蠢物一耍。”竟私下拟了题目并策论表判之类,写得端端正正,压在斗母面前炉下。自己十分快活,道是取乐他的妙法。恰遇文栋又来朝斗,看见炉下纸角,取出一看,却是预拟场中的题目,心中惊喜相半。其惊的意思,只道斗母在梦中相示,不想明白写出,这样灵感,那得不起人敬重;其喜的意思,道是场中有神道相助,举人稳稳的捏在手中了。遂手舞足蹈的到窗下寻些底本,挪凑停当,细细读熟,一字不敢遗落,只有曾杰暗暗笑他罢了。此话不题。
单说试期已到,那些有科举的秀才,纷纷进场,各逞英雄,思量鏖战。少顷,传散题目。不道文栋又遇着包糕纸,与曾杰所拟的一字不错,便满怀得意,一笔挥就。那曾杰到吃了一呆:“我无心戏他,谁想到作成他的机会。”幸亏曾杰是个才子,虽是不曾打点,也不在心上。做完文字,自己看了一遍,便道:“我今科必中解元,决无他虑的。”交卷出场,“甚是得意。
回到寓所,只见曾修也出来了。问他的文字,曾修便念与哥哥听。曾杰道:“我道今年解元,必定是我了,那晓得又被你夺去。”自此三场之后,曾杰、曾修各怀着解元二字,竟住在官所,癩候捷音,只有吕文栋依旧回到三元阁去。因有题目这段事情,口中虽说轮不到我,心上却也做七八分的指望。
过了几日,放出榜来,第一名解元竟是吕文栋。那些报捷的挤到三元阁上讨赏,文栋到没个主意。适值卜升知道,连忙过来,招驾过去,连文栋也请他到家住下。一切事体,俱是卜升支持,不费文栋一毫的心。文栋忙忙的拜房师,见座师,祭祖拜客,甚是有兴。此事且搁过,无暇细述。
再说曾杰、曾修这样好文字,为何到在孙山之外。原来房师中意曾杰的卷子,立意要中他解元;不料又有一个房师中意曾修的卷子,也立意要中他解元,互相争论,竟口角起来。别房的房师知道,忙过来问其缘故。遂取这两个卷子细阅,真的不相上下,定不得第一第二的。况且是个同经,一个取了第一,少不得那个要取在第六了,因此两不甘服。那个房师道:“二位年兄,本是同僚好友,怎么为着两个门生致伤和气。取了那个,这位年兄不服;取了这个,那位年兄不服。依我愚见,这两生具如此美才,那怕不登高第,就暂屈一科,也是不妨,不若放过,另取一卷罢!”遂向众卷内另抽一卷,揭开看去,也自尽可做得解元的。那两个房师也便消释,竟将这卷中了第一。
及拆起号来,却是吕文栋。后人有诗讥诮曾杰,道:为人切莫恃多才,也得天公照顾来。
多少心机无用处,总成别友似神差。
当下曾杰、曾修见自己不中,闷闷的归家。更自一件,自己不中,到也罢了,只有文栋,向来看不上眼的,如何到中了解元,可不是试官没眼么?且又懊侮自己不是,这几个题目,为什么自己不打点一番,却送与别人受用。未免日日忧郁,竟成隔气的症候。曾修再三相劝,也只好在耳边过去,怎能解得心上的事来。勉强调治,才觉轻可。
及至挨到下科,不料父亲曾士彦又不愿做封君,另投在别人家做公子去了。曾杰弟兄大哭一常只得向学中报了丁忧,少不得又要迟上三年。那曾杰一来功名心急,二来为父丧,终日哭泣,忽然旧病复发,医治不好。可惜锦心绣肠,变个〔陈〕腐老儒。只有曾修后来依旧中解元,会试不第,遂选了无锡知县。到底为着恃才二字,得罪上司,被上司参劾,罢职而归。
此是二曾的结局了。
如今且说吕文栋上京会试,寻了寓所安顿。那寓所间壁已先有一人在内,也是来会试的。文栋道是同志,思量与他做个朋友。不料那人再不在寓的,也不见他念一句书。日日归来,便听得他喜笑的声音。文栋不知什么缘故,未免钻穴相窥起来。
只见他对着一个笔孔,在那里笑,却又把来藏在一个皮匣内,再不肯轻易放在桌上。原来那人姓纪名钟,徽州人,与会场的房师是个亲戚。那房师平昔受了纪钟的恩惠,许他中个进士相报,因此与他几个字眼。纪钟把来放在笔孔内,心中十分得意,渐渐露出小器易盈的光景。当下文栋看见,一心猜去,必是会场的关节。
思量要窃他的,却没个机会。又自转道:“且慢慢的算计,或者可以到手。”遂候那纪钟出去,便过来与那守寓的小厮闲话。有时叫到自己这边来,把些东西与他吃;有时送他几个钱。
看看相熟了,然后问他道:“你家相公时常好笑,这是什么意思?”那小厮道:“我也不知。但见相公时常对着笔孔,便要笑将起来。”文栋道:“这个笔孔带在身边的,还是藏在那里的?”小厮道:“相公恐怕遗失,被人瞧见,不带去的,只藏在一个皮匣内。”文栋道:“你去把我一看。有什么好笑的话,待我学了,也说一个与你听,可好么?”小厮道:“皮匣是锁的,钥匙相公又带去,却是取不得。”文栋道:“待我过去看看何如?”遂同了小厮,走去看了锁之大小,然后寻个捵子搠开。取出一看,见里面有一条小纸,上写着三个大字在第一行,余无别话。文栋记了,原处放好,锁着,对小厮道:“我道是个好看的,原来没有什么。你家相公回来,不要说起。”小厮应允。
如此又过月余,场期已近,文栋即忙收拾进常照依笔孔上,如法做去,果然有些灵验,已高高的填上一名进士。但纪钟又是怎的?只因试官见了文栋的卷子,道已合式,必然无疑了。不料纪钟的卷子,题目上有一个错字,监场的早已将他高标出来。那试官再解说不出文栋的缘故,只道纪钟转做人情的。
及问纪钟,又毫不相干。况此句话,又说不出的,不好问得文栋,竟做个朦胧过去罢了。文栋到白白的中个进士。又殿试二甲,选了部属。他就出个疏,告假归娶。圣旨准奏,钦假还乡,娶后补官。
一路甚是风光。到了卜升家中,俱请出来拜见。遂央道士说知钦假归娶之意,卜升也就择吉成亲。当夜卜升夫妇受礼已毕,更无别人相见。文栋想道:“我那岳母,怎么不见?决因寡妇,不便出来,故叫叔翁夫妇受礼了。若到三朝,必然看见的。”及至满月,也不见影,心上疑惑,问那琼枝,却又含糊不应,正不知怎的缘故。
一日,出去拜客,看见一个命馆,招牌写着“铁口最准”四字。文栋一时高兴,便把八字与他推算。那先生道:“这定是发过,老先生的尊造,不要寻常看过了。但少年必然刑克父母,到二十岁上,方有际遇。交三十五、六,便历仕显宦,得圣上恩宠。寿原也到古稀之外。”文栋见他讲得有些相对,又把夫人的八字与他一推。那先生又细细的看去,说道:“这个不要怪我胡言,是个至苦至穷的八字,只恐还要到求吃的地位。”
文栋口虽不语,心上有些怫然,道:“通是江湖套子,一些不准的。怎么我做了官,夫人到要求吃起来?”及归家说与夫人知道,夫人笑了一声道:“这个果然不是我的八字。”文栋吃惊道:“怎么不是夫人的!难道初行聘之时,另有替身不成?”
夫人道:“这是我家姐姐的。我虽与同年,却是某年某日某时生的。”文栋道:“这又解说不出了。既是令姐,如何又是同年?怎么与我成亲的,却是夫人,又不是令姐?”那夫人道:“这不是我家的姐姐,是伯母那里的姐姐。”因把其中缘故,并如今流落的话头,细细说了一遍。文栋道:“原来如此,怪道令尊如此用心。我还道是你令伯母的意思,一向错认了叔翁,谁知却是岳丈。今日方才把个大梦醒了。只是你家姐姐流落在外,怎么不寻了回来?我忝在至亲,岂有坐视之理。”随即唤两个人,叫他四面寻访。后来寻到家里,亏了文栋,扶持他起来,将就过得日子。那曾氏深悔不听叔叔,致有出乖露丑这些事体,又感激文栋肯用亲情,日日祝颂不了。
且说文栋又将真八字与先生推算。那先生写了命限,排列五星,说道,“这才是夫人的命,与前日看的大不相同。”文栋方信这八个字竟是个圈子,凭你上智下愚,穷通寿夭,俱跳不出的。每每劝人安分守己,不要妄作妄为。又叫人敬重斗母,吃些斗斋,以免罪愆。
我这回小说,不是说才子不好,是说不存善心,便无好结局了。即看曾杰因一点妒心,害了文栋,不惟自己一个解元,移在文栋身上,连这性命也早早缴还阎府。有人说道:“曾杰既拟得这几个题出,倘然自己打点一番,或者依旧中了。”殊不知曾杰的文字未尝不好。这几个题目,直是天使其然,照顾文栋的。故我不谓之人拟,竟谓之天拟也可。又有一说,不是文栋朝礼斗母,曾杰也不起戏谑的念头。总有这个念头,也未必做出,这个直是文栋心上拟出来的。故我又不谓之天拟,竟谓之(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