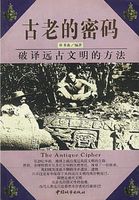刚从严冬的哈尔滨返回京城,便惊闻诺齐克教授不幸病故的噩耗,心底顿生哀痛。几年前访学哈佛哲学系时听斯人杏坛高论、与斯人膝促会谈的情景倏然重现,仿如昨天。斯人已去,音容犹在,我该如何诉说萦绕于这去与在之间的记忆和伤感啊!在我的记忆中,诺齐克既是一位才华纵横、富有个性的知名教授,又是一位意志果敢、性情豪狂的自由思想家。而且,学术与思想、率性与理智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生动跌宕而又和谐一致。
一九九三年夏至一九九四年秋,我终于实现了期待已久而又一再延滞的哈佛访学计划。我选择了哲学系作为自己年度访学研究的基地。抵达哈佛的第二天,我便与罗尔斯、诺齐克两位教授取得联系。
讨教于二位名师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十分幸运的是,两位教授在这一学年都有课程开设。系办公室的秘书告诉我,这是罗尔斯教授离休前的最后一课,而诺齐克教授也将在下一学年去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讲学。因此,我在选听罗尔斯教授的“政治哲学”一课的同时,也选听了诺齐克教授的“耶稣、佛陀和苏格拉底”和他为研究生开设的人权问题的seminar。诺齐克教授的本科课程让我好奇。他的成名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是我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最后一节里所叙述的主题内容,去哈佛之前,我就想找机会向他证实一下我在拙著中对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解程度,现在却听他在课堂上侃侃而谈先知圣人们的人生哲学,其间的反差对照自然让我略感诧异:这位曾经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锋芒毕露、论辩强悍的现实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自由思想者,怎么会突然钟情于先知圣人的人生哲学智慧,显出如此深厚的理想主义终极关怀呢?
通过我与他一系列被他戏称为“系列会谈”的学术交流,我才慢慢明白这其中的原委。我们的第一次会谈是在他开课后的第三周的“办公时间”(office hour)进行的。在我向他报告我对他有关权利资格和社会正义的思想理解之后,他告诉我,有两点是正确无疑的:第一,他的确秉承了洛克一海耶克一路的自由主义传统,即:坚决维护个体自由权利、尽力限制国家政府(对个人)的权力干预,并坚信这是不可退却的自由主义原则立场。第二,他与罗尔斯教授的论争既具有“家族内部”之争的性质,也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分歧,至少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如此,但他不同意我把他和早期的卢梭扯在一起,甚至表现出对这位法国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的某种厌恶。
他也不赞赏我把他与罗尔斯教授互比互论的做法,并反复告诉我,他与罗尔斯的分歧并没有我(以及学界许多人)所想像的那么大。
他反对的只是后者对国家制度之正义安排的过分偏重,但绝不反对后者关于正义之基本原则的阐释,如,个人自由(权利)优先的正义“第一原则”。他给我详细讲述了他写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的动机和经过。一九七零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旋即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轰动性影响。对于诺齐克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来说,刚刚跨入被誉为“美国本土哲学之摇篮”的哈佛哲学系,便敏锐地感受到了某种学术挑战的契机。他放下了手头已近脱稿的大部头哲学专著《哲学解释》的写作,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迅速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年轻的他向罗尔斯叫板:凭什么理由给予国家以如此大的限制个人权利的权力?这种国家的权利限制是否正当合法?正义是否必须以牺牲部分个人的权利为代价?如果说国家的合法性只能由她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来证明,那么,罗尔斯意义上的国家究竟是一种正义合法的国家?还是一种正义道德理想的乌托邦?无政府状态不利于现代民主国家的生存,难道超“最小国家”(the minimal state)的乌托邦式国家就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这一系列的疑问均来自罗尔斯的社会正义伦理理想与诺齐克的最充分个人权利与“最小国家”的社会道德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和冲突。
诺齐克是坚定的,也是成功的。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年轻和初来咋到而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尽管罗尔斯既是他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学长和老师,又是他哈佛哲学系的长辈同事,并且正处在如日中天的颠峰状态。他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是最早向罗尔斯发起挑战的代表性著述,而且和《正义论》一样,都获得了美国“卡巴图书奖”,只是时间上晚了四年,这是美国哲学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年,年仅三十六岁的诺齐克不仅成为了哈佛的终身讲座教授,而且成为了哈佛哲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随后,他又主持了《哈佛哲学评论》杂志,接连出版了《哲学解释》(1981)、《合理性的本性》(1993)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哲学著作,很快便跻身于当代一流哲学家的行列。
诺齐克是幸运的,也是智慧的。他是一位天生的自由思想家和真正的“爱智者”(哲学家)。他有幸在普林斯顿这一全美最好的分析哲学重镇接受分析哲学的训练,又有幸成为哈佛大学哲学系这个被誉为“美国本土哲学之摇篮”和自由主义哲学堡垒的特殊哲学共同体的一员。除了他和罗尔斯之外,很少有人能够享有这样的学术机缘。但更为关键的是,诺齐克自身具有他同代人少有的趁“机”化“缘”的天资!他思想敏锐而洒脱,在他的课堂上,几乎任何一个提问,都会成为打开他思想喷泉的闸门。我清楚地记得,在他主持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湖seminar上,一位学生对J.J.汤普森《权利的领域》提出其“领域”限定的疑问时,诺齐克竟然就人的权利如何不能人为地给予限定漫谈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不断博得学生们的啧啧称赞,以至课后学生们还围着他喋喋不休。然而,诺齐克还有着不易为人们注意的一面:他执著于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自由辩论风格,却从不失对他人和对手的尊重。我亲眼见到他抢着为罗尔斯教授抱书、掺扶罗尔斯上楼的情景;也见到他一边啃三明治,一边听学生反驳他自己的观点并不断点头的情景。有一次在我谈到有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时,他甚至用征询的口吻向我提出:“万,可否下一次让我的夫人一起参与我们的会谈?她一定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我知道,他的夫人曾经是前东德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员,肯定在这方面卓有洞见,诺齐克的提议是自然合理的,但我仍然对他如此谦和地提议感到些微吃惊:这姿态似乎与他“一贯的”逼问方式不吻合。然而,这也许才是真正的自由思想者的品格和姿态!
“哈佛哲学”的奠基者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真正的哈佛是自由思想和思想自由的福地。诺齐克以自己的哲学方式追循着这位先辈的足迹,以自由思想家的姿态自由而洒脱地走在思想自由的时代前沿。前年晚秋时节,我曾经重返哈佛作短暂停留,本想登门拜访他和罗尔斯先生的,不期这两位昔日的访学导师都住进了医院。哈佛哲学系的秘书告诉我,诺齐克教授的肠胃病已经发生癌变,想不到今年的严冬季节他就匆匆地走了。对于一位充满思想活力和哲学创造力的智者来说,六十三岁的年龄无论如何都不该成为生命与思想的终止符号啊!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在天国继续他关于耶稣、佛陀和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话题?以及他关于人权和自由的思想争论呢?
苍天在上,斯人可鉴!呜呼记之!
二零零二年元月二十四日深夜急就于北京西郊蓝旗营悠斋
(原刊于北京《财经》,2002年第2—3期舍刊。发表时略有改动,现恢复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