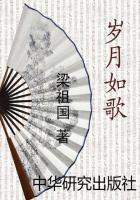陈言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朱小北和果青的关系却迈出了一大步。朱小北已经感觉离不开果青了,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使她痛苦。
她几次到果青租的房子去,在那里和他做爱。她没有想到自己是个如此放荡的女人,为了那种通电般的喜极而泣的高潮,没有什么事是她干不出来的。果青也变得让人认不出,那么凶狠、霸道,朱小北激动地感到自己被他一次次地占有、蹂躏,无比的陶醉。
她不由自主地喊,哦,哦,我是你的你的你的……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离婚!
“你离吗?”果青勒得她的肋骨咯咯直响:“你不离我就杀了你。”
“那我就吃了你。”
他们嘶嘶地叫着,脸兴奋得变了形。时间从来没有过得这样快,转眼之间就到了陈言回来的日子。朱小北忧郁得要命,简直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陈言回来后的第三天,出版社公布了分房方案的第一榜,陈言是个一居室。他立刻给朱小北单位打了电话,可单位的同事说她没来上班。陈言的心一沉。
其实陈言回家后就有所感觉,觉得朱小北变了,人发蔫儿了,总在愣神儿似的,这使他觉得自己一直被欺骗,必须和朱小北严肃地谈谈了。
朱小北下班回来陈言问她今天干什么了,她说买月饼去了,快过中秋节了嘛。陈言犹豫了一下,把一居室的消息告诉她,只见她眼睛亮了一下,亮光很快熄灭:“是吗,那太好了。”她只说了这么一句,没说别的。
晚上陈言画出一张一居室房间的平面图,给朱小北看,他想把门厅当客厅,把厨房的门改一个位置,脑子里有很多很多想法。
朱小北默默地看着图,微笑地点着头,陈言觉得她并没有听他说话。
“你想什么呢?”他问。
“我吗,”她顿了一下,“我想要是有两间就好了,一间太小了。”
“嗨,以后有了孩子再说吧。”
朱小北出神地一笑:“孩子,是啊,孩子。”
她温和的态度让陈言不安。上床后陈言在黑暗中和朱小北做爱,然后从身后搂着她,想象着他们怎么躺在自己的新家里。
“你困了吗?”他问她。
朱小北没出声。陈言默默地抱着她不动:“小北,你还爱我吗?”
她也不动。
“你怎么不说话?我在问你。”
“爱。”这一声“爱”就像是一声叹息那样。
陈言抬起手打开灯,朱小北慢慢翻过身来,两个人四目相对。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和果青见面了?”这句话终于说出来了。
朱小北眼睁睁地看着陈言,平静地反问了一句:“你说呢?”
陈言感到心咚咚咚跳得厉害,不知该说什么。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朱小北当然和果青见过面。说到底见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朱小北的平静。天哪,陈言真的有点害怕了。
经过清洁工两天的扫除,活动中心的窗子擦得透亮透亮,阳光把屋子照得明晃晃的,四下里耀眼极了。一盒盒装潢漂亮的月饼把门口的那张大桌子堆得满满当当,满屋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这些当年的领导干部可不是拿了月饼就完事,人人都要问朱小北一些问题,月饼是哪儿出的,什么厂家,质量和价格如何,好像要考察工作似的。朱小北答不上来,就推到小胡身上,说是他去买的。小胡一进屋就得回答许多人的问题,他告诉他们这是正经的杏花楼的月饼。
郑局长用手点着小胡的鼻子尖:“你个小胡,想蒙我哇!杏花楼在上海,你去上海买的不成?”
小胡干脆拉下脸:“人家美国的麦当劳有分号,咱们中国的杏花楼也有分号。”这下他招来了众多人的围攻,骂他滑头,搞假冒伪劣。有人当即打开盒子检验,品尝之后觉得味道还不错,原来是广东月饼。
隔壁的会议室里要举行一个中秋茶话会。朱小北发完月饼又忙着沏茶倒水,不少人到了该吃药的时候,需要凉开水,有人又嫌凉开水太凉,要温乎的,后来朱小北也弄不清谁要凉水谁要温水了,结果他们自己也把吃药的事忘了,都在专心谈着投机的话。
也有的老头儿满脸不痛快地溜达来溜达去,朱小北就问他们需要什么,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儿主动和他们说话,老头们就高兴了。
小胡忙得满头是汗,不时偷偷向朱小北做怪相儿,表示烦死了。可朱小北并不觉得,因为她在说话做事的时候心并不在这儿,她的思想在想着果青,想着陈言,想着未知的将来。她甚至觉得手上有事可干,忙忙碌碌的倒挺好。
下午活动中心安静下来,小胡提前下班走了,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只剩下朱小北一个人,守着十几盒没发出去的月饼。午后的阳光有些发白,朱小北的脑子里也白茫茫的。她想着和果青做爱的情形,想到陈言对她的感情,还想到了那个一居室。她要把墙涂成蓝色,果青喜欢蓝色,一想到和果青一起生活的可能,她的心里就掠过一股凉幽幽的震颤。
三点多钟,陈言的电话打断了她的思绪。他问她几点去奶奶家,要不要他到单位找她和她一块去。朱小北有点不耐烦,说:“用不着,我还不知道几点下班呢。”
陈言顿了一下,声音有点哑:“你是不是去找果青呀?”
朱小北冷笑一声:“对,那我就找他去,再见。”
挂上电话她的心情完全变坏了。她很想发脾气,可又没有对象,本来她可以立刻给陈言打个电话回去,可她克制住了自己。
也许她就该实话实说,告诉他她已经不爱他了。
朱小北准备去奶奶家,她挑了两盒月饼,就是说把她觉得不好吃的都拿出来,放到别的盒子里。自从上次为了她大闹一场,再到奶奶家她说话就很小心了,虽然那件事再没人提起,可她总感觉爷爷奶奶的关系有了裂痕。她偷偷地问过奶奶还生不生爷爷的气了,奶奶抿着嘴不说话。
“你会和爷爷离婚吗,会吗?”
张茹使劲戳戳小北的脑门儿:“你呀,就别再说疯话了。”
奶奶家已经有了三盒月饼,加上朱小北拿来的两盒就是五盒。
就月饼大泛滥的问题朱久学开始发表意见,意见逐渐上升为抨击,整个单元都充满他直通通的洪亮的声音。
朱小北躲到屋里看杂志,朱涛陪爷爷在客厅里说话,准确地说是听爷爷说话,丁亚兰帮奶奶在厨房里做饭,吃完饭陈言和她负责洗碗,每年中秋节都是这样。
天已经黑下来,陈言却还不露面。朱小北有点着急了,站在窗口往外看,她心里不相信陈言会生她的气不来,那绝不可能。
朱涛问:“小北,陈言怎么还不来?”
她说一会儿就来了,就跑进厨房,奶奶正在和妈妈说月饼的事。
中秋节家里总要剩下好多月饼,张茹当早点吃要吃好久,朱久学是一日也不吃的,因为他不喜欢甜的东西。张茹实在吃厌了,朱久学就批评她,说多少贫困地区的孩子想吃都吃不到。张茹说送人,朱久学又说她是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拿去打发别人,弄得张茹永远没理。
丁亚兰笑着说:“不想吃就别吃,可别勉强。”
张茹说她打定主意了,再不勉强吃月饼,朱久学爱怎么说怎么说,随他去。昨天她已经表明了这个态度,朱久学居然笑嘻嘻地说:“谁让你吃了,是你自己愿意嘛,爱吃嘛。”“小北,陈言怎么还不来?”奶奶想起来了,也问她。
一会儿的功夫朱小北不断地被家里人轮流问来问去,陈言呢?
怎么还不来?哪儿去了?她被问烦了,干脆说:“他不来了。”
话一出口她忽然明白这是真的,陈言真的不会来了。
朱久学对陈言说好来而不来大为不满,其实他并不真的在乎陈言这个人,只觉得这是对他的冒犯,他沉着脸背着手:“平时看不出来嘛,怎么可以这样!他有什么事情?”
“小北,爷爷问你话哪!”朱涛提醒女儿。
“别问我,得问他。”
朱久学一下发火了:“你是我孙女,我为什么不能问你?”
朱小北忍了又忍:“对不起,他没告诉我,我怎么知道。”
朱涛摆出和事佬的样子,说陈言来不来无所谓,我们一家人,老少三代都在嘛,这就叫团圆。看在儿子的面子上朱久学才不再纠缠了,可一顿饭却吃得别别扭扭。
饭后朱久学下命令每人要拿一盒月饼走,不然张茹要把月饼全部扔到垃圾箱去。张茹忍不住辩解,说她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每年的月饼都是她一个人吃下去的。朱久学就冷笑,说她的记性成问题了,昨天说的话今天就忘,是不是得了健忘症,要不就是老年痴呆的前奏。
这一套弄得朱小北的心情糟糕透顶。
这天晚上夜空中有一轮很大的月亮,使中秋节显得很完满。汪丽琴独自坐在家里,杜震出差了,也许去找他的女演员去了。她走到阳台上想看月亮,可月亮还被楼房挡着,她只能看到地下银白的月光和楼群的黑影。
汪丽琴的脑子里想着陈言,她已经感觉到陈言和朱小北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怎么了,不好了吗?她多么想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