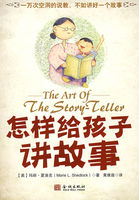病雪
幽谷拾光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用左手握紧右手,让响亮的鞭影不断抽打自己怯懦的思想。朝前走,莫回头,山的那边是水,水的那边是蛟龙出海根生的目光朝出站口扫了扫。出站口空荡荡的,只有一汉子在那里漫无目的地游动,一件汗衫斜斜地搭在肩膀上,露出漆黑而结实的肌肉。还在县农业局等候分配的时候,局长就同凤凰乡通了电话,乡里表示要派人来车站接。而出站口除了这个汉子别无他人,看来凤凰乡慢了半拍,还得多等一会儿。根生情不自禁放慢了脚步。而这时汉子却朝他走了过来,两撇乱糟糟的胡子上下一分,问道:“你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吧?我是凤凰乡的,跟我走吧。”说罢,汉子两只大手一伸,就将他手上、肩上的包裹全撸了过来。
他没有推辞。虽然凤凰乡的头头没来,但对于凤凰乡派来一个脚夫这一点根生还是相当满意的。卸下了沉重的包裹,根生备感轻松,步子不觉迈得大了些,好似对即将面临的生活又隐约滋生出一点儿希望来。经过马路的时候,汉子停也没停,没有丝毫犹豫就踏上了一条崎岖而坎坷的山路。
一阵凉意不自觉掠过根生的心头。难道他要去的地方落后得连马路都还没通上?于是他不禁试探着问:“这路,要走多远?”“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汉子头也不回。汉子蒲扇般大小的两张脚板像踩了风火轮,在根生前面飞快地转个不停。硬着头皮跟在后面的根生喘气不觉粗了起来。汉子察觉到了异样,说:“歇歇吧。”然后把包裹一古脑儿放在一株正在盛开的映山红旁边,从肩膀上扯下汗衫,搭在一块狰狞的怪石上,冲根生说:“来,你坐这儿。”待根生坐下后,汉子也一屁股坐了下去。
“像你这样自愿到我们山旮旯里来的大学生真不多见。”汉子盯着根生的眼睛在正午日头的照射下眯成了两条深深的沟壑。在汉子的眼睛里,根生分明看见自己正在逐渐变成一锭闪闪发光的金元宝。“饿了吧,吃点东西?”聬箸:恵汉子伸手在口袋里搜索了半天,掏出了一个铁硬的馒头。馒头由于长时间受到重压,已变得奇形怪状。汉子将馒头掰成了两半,将其中一半递了过来。根生摇摇头,表示不饿,但他的心里头分明在反问:“这玩艺儿也能吃?”
“也难怪,你们大学生都是在蜜罐里泡大的,这东西真有点难为你了。”汉子的话语里明显充满了自嘲的意味。
他把两半馒头扔进了窟窿一样的嘴里,接着根生的耳鼓里便清晰地传来了汉子尖利的牙齿切割坚硬的馒头发出的“咕咕”声,就像有一群蛤蟆在汉子的嘴里欢快地唱歌。
“我们泥腿子跟你们大学生是不是很难沟通?”汉子紧紧盯着根生,眼光里半是欣赏半是疑虑。根生本来想点头的,因为他觉得跟这个粗手粗脚的帮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他感觉这样又欠妥,便机械地摇了摇头。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汉子说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
根生没有搭腔,这时一种听天由命的念头在他脑袋里占了上风。
“那我们走吧。”汉子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抓起包裹,快步赶起路来。根生一步也不敢落下,紧紧跟在后面。大概走了二三十里山路,这时根生听见汉子说,“我们坐车走吧。”
坐车?根生这才发现他们已走到公路边。
根生觉得这地方眼熟,这不就是自己刚才出来的那个火车站吗?汉子大手一招,一辆桑塔纳轿车无声地滑了过来。
根生带着硕大的问号上了车。在车上,汉子对根生说“你们搞田径运动是不是也讲究热身?”
“嗯。”根生似懂非懂。“我们今天走的这几十里冤枉路也姑且叫它为热身吧。”不过,汉子顿了顿,“前几天也来了几位大学生,他们都还没进行完热身就走人了。”
轿车驶进了一个环境幽雅、造型别致的居民小区,缓缓地在一幢小楼前面停下。汉子将一串钥匙放到根生的手中,“这幢小楼以后归你住,跃层式的,怎么样?”根生握着沉沉甸甸的钥匙,满脸憋得通红——此时的他已经鼓不起一点勇气去打听眼前这个汉子究竟是谁了。
诗文并茂
选择
流水冲刷着河床时间冲刷着人群
带着流速的事物显示了生存的消逝性
我对眼前的事物有两种态度
一是勇敢地闯入
二是偷偷地溜走
但我不能让自己随便放纵
我举起了利斧
果断地伐倒自己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