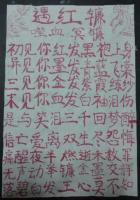现在,我的心境还处在悲痛的重压之下,这实在不是对此加以叙述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我的前途已经堵塞,我生存的力量已经耗尽,我一生的活动已经终结,除了坟墓之外,已经再也找不到任何安身之处了。我说的我越来越这样觉得,并不是我初遭悲痛的打击所致,它是慢慢地逐渐地形成的。要是我后面将要叙说的事故,没有朝我接踵而来,开始时把我的悲痛搅乱,末了又使我的悲痛增加,那我也许会立即就陷入上述的那种绝望的状态之中(虽然我觉得还不至于如此)。事实上,在我充分认识自己的痛苦之前,其间已隔了一段时间,在那段间歇时间,我甚至以为自己最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我的心事可以放在一切最纯真、最美好的事物上,用那个永远结束了的温柔故事,来慰藉自己。
我应当出国的意见,最初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或者说,我们是怎样取得一致意见,说我得换个环境,外出旅行,以恢复我的平静,甚至到现在我都不很清楚。在那段悲哀的时期,爱格妮斯的精神,如此深深地渗透于我们所思、所说、所做的一切之中,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主张归之于她的影响。不过她的影响都是那么不知不觉的,因此我也没有感觉到。
现在,我真的开始想起,过去我把她和教堂彩色窗玻璃联系起来的想法,就是一个预兆,预示日后灾难降临到我头上时,她对我起什么作用,这一预兆此时正映现在我的头脑中。在所有那段悲伤的日子里,从她举起手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起(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她就像是降临到我孤寂的家里的一位神灵。当死神来到我家里时,我那孩子气的妻子,就是在她的怀中含笑长眠的——这是在我经得住听这类话时,他们这样告诉我的。我从昏迷中醒来时,首先感到的是,她那同情的眼泪,她那鼓励和安慰的话语,还有她那温柔的脸庞,仿佛从更近天堂的静地,俯垂在我未经磨炼的心上,以减轻她的痛苦。
现在让我继续讲下去吧。
我就要出国了,这好像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了似的。现在,我亡妻会消亡的一切,都已埋入黄土,我只等米考伯先生说的“希普最后将被研成粉末”,然后就和移居海外的人一起动身。
由于特雷德尔(我患难中最关切、最忠诚的朋友)的要求,我们又回到了坎特伯雷,我这是指的我姨婆、爱格妮斯和我。我们依照约定,径直来到米考伯先生家。打从我们那次爆炸性的聚会以来,我的这位朋友,就一直在米考伯先生家和威克菲尔先生家辛勤工作。当可怜的米考伯太太看到我穿着黑衣服进来时,显然异常伤感。这么多年来的磨难,并没有把她的善良耗尽,她仍有着大量的慈悲心肠。
“哦,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太太,”我们都落座后,我姨婆首先开口说,“请问,你们对我建议的移居海外的事,仔细考虑过了吗?”
“我亲爱的特洛伍德小姐,”米考伯先生回答说,“米考伯太太,还有在下,还要加上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不但共同、而且各自也都考虑过了,考虑的结果,除了借用那位著名诗人的话外,也许没有更好的回答了,那就是:舟靠在岸边,我的大船已泊海上。”
“这就对了,”我姨婆说,“你们作出这一明智的决定,我预料你们一定会一切顺利,前途无量的。”
“特洛伍德小姐,你使我们感到极大的荣幸,”米考伯先生回答说,跟着看了看记事本,“由于你给我们经济上的帮助,使我们这只单薄的小船,得以在事业的大洋上起航。有关这笔经济的重要事务性方面的事,我又重新考虑了一下;现在我要求我开出的期票,分为十八个月、二十四个月和三十个月三期——毫无疑问,这些期票要按各种议会法案对此类契约的规定,贴足一定数量的印花——我原先提出的是十二个月、十八个月和二十四个月为期,不过我担心的是,这样的安排也许期限太短,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筹足所需归还的款项。我们也许,”米考伯先生说着,往房间里四处看了看,好像这间房子就是几百亩长满庄稼的农田似的,“在第一笔欠款到期时,收成不够好,或者是我们一时收割不了。我相信,在我们的那片殖民地上,我们的命运就是得跟那肥沃的土壤斗争,而劳动力有时是很难得到的。”
“期票的事,你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好啦,米考伯先生。”我姨婆说。
“特洛伍德小姐,”他回答说,“我们的朋友和恩人,给我们如此关心的美意,米考伯太太和我是十分感激的。我希望的是,这件事要完全公事公办,欠款一定得按期归还。在我们要翻开我们生命中新的一页时,正像我们就要做的这样,我们先退后一步,以便作不同寻常的向前跃进。这除了给我儿子做出榜样外,跟我的自尊心关系很大,因此要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样来作出安排。”
我不知道,米考伯先生最后说的“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样”附有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别人,现在或过去说这句话时,是否附有什么意思。不过米考伯先生对这句话似乎异常赏识,引人注意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样”。
“我所以建议采用期票,”米考伯先生说,“——因为它在商界使用方便,我相信,为此我们首先得感谢犹太人,不过他们自从有了这种东西以来,应用得太多了——因为这种票据可以转让兑现。不过要是更喜欢用借据,或者任何其他的票据形式,我也乐意采用其中的任何形式的。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样。”
我姨婆说,既然双方都同意无所不可,她认为,在这个问题的安排上,不会有什么困难。米考伯先生也同意她的意见。
“至于我们一家人,为迎接我们已知的准备献身的命运,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特洛伍德小姐,”米考伯先生有些得意地说,“我要求报告一下。我的大女儿,每天早上五点钟即去邻近一家奶牛场,学习挤奶的过程——如果那可以叫作过程的话。我那几个小一点的孩子,我也要他们去本城较为贫苦的地方,观察猪和鸡的习性,在情况许可下,尽可能作密切仔细的观察;为此,他们曾有两次差一点被车压了,结果让人给送回家中。说到我自己,在上个星期,我把精力都花在研究烤面包的手艺上;我的大儿子威尔金斯,则每天都拿了手杖出门,只要能获得粗鲁的牧人的允许,就白尽义务,帮他们赶牛——不过说来遗憾,由于人的天性使然,他也不常这样干,因为他总是受到警告,咒骂着不让他赶。”
“这一切确实好极了,”我姨婆鼓励说,“我想,米考伯太太一定也很忙吧?”
“我亲爱的特洛伍德小姐,”米考伯太太用她那有条不紊的神气说,“我不妨直说吧,现在我还没有积极从事和耕种及畜牧直接有关的各种活动,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在外乡彼岸,这两者都是要我专心关注的。跟下,我凡是能从家务中抽出一点时间,就给我娘家的人写长信,通消息。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对我说,不管她在开始时对什么人说话,最后总是要落到我身上(我想这也许是出于习惯吧),“因为我认为,应该把过去全都埋葬在遗忘中的时候,已经到了;我娘家的人应该跟米考伯先生握手言和,而米考伯先生也应该跟我娘家的人握手言好;狮子应该与羊羔同卧,是我娘家的人跟米考伯先生言归于好的时候了。”
我说,我也认为这样。
“至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接着说,“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年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在家里时,每逢我们那个小圈子里讨论什么事情,爸爸总爱问,‘我的爱玛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呀?’我知道,这是我爸爸对我过于偏爱;不过,在我娘家的人和米考伯先生的关系冷若冰霜这一点上,我当然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尽管我的看法不一定对。”
“毫无疑问,你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看法,米考伯太太。”我姨婆说。
“正是这样,”米考伯太太同意说,“当然,我的结论也许是错的,很可能是错的,不过我个人的印象是,我娘家的人和米考伯先生之间,所以会有这样一道鸿沟,追本穷源,也许是我娘家的人,担心米考伯先生要求他们在经济上作些通融。我不能不认为,”米考伯太太带着洞悉一切的神气说,“我娘家有些人,就是怕米考伯先生会要求借用他们的名字——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施洗礼是要照用他们的名字,而是把他们的名字签在票据上,拿到金融市场上去流通。”
米考伯太太说出这一发现时,那种洞察事理的样子,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这一点似的,这似乎使我姨婆颇感惊诧;她突然答道,“哦,米考伯太太,总的看来,我想你说对了。”
“米考伯先生就要摆脱多年来羁绊他的金钱桎梏了,”米考伯太太说,“即将在一个能使他施展才华的地方开始新的事业——据我看来,这一点极其重要,米考伯先生的才华特别需要空间——我觉得,我娘家的人应该出来,给这个机会增光添彩。我希望看到的是,由我娘家的人出钱举办一次宴会,让米考伯先生和我娘家人在宴会上会面;由我娘家的某个头面人物出来为米考伯先生祝酒,为他的健康和发达干杯,那米考伯先生就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带有一点火气说,“对我来说,最好是立即让我说清楚,如果是在那种聚会上让我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可能会发现,我的意见全是抨击性的;我的印象是,你娘家的人,从整体看,全都是傲慢无礼的势利小人,从个别看,个个是彻头彻尾的残暴恶棍。”
“米考伯,”米考伯太太摇着头说,“不!你始终不了解他们,他们也始终不了解你。”
米考伯先生咳嗽了一声。
“他们始终都不了解你,米考伯,”他太太说,“他们也许是没有能力了解你。要是真的这样,那是他们的不幸。我只能对他们的不幸表示怜悯。”
“我亲爱的艾玛,”米考伯先生说,口气有所缓和,“要是我的话说过了头,即使是稍微说过了头,我也感到万分抱歉。我想要说的只是,没有你娘家的人出来为你捧场——简而言之,是在临别时用他们的冷肩膀来推我一下——我照样可以去海外。总而言之,我宁愿凭我自己的力量离开英国,而不愿由他们那班人来加速推动。同时,我亲爱的,要是他们肯屈尊给你回信——根据我们俩共同的经验,显然那是最不可能的——那我决不会成为你的愿望的障碍的。”
这件事就这样和和气气地解决了,米考伯先生把胳臂伸给米考伯太太,朝特雷德尔面前桌子上那堆账册和文件看了看,说他们得先离开我们,接着便彬彬有礼地走了。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他们走后,特雷德尔往椅背上一靠,颇动感情地看着我说,这使得他的眼睛都红了,头发也显出各种形状,“我打算麻烦你办点事,借口我也就不必找了,因为我知道你对这件事深感兴趣,同时这件事又可以把你的心思岔开。我亲爱的老朋友,我希望你没有精疲力竭吧?”
“我已经一切如常了,”我停了一会儿,回答说,“比起对别人来,我们更应该多替我的姨婆想想,你知道,她已经做了那么多了。”
“当然,当然,”特雷德尔回答说,“谁能忘记这一点啊!”
“不过事情还不仅如此,”我说,“在过去这两个星期里,她又有了新的麻烦:她每天都要出入伦敦。有好几次,她都是一大早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才回来。昨天晚上,特雷德尔,她出去后,差不多直到半夜才回家。你知道,她是非常体恤别人的。她一直没有告诉我,到底是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了。”
我姨婆面色苍白,脸上的皱纹深陷,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我把话说完;这时,几滴眼泪流下了她的双颊,她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
“没什么,特洛;没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你慢慢会知道的。现在,爱格妮斯,我亲爱的,让我们着手来办这些事吧!”
“我得替米考伯先生说句公道话,”特雷德尔开口说,“虽然他这个人为自己办事好像没做出什么成就,替别人办事,却是个最不知疲倦的人。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的人。要是他一直都这样干的话,他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两百来岁了。他继续不断拼命干活的那股热情,他日夜钻研文件和账册的那份疯狂冲劲,至于他写给我那么多的信,这儿就不说了;在这间屋子和威克菲尔先生的住处之间,他都用写信的方式进行联系,甚至他坐在我对面,只隔着一张桌子,有事也都写信,其实对我口头说一声更省事;他的这种种情况,都是很了不起的。”
“写信!”我姨婆叫了起来,“我相信,他就是在梦里,也忘不了写信哩!”
“还有狄克先生,”特雷德尔说,“也做了了不起的事!他看管乌利亚·希普时,那么尽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超过他;这项工作完了后,他又全心全意地照顾起威克菲尔先生来。我们调查这件事时,他那么急着要出力帮忙,又是摘录,又是抄写,拿这个,搬那个,做了那么多实际有用的工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狄克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姨婆喊着说,“我一直就是这么说的。特洛,这你知道。”
“我要高兴地告诉你,威克菲尔小姐,”特雷德尔接着说,语气既极其体贴又极其诚恳,“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威克菲尔先生已经大大地见好了。摆脱了长期压在他身上的魇魔,消除掉生活中的恐惧忧虑,他几乎像换了一个人了。有时,就连他那受了损害的对事情要点的记忆力和注意力,现在也都大大地恢复了;因此他能帮着我们把一些事情弄清楚了;要是没有他的帮助,即使并不是毫无希望弄清,但一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不过,我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简要地说一说结果,有关我看到的一切有希望的情况,就不细说了,要不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啦。”
他那轻松自如的态度和令人喜爱的真诚,都表明他说这些话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我们高兴,让爱格妮斯听到,别人在提到她父亲时,都有较大的信心;但是并不因此而让人感到美中不足。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吧,”特雷德尔看着桌子上的文件账册说,“我们把款项都结算过了,把一大堆最初无意造成的混乱情况,以及后来有意造成的混乱和弄虚作假的情况,都作了清理,我们认为,威克菲尔先生现在可以结束他的律师事务和信托代理,没有任何负债或亏空。”
“哦,谢天谢地!”爱格妮斯激动地叫了起来。
“不过,”特雷德尔说,“余下可供威克菲尔先生生活之需的款项——我说这话,甚至是假定把房子卖掉——为数已经不多,多半不超过几百镑。也许,威克菲尔小姐,最好还是考虑一下,是否可以保留他多年来承担的财产代理业务。你知道,朋友们可以帮他出出主意;现在他已经无牵无挂了。有你,威克菲尔小姐——科波菲尔——还有我——”
“这事我已经考虑过了,特洛伍德,”爱格妮斯看着我说,“我觉得不应该保留,断乎不能保留,即便是我非常感激、欠情很多的朋友来劝我,我也认为不应该保留。”
“我不是说我这是劝告,”特雷德尔说,“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把这事提一下。没有别的意思。”
“听你这么一说,我很高兴,”爱格妮斯从容地回答说,“因为你这句话,使我有了希望,几乎可以说是使我有了把握,我们两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亲爱的特雷德尔先生,亲爱的特洛伍德,只要爸爸一旦能体面地摆脱出来,无牵无挂,我还有什么要求的呢!我一直指望,要是我能把爸爸从捆缠住他的罗网中解救出来,我就要用自己一点小小的孝心,来回报我欠他的恩情,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他。这是我多年来最大的愿望。由我把我们未来的生活担负起来,是我的第二大幸福——仅次于从所有信托业务和所负责任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你可曾想过怎么担负呢,爱格妮斯?”
“想过不止一次了!亲爱的特洛伍德,我并不担心,我有成功的把握。这儿有这么多人认识我,都待我这么好,因此我很有把握。你别对我没有信心。我们父女俩所需要的并不多。要是我把这座可爱的老屋租出去,再办一所学校,那我就成了既有用又快乐的人了。”
她那愉快的声音中所表现出的安详热情,首先唤起我对这座可爱老屋的清晰回忆,接着又使我想起我那冷清清的家,因而我的心里充满要说的话。特雷德尔有一会儿假装忙着在文件堆里找东西。
“现在,特洛伍德小姐,”特雷德尔说,“该谈谈你的财产了。”
“好吧,特雷德尔先生,”我姨婆叹了一口气说,“关于我的财产,我要说的只是,要是那笔财产已经没了,我也受得了;要是它还在,能取回来我很高兴。”
“我想,它原本是八千镑,全是统一公债,是吧?”特雷德尔说。
“正是!”我姨婆回答。
“可是我算来算去,还是不超过五这个数字。”特雷德尔带着困惑不解的神气说。
“你的意思是说,不超过五千镑?”我姨婆异常镇静地问道,“还是五镑?”
“五千镑。”特雷德尔回答。
“就这么些了,”我姨婆说,“我已经卖掉了三千镑。其中一千镑,我用来付你学法律的学徒费,特洛,我亲爱的;另外的两千镑,我留在了身边;我那五千镑弄没了的时候,我想这两千镑还是不说为好,悄悄留着,以防万一。我想要看看,你应付艰难困苦的能力到底怎么样,特洛。结果你应付得非常出色——艰苦卓绝,自力更生,克己为人!狄克也是这样。先别跟我说话,因为我觉得我的心神有点纷乱!”
看到她笔挺地坐在那儿,两臂合抱,没有人想到她会心神纷乱;不过她的自制能力是惊人的。“那样的话,我可以高兴地说,”特雷德尔兴高采烈地喊着说,“我们把全部款子都收回来了!”
“别给我道喜,不管是谁!”我姨婆喊着说,“是怎么收回来的,特雷德尔先生?”
“你原来以为,这笔钱都让威克菲尔先生给滥用了,是不是?”特雷德尔说。
“我当然这样想,”我姨婆说,“所以我就一声不吭了。爱格妮斯,一个字都别说!”
“这笔公债确实给卖掉了,”特雷德尔说,“是凭你给的委托代理权卖的。不过,是谁卖的,实际上是谁签的字,我就不必说了。卖掉之后,那个混蛋对威克菲尔先生撒谎说——而且还用数字证明——这笔钱他拿到手后(他居然说,他这是根据威克菲尔先生的指示),用来填补别的亏空和欠款了,免得事情露馅。威克菲尔先生,由于在他的掌握之中,变得软弱无力,毫无办法,他明明知道,这笔本钱已经没有了,可后来还假装着本钱还在,给你付了几次利息,这样一来,他就不幸使自己成了这一骗局的同谋了。”
“而且最后把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我姨婆补充说,“给我写了一封信,像发疯似的,指控自己犯了抢劫罪,以及一大堆听都没听到过的罪名。接到这封信后,一天早上,一大早我就去见他,向他要来一支蜡烛,当场把这封信给烧了,同时对他说,要是有一天,他能为我和他自己把钱弄回来,那就弄回来;要是弄不回来,为了他女儿,就严加保密,对谁也别说起——不管是谁,要是现在要跟我说话,我就离开这屋子!”
我们都默不作声,爱格妮斯则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那么,我亲爱的朋友,”我姨婆停顿了一会,然后说,“你真的逼得他把钱吐出来了?”
“嘿,实际的情况是,”特雷德尔回答说,“米考伯先生把他包围得严严实实了,准备了许多新的办法,要是旧办法不起作用,就用新办法治他,使他没法逃出我们的手掌。一个最让人感到意外,连我也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是,他侵吞这笔钱,与其说是为了满足他的贪欲(他的确贪得无厌),还不如说是由于他对科波菲尔的仇恨。他曾直截了当地对我这样说过。他说,他甚至愿意花掉这么多钱,来打击科波菲尔;或者伤害他。”
“哼!”我姨婆沉思地皱起眉头,朝爱格妮斯看了一眼,说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特雷德尔说,“他跟他妈一起离开这儿了。在整个这段时间,他妈一个劲儿叫叫嚷嚷的,又是哀求,又是自揭疮疤的。他们是搭去伦敦的夜班公共马车走的,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对我的仇恨,在临走时肆无忌惮地表示了。看来他恨我的劲儿,似乎不亚于恨科波菲尔先生;就像我对他说的那样,我认为这实在是对我的一种恭维。”
“你估计他还有钱吗,特雷德尔?”我问道。
“啊,有钱,我认为他还有钱,”他郑重地摇着头说,“我得说,他一定用各种手段捞了不少钱。不过我想,科波菲尔,要是你有机会观察一番他的经历,你会发现,这家伙即便有了钱,也决不会不作恶的。他就是这样一个虚伪的化身。不管做什么事,他走的一定是邪门歪道。这是他表面上以卑躬屈膝来克制自己的唯一补偿。由于他总是在地上爬着去追求这样或那样的小目标,他始终把沿途碰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加以放大,结果是,凡是见到在他和目标之间的任何人,即便是最天真无邪的,他都要仇恨,都要怀疑。因此邪门歪道越来越邪歪,不论是什么时候,为了一丁点儿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也没有,全是这个样。只需想一想他在这儿的历史,”特雷德尔说,“这就知道了。”
“他是个卑鄙无耻的恶魔!”我姨婆说。
“关于这一点,我真的不明白,”特雷德尔若有所思地说,“很多人,要是存心想要卑鄙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卑鄙。”
“好了,我们还是来谈谈米考伯先生吧。”我姨婆说。
“哦,真的,”特雷德尔高兴地说,“我还要再大夸特夸米考伯先生一番。要不是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耐心勤奋、坚持不懈地苦干,我们永远也别想做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来。我觉得,当我们想到米考伯先生可以用他的沉默和乌利亚·希普作出什么妥协时,我们应该考虑到他是在为正义而主持正义。”
“我也这样想。”我说。
“那么,你说该怎么酬谢他呢?”我姨婆说道。
“哦!在你提到这事以前,”特雷德尔略带不安地说,“我就想到,我们用非法的措施——这次的措施从头到尾完全是非法的——来解决这个难题时,恐怕有两点应该排除在外,(不可能事事都照顾到)。米考伯先生向乌利亚预支了不少工资,他给乌利亚立了好些借据什么的——”
“哦!这些钱是必须归还的。”我姨婆说。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根据这些借据起诉,也不知道这些借据现在在哪儿,”特雷德尔睁大眼睛回答说,“我预料,从现在到他出发去海外这段时间内,米考伯先生会不断遭到拘押,或者是强制执行。”
“那样的话,他会不断得到释放、解除强制执行。”我姨婆说,“一共多少钱?”
“嘿,米考伯先生把这些交易——他把这叫作交易——都郑重其事地记在一个本子上了,”特雷德尔微笑着回答说,“他加在一起的总数是一百零三镑五先令。”
“那么,包括这笔欠款在内,我们该给他多少?”我姨婆说,“爱格妮斯,我亲爱的,我们之间怎么分担,以后再说。现在先说说,我们该给他多少?五百镑怎么样?”
一听这话,特雷德尔和我都立刻插嘴了。我们两人都主张给他一小笔现金,欠乌利亚的钱,待他每次来讨时,都代他还清,但事先不必跟米考伯先生讲定。我们建议,除了负担米考伯先生一家的旅费和装备的费用外,再给他一百镑现金。米考伯先生归还这些垫款的办法,应认真订立契约,这样可使他有一种责任感,也许对他有好处。对此我又作了补充建议,由我把米考伯先生的为人和历史,对佩格蒂先生加以说明,我知道佩格蒂先生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们另外再悄悄交给他一百镑,由他根据情况借给米考伯先生。我进一步建议,由我酌情把佩格蒂先生的经历中我觉得应该说的,或认为可以说的,告诉米考伯先生,好引起他对米考伯先生的关心;尽量使他们为共同的利益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大家都热烈地赞同我的这些意见;我可以立即在这儿提一下,过不多久,这两位主要的当事人,都真心诚意、和睦融洽地做到了这一点。
看到特雷德尔焦急不安地朝我姨婆看了一眼,我就问他,他刚才说的第二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是什么。
“科波菲尔,要是我提到一个令人痛苦的题目,我得请你跟你姨婆原谅,我很怕提到这个问题,”特雷德尔犹疑地说,“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提醒你们一下,很有必要。米考伯先生令人难忘地进行揭发的那天,乌利亚·希普曾威吓你姨婆,他暗示的是有关你姨婆的——丈夫。”
我姨婆依然保持着笔挺的姿态坐着,显得很镇定,她点了点头,表示记得。
“也许,”特雷德尔说,“这只是无的放矢的胡扯吧?”
“不。”我姨婆回答说。
“这么说——请原谅——真有这么一个人,而且完全受乌利亚的操纵?”特雷德尔吞吞吐吐地说。
“没错,我的好朋友。”我姨婆说。
特雷德尔明显地拉长着脸解释说,他没能处理好这一问题。这跟米考伯先生的借款一样,没有包括在他所提出的条件之内;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有任何权力来对付乌利亚·希普了;要是他能伤害或扰乱我们或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毫无疑问,他一定会那么干的。
我姨婆始终没有作声,直到又有几颗泪珠流到她的脸颊上。
“你说得很对,”她说,“你提到这件事,想得很周到。”
“我——或者科波菲尔——能帮忙做点什么吗?”特雷德尔柔声地问道。
“用不着,”我姨婆说,“我得再三对你感谢。特洛,我亲爱的,这种恫吓落空了!我们还是把米考伯先生和米考伯太太请回来吧。你们都别再对我说什么了!”说着她抚平衣服,坐得笔挺,眼睛看着门口。
“哦,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太太!”他们进来时,我姨婆说,“我们正在讨论你们移居海外的事,非常对不起,让你们在外面等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我把我们打算怎么安排,告诉你们吧。”
她一一说了我们的安排,他们全家人——孩子们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满意,把米考伯先生那种签订任何票据时开始阶段的守时习惯,也大大地激发起来了,他立即兴高采烈地跑出去买贴在期票上的印花,怎么劝也劝他不住。可是他的欢乐受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还不到五分钟,他就被一个法警押回来了,泪如雨下地告诉我们说,一切都完了。对此我们早有准备,这当然是乌利亚·希普在控告他,于是我们马上付了钱;又过了不到五分钟,米考伯先生就坐在桌子旁,十分高兴地在贴在期票的印花上填写起来,只有干这种愉快的活儿,或者调制潘趣酒,才能使他那份得意之色,在那张发光的脸上完全露出来。看他带着艺术家的情趣,像画画似的在那些印花上描着,横过来竖过去地看了又看,还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记下日期、金额这些重要事项;填写完后,又仔细查看了一番,深深感觉到这些印花的宝贵价值;他这种种表现,真是一番难得看到的美景。
“哦,米考伯先生,要是你允许我劝告你一句的话,”我姨婆默默地观察了他一会之后说,“你最好从此以后,发誓不再干这种活儿了。”
“特洛伍德小姐,”米考伯先生回答说,“我的意图就是要把这样一个誓言,在未来的白纸一张的新篇章上记下来。米考伯太太可以为此作证。我相信,”米考伯先生庄重地说,“我儿子威尔金斯会永远记住,他宁愿把手放进火里,也比用它去摆弄这些在他父亲命脉里放了毒的毒蛇好得多!”米考伯先生深受感动,立即成了失望的化身,用阴郁恐怖的眼神注视着这些“毒蛇”(他刚才对它们那爱慕之情,并没有完全消退),然后把它们折了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
那天晚上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我们都已让烦愁和劳累弄得精疲力竭,于是姨婆和我决定第二天回伦敦。根据安排,米考伯一家把家具什物交经纪人卖出后,也随我们去伦敦。威克菲尔先生的事务,以适当的速度,由特雷德尔主持清理。清理期间,爱格妮斯也去伦敦。那天我们都在那座老屋里过的夜;驱除了希普母子,这座老屋仿佛清除了一场瘟疫。我躺在我那个老房间中,就像是一个遭遇沉舟之难的浪子返回到家园。
第二天,我们回到伦敦我姨婆家——我没有回自己家;当我们像往常那样,在睡觉以前,单独坐在一块儿时,她说道:
“特洛,你真想知道我最近心里有什么事吗?”
“我真想知道,姨婆。如果说有什么时候,由于我没能为你分担你的悲伤和忧愁而感到不安,那就是现在了。”
“孩子,”我姨婆慈爱地说,“即使不加上我这点小小的痛苦,你自己已经够伤心的了。我所以瞒着不把事情告诉你,就是出于这个动机,特洛。”
“这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说,“不过现在你还是告诉我吧。”
“明天早上你能跟我一起乘车出去一趟吗?”我姨婆问道。
“当然能。”
“九点钟,”她说道,“到那时我会告诉你,我亲爱的。”
于是,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就坐了一辆轻便马车前往伦敦。我们穿过街市,走了很长一段路,最后来到一所大医院。在医院大楼的近旁,停着一辆素净的柩车。柩车的车夫认出我姨婆,他遵照我姨婆在窗口打的手势,缓缓地赶动了柩车,我们的车就跟在后面。
“现在你明白了吧,特洛,”我姨婆说,“他走了!”
“是在医院里去世的吗?”
“是的。”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我旁边;不过我又看到她脸颊上流下了几滴眼泪。
“他先前在那儿住过一次,”我姨婆接着说,“他已经病了很久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个支离破碎的人。这次最后发病,他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了,就要求他们打发人来叫我。这时候,他表示很悔恨,非常悔恨。”
“你去了,这我知道,姨婆。”
“我去了。后来我跟他在一块儿待了好些时间。”
“他是在我们去坎特伯雷前的那个晚上去世的吧?”我问道。
我姨婆点了点头。“现在谁也伤害不到他了,”她说,“恫吓落空了!”
我们乘车出了城,来到霍恩西的教堂墓地。“这儿总比在街上好,”我姨婆说,“他是在这儿出生的。”
我们下了车,跟在那具普普通通的棺木后面,来到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角落,下葬仪式就在这儿举行。
“三十六年前,也就是今天这个日子,我亲爱的,”当我朝轻便马车走回去时,我姨婆说,“我们结了婚,愿上帝饶恕我们大家吧!”
我们默不作声地上车落了座;她就这样握着我的手,在我身旁坐了好久。后来她突然哭了起来,说:
“我跟他结婚时,他的样子还是挺英俊的,特洛——可后来可悲地变了样了!”
她并没有哭多久。她这么一哭,心情舒畅多了,很快便又镇静下来,甚至有些高兴起来。她说,她神经有点衰弱了,要不她不会忍不住哭起来的。愿上帝饶恕我们大家吧!
于是,我们就这样乘车回到她海盖特的小房子里。我们看到了下面这封短信,这是米考伯先生通过早班邮车送来的:
星期五,于坎特伯雷
亲爱的特洛伍德小姐及科波菲尔:
最近天边隐约显现之乐土佳境,如今又被难以穿透之浓雾所笼罩,永远在一个厄运注定的可怜流浪者眼前消失矣!
希普控米考伯另一案之拘票已发出(以威斯敏斯特王家高等法院名义所发),而此案之被告,已被该辖区具有司法管辖权之行政司法长官所拘押矣。
时刻已到,决战在今朝,
前线的军情吃紧了,
骄横的爱德华大军已到——
带来了镣铐和奴役!
此即吾委身之所,并将委命于迅即到来之结局(因精神痛苦超过一定限度,必将不堪忍受,吾自觉已达此限度矣)。呜呼!如后来之旅人,出于好奇及同情(但愿如此),访问本城负债人囚禁之所,当细察其墙壁时,也许会沉思默想(吾相信必定会)这用锈钉刻画于墙上模糊不清之姓名缩写:
威·米
附言:吾重启此函,特此奉告:吾等共同之好友托马斯·特雷特尔先生(尚未离开我等,伊气色极佳),已以特洛伍德小姐崇高之名义,付清这案之欠款及讼费。吾与全家,又处于尘世福祉之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