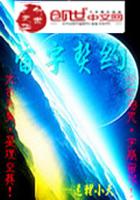为处理杜氏的后续事宜,这个在集团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也变得异常忙碌。临走时,他让我睡一觉再回家,可是他离开后没多久,杜见修找上门来。
杜见修没有敲门,直接输入密码进来。我坐在沙发上惊悚地望着那动一动嘴皮子就能让我自己挖坑自己跳的男人,他却连一个起伏的眼神都没有给我,直接开门见山。
“不用那么惊讶地看着我,他的密码从小到大都只有一个是我妈的生日。接下来也不用作出瑟瑟发抖的表情,余小姐,因为我不会再试图用任何的方式伤害你。你有什么罪呢?只不过恰好在他任性的时候成为了与我作对的工具。说起来,你也是个可怜的姑娘。既然是他太过任性,那么从现在起,我不会再迁怒其他人,只会竭尽全力来破坏他的人生,总好过到头来被别人破坏。”
“你……”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和他的恩怨纠葛,那么你应该比谁都明白,见襄永远都赢不了我,因为他得到的太多了。仗着年纪小,从小胡作非为却还是能得到所有人的关心爱,长大了也悠游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并不太明白,我们这样的人其实从出生开始就被迫上了战场。而我,将会是这场战争里最后的赢家,因为失无所失。”
“我……”
“还有,不知道我这傻弟弟有没有告诉你,因为今天在公共场合不顾一切解救你的行为,他可能面临被董事会投票除名。并且,两个小时以后就是股东大会,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让你亲眼见证他从云端跌落谷底的过程。很遗憾,余小姐,因为你,他精光闪耀的人生会出现第一次耻辱性的败北。”
我讲过,这男人有一种光是说话就能吓到人的能力,起码从开始还想佯装淡定的我,直接被他的话吓到从沙发上跳起了身。我拦住转身欲走的杜见修,跟花果山的猴子似地,身手敏捷地跳到他跟前,艰难地用自己的身高拦住对方。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杜见襄的那句“天塌下来,矮子是抵挡不了的”。我仰起头,露出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祈求表情,祈求这个男人对自己的亲弟弟手下留情。
“请别这样。”
我抖着嗓子说。
“或许在你看来,这只是简单的利益较量,于他而言也顶多就是一次失败,可在我看来,那根本不是较量,是背叛!”
背叛!
这两个字刺激到了杜见修,他眼里的情绪终于有了起伏,几乎伸出手要掐住我的脖子,可他修长的五指只是轻轻从我脖颈划过以作威胁,我却居然不怕死地继续往下说。
“是背叛,不是吗?如果有把对方当作亲人看待哪怕一秒的话,早该意识到,那个人无论表面上做得多么恨你,却从来没有要和你争夺任何东西的样子。所以我请求你,不要再让他的人生遭遇同样的背叛……如果你觉得我是一切灾难体,担心我再惹出祸乱,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再和杜公子产生任何交集。”
“因为三天后,我就会离开N城。”
杜见修挑了挑眉毛,似乎在考量我话中的真实性,也不太明白我为什么突然决定离开的理由,我却诡异地对他笑了笑。
“你大可放心,我不是为了要替杜见襄拖延时间,而是在你来之前,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不是情急,不是任性,而是从杜见襄对我表明心迹的那刻起,这个决定早已在心中生根发芽。
因为,许初颜发生意外的那个夜晚,不仅为我和乔北方划出片永远跨不过的沧海,也就此成为了我顺遂人生的分水岭。
当我被许初颜推搡到撞在杜见襄坚硬的车顶后,我的左耳便开始时不时地泛疼,直到渐渐听不清楚那些细声细语。在杜氏集团门外,为了不让杜见襄陷入口诛笔伐的境地,我被大片记者围攻,别人的问话如潮水般涌来,我却无论怎么集中注意力,耳边也只余下涣散的音节,直到秦太阳将我带离是非之地后,我一个人去了医院。
“剧烈撞击导致外伤性出血却没能及时处理,中耳化脓后穿破了鼓膜,破坏了大半的听小骨。现在你受伤的左耳听力几乎全无,全靠右耳传声,加上你中途发烧过一次加重了炎症和病毒感染,恐怕要不了多久,右耳的听力也会退化,回天乏术。”
看,风水轮流转,我因为乔北方父亲的牺牲而没有家破人亡,健康富足生活到现在,最终我也还在了他爱的人手上。我们欠谁的债,某天总会以不自知的方式偿还。
所以杜见襄留给我的选择,根本就不是选择。我根本不会以任何的名义去阻止乔北方订婚,更不会出现在机场,因为配不上。
我忘了杜见修什么时候离开的,也忘记了他到底有没有答应我的请求,我只记得他离开后,客厅碎了一地明晃晃的日光。我戴着失而复得的黑框眼镜,眯着眼睛数光线。
一束,两束,三束……越数泪越掉,越数越慌张。
悲欢离合这轮回之道,你我不过凡人尔尔,如何逃?
我精神涣散地从杜见襄那里回到公寓,却发现此时应在报社忙得焦头烂额的秦月亮正端坐在沙发上,似乎坐了很久,眼睛有些红,不知是不是哭过,美二代难得在一旁恹恹地看着我两,不敢靠近。
在杜见襄公寓时,他曾试探性地问过我,有没有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这个秘密告诉过别人,我回忆起在报社楼下遭遇的非人待遇,连想都没想,当机立断摇了头。尽管我以为,在关键时刻会为我上到山下火海的人,并没有这样做,可我始终做不到,让她一一体尝这样的屈辱。她是那么高傲的姑娘,若真遭遇这样的事情,不如去死。
我不声不响地准备回房间,秦月亮终于主动和我搭了话,却不是乞求原谅。
她说:“余笙你放心,我不会对你说对不起,你猜得对,上次我因为那个偶然的错误确实差点被开除,是你喝醉后透露的秘密解除了我的困境。作为交换,我升职加薪,才有了钱还你父母。我不管你会因此怎么想我,也不会强求你站在我的立场来为我考虑,在我看来,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错了就是错了,你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
我脚下的步子定住,没回话,只怔怔看着沙发旁边那个大行李箱。当初我和她同气连枝将它搬上来,如今它孤零零地躺在地上,明明是要被自己的主人带走,却一副被遗弃的模样。它令我不禁联想起自己,明明是留下来的那一个,明明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那一个,却怎么可怜到连一句指责的话都说不出口,只悠悠告诉她说:“月亮,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强求过我要站在你的立场考虑,可我无时无刻不在这样做。你被主任骂得狗血淋头,我为了不伤害你的自尊,只当从未见过。你因为秦太阳负债,我二话不说硬着头皮回家帮你借钱。你面临被开除的危险,我为了你,死皮赖脸地去祈求杜见襄答应让你专访。可我没想到,我最终换来的是什么这样一句——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
语毕,秦月亮终于崩溃在我面前,泣不成声。她张了张嘴,一句对不起几乎要脱口而出,可最终还是没有,仿佛无颜再面对似的,起身拉了行李就要往外走。
我稳住语气叫住她,尽量让这场离别看起来没那么撕心裂肺。
“你把美二带走吧,我看得出,它喜欢的人,不是我。”
可话音方落,我抑制许久的眼泪已经奔腾而出,像无数次幻想过的那样,文艺凄美地从眼角滑到下巴。语气忧伤得好像并非在说一只猫不喜欢我,而是所有我曾视他/她如命的人。
不知美二是不是能听懂人话,又或者被我过于悲戚的表情惊讶到,所以它在这个当头悠悠地起了身,头一次喵呜着在我脚下撒娇般地转悠,深褐发亮的双瞳里,没了过往的嫌弃。我很想伸手将它抱起来,可是我不能。如果我将它留在身边,那余生的每分每秒,都会想起一个叫乔北方的男子,想起他对我的嗤之以鼻,想起我对他的爱而不得。
秦月亮最终搬去了哪里我并不知道,或许回了家。我之所以没有勉强她留下是因为,让她继续用一张忏悔的脸来面对我,我们都会疯掉。我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深渊。秦月亮不愿告诉我她的深渊,也许是因为骄傲,也许是因为,有些事情在她看来,我不知道,比知道更好。她走的那天,我也退房搬回了家,我妈抽风着问我这是要拿着行李嫁进杜家的节奏了吗,我却重重关上了卧室门,片刻后又打开。
“你和爸不是希望我去国外读研究生吗?我想了想,自己学到的东西的确不足以应付这个世界,现在就着手办吧。”
说完,不管外面的人如何将门敲得震天响,蒙头倒床,哭到天昏地暗,日月同辉。
许江应该看过黄历,三天后,正好是新一年的春分,白天和夜晚的时间一样长,据说,这天是太阳和月亮结婚的日子,特别浪漫。可老天从清晨便开始不作美,阴气沉沉地下起了雨,让白昼看起来也如黑夜,导致许氏临时发声明,将仪式的时间从中午推到了晚上,将巨大的人工草坪统统搭上了浪漫粉的巨大帐篷。
我原本不想出现在那样的场合,毕竟没收到邀请,可杜见襄帮我找回的眼镜,是比美美还烫手的存在。我曾信誓旦旦将它当作我和乔北方之间的定情信物。我说天涯那么远,你那一半走了一圈还是回到了我这半的身边,所以我们的人生注定牵系一辈子。而如今,一辈子太短,不再属于我的东西,不该还留有念想。
说来也巧,杜见襄给我发来消息,说航班晚点,正式起飞的时间是晚上八点,正好与订婚典礼的时间重合,我却没做任何回复。因为这几天,杜氏没有传出一点风声,杜见修遵守了承诺,我离开N城,他游说董事会的人放弃投票。临到最后,我不敢再让自己稍有一步的行差走错,只怕再卷起滔天巨浪。
去婚礼前,我沉重的心情反倒一派轻松,好像多年的执念将在今天画下句点。而我为了庆祝他向我举起这最后的、致命的一刀,甚至认认真真地化了妆,换上礼服赴刑场。
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不到六点,天已彻底黑下,空气中还隐隐带着冬日的濡湿,晃来晃去的车灯闪得我眼睛胀疼。开车的出租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长相颇为俊秀,从我上车开始便多看了我几眼,而当我报出要去的地点,他更是怪异地对我说:“今天去那里的可都是富甲人家啊,你怎么还打车。”
我说:“做土豪久了,今天想体验一天平民的生活,别人都香车宝马驾到,我坐一出租车,多惹眼多拉风啊。”
惹得年轻司机放声大笑。
“像、真像……”
他下意识吐出几个单音,惹起我的好奇,追问起因。兴许是在堵车长龙中等着也无聊,他共我讲起身世。
他说自己不是本地人,没有母亲,从小被混混父亲东拉西扯养大,所以在他的观念里,天下就没有拳头解决不了的事情。可是在他最缭乱的青葱岁月里,却遇见了一个与他同样张牙舞爪,内心却比谁都纯白的女孩子。
“很倔,面上再多心事,嘴上也随时随地不肯认输。她用最好的青春和全部的热情来喜欢除了一张脸其他一无是处的我。我也曾答应过,要给她一份世上最干净的感情,但人也许都犯贱,有了这样,总还念着缺的那样,比如钱。所以后来,我和一个富家女纠缠不清,亲手将她奉上的感情弃若敝屣,甚至让她遭到了无妄之灾。”
夜黑,风高,雨低。这个年轻的的士司机,说到中途,居然红了眼眶。他说,他对年轻的自己很失望,后来想弥补,却已经没有了资格。
就在红绿灯口,他伸出自己带着狰狞伤口的腿给我看,佯装轻松道:“这世上是有报应的,对吧?今天,是她结婚的日子。”
我眼眶莫名一热,说,你别再讲。
感情这东西,说穿了就是一场游戏。有的人顺利通关,有的人走得坎坷。通关过程你被虐得再厉害,死一万次,程序也不会因为你一个人而更改,欺负人如此彻底。
我和年轻司机一路默契地沉默,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现场,因和他太投缘的关系,我让他在外面等一会儿,想把眼镜交给乔北方以后就走,再搭他的车。因为我有预感,当我真的将东西还给他以后,必定会忍不住歇斯底里肝肠寸断一番。与其将脆弱暴露给路边并不懂得的陌生人,不如让它展现在感同身受的人面前,至少那样,我会觉得世上伤心人不只我一个,这样才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可我又再一次地没猜到开始,也没猜到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