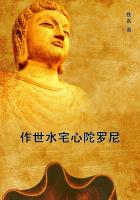初春夜晚寒冷的天气,厉君措背着司徒透经过那片依旧葱翠的葡萄园。
在这个万物还未来得及复苏的时节里,整个金都也只有厉家周围能有这样的生机盎然。
厉君措的嘴角微微勾起,没有直接走向厉宅。
冷风袭来,司徒透搂住厉君措脖子的胳膊紧了紧,“怎么不是回去吗?”
厉君措不语,反而背着司徒透走进了葡萄园。
葡萄园里的叶子挨挨挤挤,长得十分茂密。
厉君措背着她走了一段距离,终于在一个葡萄架下停了下来。
司徒透从男人的背上下来,就看到葡萄架周围结结实实地打了木桩子,木桩子上面是架子,架子上挂着的是个造型古朴的大秋千。
她眯着的眼睛顿时放出光彩来,弯着嘴角又惊又喜,伸手指着秋千,“你真的让人做了?”
前段时间,她跟着他进园子里看葡萄的长势时,曾经指着这里的葡萄架随口说,如果这里有个秋千就好了。
听人说,在七夕那一天,坐在葡萄架下就能够听到牛郎织女的私语。
厉君措当时翻着白眼看她,“你们女人不只迷信,还爱八卦。”
没想到,在她不在的这十几日,他竟然真的在这里架了个秋千。
司徒透坐在秋千上,眨着两只清澈的大眼睛,冲厉君措明媚一笑,招了招手,“过来坐啊。”
男人却没有立即坐下,反而转身从后面的葡萄叶子掩映的地方端出来一个盘子,盘子里面是堆成小山一样的白雪。
他端着盘子和她并排坐在秋千上,有些得意地扫了一眼司徒透好奇的眼神,伸手来将盘子里面的雪掸掉。
盘子里面便露出一串已经成熟的,很大粒的诱人的葡萄。
这种吃法,她教他的。
司徒透直勾勾地盯着那串葡萄,咽了口口水,吃货的世界里是没有“出息”这两个字的。
她的手指动了动,用眼睛瞄了瞄坐在身旁的厉君措。
厉君措嘴角似笑非笑,曜黑的眼睛中流泻出璀璨的光芒,“前段时间不是还吵着要吃园子里的葡萄么。”
司徒透抿着小嘴巴,伸出手来轻轻摘了一粒葡萄放在嘴里,冰凉的感觉将甜蜜放到最大,在她的嘴里炸开。
她满足地点了点头,“想不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连葡萄都已经成熟了。”
厉君措从司徒透手中抽过巧克力盒子,打开掰了一块塞进嘴里,眼睛盯着天边的星星,“嗯,没想到你走了这么久。”
司徒透侧着脑袋,看着男人比星星还要灿烂的眼睛中闪烁的光彩,又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巧克力。
这么难看的东西实在和他太不相配。
他英俊得太完美,完美到几乎任何有缺陷的东西在他身边都相形见绌自惭形秽。
“别吃了,那么难看。”她小声嘟囔着。
男人却又填了一块巧克力在自己的嘴里,“味道还凑合,而且,这辈子第一次有个女人为我做了这么难看的东西。”
司徒透的心陡然一颤,愣怔地眨着眼睛看他,“柔柔……没有送给你么?”
厉君措的下巴轻扬,目光悠远地盯着天空,“你在和我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提到别人么。”
司徒透低下脑袋,塞了粒葡萄进嘴里,按理说厉君措现在应该正在纪柔在一起,过着属于两个人的第一个情人节。
可是,他怎么突然回来了呢?
司徒透揉了揉脑袋,他不让她问,她也有些逃避般不愿意提起。
将口中的葡萄咽了下去,司徒透开始将话题扯到一边,“又不是在温室里,你们厉家的葡萄园为什么一直都能这么碧绿碧绿的?就连葡萄熟了叶子也不会掉?”
说到让厉君措颇为自豪的事情,他的嘴角微微扬起,“厉酿红品用的葡萄,自然不会和别家相同。”
司徒透扁了扁嘴巴,那手指戳着盘子中的葡萄,“我知道你们的红酒一旦投入市场就会被抢购一空,但是这样的葡萄应该违背自然规律,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男人扬起大手,在司徒透的脑袋上敲了一下,“科学是什么,懂么。”
司徒透吐了吐舌头,睨了他一眼,低着头默默吃着盘子里的葡萄。
刚才还晴朗的天气,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飘飘洒洒落下了雪花。
原本衣衫就比较单薄,再加上又吃了大半盘子冰葡萄,司徒透不自觉地打了个冷颤。
厉君措侧头,轻轻拨了拨落在司徒透乌黑秀发上的落雪。
他将身上的外套脱下一半,一半仍然留在自己身上,冲她扬了扬眉角。
司徒透咬了咬嘴唇,犹豫着仍然坐在原地,与厉君措保持着半个身位的距离。
男人蹙眉,伸出一只有力的手臂,直接将司徒透揽了过来。
一件外套将两个人紧紧裹在一起,司徒透半伏在男人的胸膛,听着男人强有力的心跳,伸出手来轻轻接住飘落的雪。
厉君措箍住她的手很紧,性感而深沉的声线飘荡在她的耳畔,“这个地方留给你,避风,遮雨,挡雪。”
司徒透缓缓抬起脑袋,与男人的眼睛对视。
今天的男人少了平日的张扬跋扈,多了一丝安静深沉,一双黑色漩涡般地眼睛紧紧锁住她。
司徒透的心突然“扑通扑通”不安地跳了起来。
她紧张又局促地避开男人的目光,想要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却又被他紧紧按住,“别动。”
安静的空气中,时间都好像静止了。
司徒透清了清嗓子,“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厉君措坐着没动,声音格外低沉,“你走的这十几天,又没有想……家?”
其实,他想问的不是这个。
司徒透抬眼,看向那栋富丽堂皇的大宅子,她该说想了还是没想呢?
男人听不到她的回答,紧紧蹙起了眉头,“今天不许回司徒家。”
司徒透抬头,“可是……”
可是头才抬到了一半,就被男人的一只大手按住,重新将她的脑袋贴住自己的胸口。
厉君措从来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但在要开口之前还是深深吸了一口气。
“司徒透,你的心是石头做的么?”
司徒透愣了愣,“啊?”
厉君措皱着眉头,“你在司徒家的这十几天,就真的一点都没有想过这里,没有想过……我么?”
“我……”司徒透想说自己想过啊,天天在想,无时无刻不在想。
“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可是想过呢。”厉君措突然开口。
司徒透眨了眨眼睛,身子一颤,生怕是自己理解错了,小心翼翼问道:“谁?想过什么?”
厉君措纤长的睫羽上好像也落了雪,淡淡地眨了眨眼睛,“你走之后,还有其他人住在这里么?住在这里的那个人,每次一回来,就只能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子,原来只有房子的地方不叫家。”
司徒透觉得,自己是个太感性的人。厉君措简简单单一段话,却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湿了眼眶。
“君措,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你还不明白么。”厉君措感受到胸口因为她的眼泪沾湿而传来的淡淡凉意,伸手来抹了抹她的眼睛。
“我不想让你和苏颂宜有任何联系,不愿意你去多管你哥哥的事情,甚至不同意你去帮助项易,我只想像这样,把你箍在我的身边,你只能是我的女人,这样你还明白了么?”
司徒透就好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顿时大脑一片空白,愣在当场。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发现你那样苦苦喜欢的一个人,恰好也正悄悄地喜欢着你。
只是这样的喜欢,如果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呢?
司徒透哽着嗓子,“可是,柔柔呢,她怎么办?”
厉君措的语气有些急,“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都是为别人考虑?你就不能想想你自己,或者考虑考虑我?你给我听好了,感情是条单行道。”
司徒透愣怔看着男人认真的表情,没有了平时玩世不恭骄傲的样子,只是霸道依旧。
感情这件事情,讲究得是你情我愿,她也很清楚。
只是这样,算不算是一种对友谊的背叛?
她的眼泪啪嗒一下掉了下来,“我也很想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用顾忌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那样,可能我当初就会不顾钱莉莉肚子里的孩子,把苏颂宜留在我的身边。”
她抹了一把眼泪,“如果那样,我就不会和那个给我欢喜,让我落泪的混蛋在一起,我也就不用像现在这样明明长了一张嘴巴,却永远要做个哑巴,如果……”
司徒透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疼痛来得那么突然,小腹里面就像搅了一把刀子。
厉君措一蹙眉,看到她的脸色已经瞬间煞白,双手捂住小腹,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怎么了?”
司徒透有气无力,“肚子,好疼……”
男人的目光一沉,一把将她抱起来,“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司徒透搂住他的脖子,微微摇了摇头,“我没事,只是需要去趟卫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