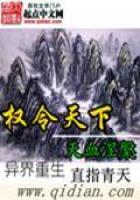前不久,老友们聚在一起,谈起我出书的事。说你这个人就是怪,人家出书时你不出,人家不出书了,你倒出起书来。还有人说,你不是反对出书么?老了怎么又出尔反尔了?我笑而未答。
对于出书,我一直怀着诚惶诚恐的纠结心理。记得世纪初刮起一股出书热,无论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一古脑儿纷纷涌出。一时间,洛阳纸贱,作家满天飞。见面就有人问,你出书了么?然后故作扭捏地塞给你一本书,然后写上“请君斧正”,然后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其中当然不乏真正的文字高手,但却是凤毛麟角,反正我收到的几本,大多数不敢恭维。热爱写作的文学爱好者,无论水平高低,其热情亦可说难能可贵。当时书号也好批,只要找到一点关系,交上一定的费用就放行。只要有钱,不管好赖,不论发表过还是未发表过,出版社也一路绿灯。
记得在一次书会上,有个教育界我熟悉的酸文人,平时会鼓弄一些春联、对联,哼一些歪诗,偶尔有豆腐块见诸地方小报。他拉我到会场一角,说只剩几本了,留给你一本。看看内容,简直让我这个半瓶醋的人也笑掉大牙。夹在书中的名片上赫然印着“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的头衔,上面又用墨水笔添上“中国当代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终身名誉主席”的字样!想起央视春晚宋丹丹、赵本山和崔永元的小品。无论是“白云”的“相当的期盼”,还是“黑土”反其道而行的讥讽,都是对“赶风出书”的一种调侃。
对于作品,我一直认为只有在报刊上发表了的文章,才能被称之为作品,所以对自己未发表过的文章只称习作。如今网络文学如火如荼,网上发表的文章则又另当别论。当然,发表的文章不一定都是好文章,未发表的文章不一定都不是好文章;对于出书,我认为出书者必是有一定名气的作家,文章一定要是高水平有品味能被称之为作品的好文章。同理出版的书不一定就好,未出版的书不一定就差。但现实中透着万般的无奈,要发表自己的文章,不但要看文章质量的好坏,或多或少也牵涉到一些人情关系和“金二戈”。但对于文友来说,发表与不发表文章,出书不出书,确实是一个瓶颈。如果你想谋得一个职称,如果你想进作协一类的团体,人家首先会问,你的文章发表了多少?你出了几本书?所以我反对自己出书,但不反对别人出书。
文字是我所爱,出书当然是文学人的梦。学生时期喜欢读书,写话,曾多有范文在高年级传阅。教导主任曾在学生会中对我们几个委员说,兴许我们当中几十年后出个郭沫若也未可知。从那时起,我的心田里便种下了文学梦。六十年代末有文字上了广播,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七十年代末一篇通讯上了市报头版头条让我出了点小名,此后专业论文、文学作品屡屡见诸报刊。工作生涯中对本门专业小有研究,曾在各级报刊、论坛发表专业论文、调查报告数十篇,多次获奖。本门工作外还兼点文职,平时喜欢耍点小笔杆,随心,随性,胡乱涂鸦,却也小有收获,文学作品屡见报端。说实话,我亦俗人,当时也受潮流的影响和文友的鼓动而蠢蠢欲动。但我用自己的方式“出书”,我边学电脑边打字,把我发表过的文章汇集起来,编辑成11万字的论文集和10万字的散文集,然后,自己设计封面、插页,自己用公家的打印机用“吃混钱”淘来的白纸各印了百余本。作者、责任编辑、图文设计:未名书屋屋主(笔名),出版发行:未名书屋出版社,印刷:未名书屋文印社。一分钱未花,既出了书又学会了电脑。
国庆60周年前夕,宣传部和作协组织了一次集中出书,我的心又活泛起来,想把自己的那个集子与以后几年的文章合并出书。可是重温旧作,内心深感到那些过去的所谓作品是何等的稚嫩,文字里的瑕疵与不足,足以让我脸红,知识的浅薄和品位、境界的低下足以让我汗颜,我何德何能以何面目出书!于是放弃了那次出书的大好机会。
记得有次与南京来的作家采风团聚会,与专业大作家罗望子聊天。他问我出过书吗,我回答后,他劝慰我,不要总想着发表,只要想着去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就得,这正合我本意。退休后写一些小文,聊作消遣。在文学网站和报刊杂志上发表,几年时间便有了200多篇。好心人相劝:“出个集子吧!”文友圈的人,更是热心鼓励,搞得我又有点心绪不宁。等到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写这些文章,本意用来打发时光的,早就远离了名利场,何故人老了,反而赶起了时髦,没事找事做?大概骨子里未完全达到那种至高的思想境界吧?在我的潜意识里也还有那个出书的梦。
恰好去年江山文学网在成立五周年之际,将我网上发表的文章有选择地汇集起来,为我免费出了一本纸质电子书,作为前者散文集《心海微波》的姐妹篇姑且名《网海逐波》。思量着花一点钱印一点,送一送至交文友。原稿被散文大家、市散文学会会长赵永生先生看到了,建议走官方正规渠道发表,我心有疑忌。会长热情鼓励,我又在原稿基础上进行了取舍,便有了这本拙著。深深感谢我敬佩的军旅作家、《响商》杂志的总编、中国散文学会、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吴万群先生从百忙中为我作序,对我和我的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书家汪明军先生挥毫作书名题字,更为拙著添彩增色。
生于菊月,先父给我起名菊生,便对菊情有独钟,记得儿时江南夏夜的篱笆边,傍着野菊,闻着菊香,睡在凉席上数星星,边听先母讲故事边做着玫瑰色的梦。退休了,又返老还童,过起了陶渊明式的生活,每每灯下走笔,阅读,在键盘敲击心语,案前解语的菊总心有灵犀,左右顾盼,伴我夜读,与我对话。在文学网上也曾用“东篱子”的笔名发表文章,便为这本集子取名《东篱夜话》吧。另一部游记专辑取名《旅途拾贝》,则是我前半生游览祖国旅途中拾得的一掬贝壳。
晚年为自己编两本“自选集”,只是把以前所写的文字归拢一下,但实际上却是一次“自我盘点”,是生命进入冬季时对自己前三季度的一次回顾和检验。文章不算好,书,也不一定有人爱看。但我确实是用心去做了,因为那里面有我的流年碎影,我的人生印记,每一篇文章都记录了尘封的往事和彼时的情感。不管有意思没意思,有意义没意义,起码可以留给我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了解前辈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由他们去评高论低。我只知道花自己的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就知足心安了。
毕淑敏在《书的莞尔一笑》中对自己的文字和书的心语,激起我内心的共鸣。她说,“……一笔一画地完成它们,对自己多了一些胆战心惊的了解。好像一只手,探进了自己的胸膛,感到了心的灼热和它搏跳的艰难。”这正是我此时心迹所至。她还说:“它们一旦脱离了我的笔端,就有了独自的生命。我根本不知道它们会走到哪里,会结交怎样的眼神,会有怎样波光诡谲的命运。一大批书籍,肯定是化为垃圾了,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一点也不悲伤,连自己的肉身都会在某一天焚为灰白色的粉末,更何况无知无觉的纸浆!其中有极少的一部分,也许会站在书架上,那简直就是住进了书籍的五星级宾馆了。”她说,对于作家来说,要学会微笑着面对生命的终极——因为还会活在自己的文字之中。这样的文字,读来更觉心灵震撼,就像是对我说的。
曾有人问著名作家韩少功,文学有什么用?阅读再多的文学作品,也无法给我们直接带来牛奶、面包、房子、车子。况且,现在出书费用不低,堆在桌上这么一大摞子书,掏的是个人腰包。韩少功怎么回答的我记不清了,但我认为,人对精神生活存在本能的需求,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这种需求越高,在这个物欲膨胀的社会更应该在精神上有所追求,当今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更证明这一点。一个奔七的人,为一篇文章苦思冥想,为一本书有时甚至心力交瘁,一旦完成了却倍感满足,这样乐此不疲也是一种晚来青春的挥洒。我幸慰,为这些文字,为这书。我不知道我这条路究竟会走多远,但我终究还是选择了。不管结果怎样,也将一如既往走下去,让自己活在自己的书中,活在自己的文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