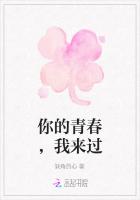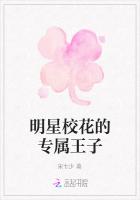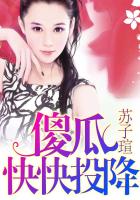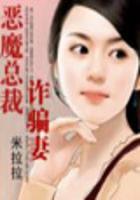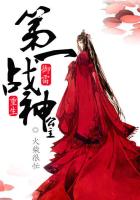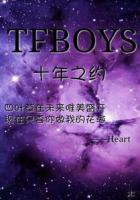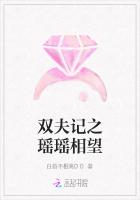沐青莲家里收拾得还算干净,于刚、青莲暂住在父母西侧的小平房里。这间堆放杂物的小屋,二人回来前才腾出来。存放粮食的木仓占了半间屋,没法挪动,只好在上面铺张塑料置放东西。小孩是在回家后十一天才生的,女孩,比预产期晚了几天,还算顺利。于刚和沐青莲商量后,给女儿取名于音。
小生命给于刚和沐青莲带来劳累,也带来了希望。他们知道,这一辈子不可能没有变化,也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基本的格局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做一个小办事员,做一个普通的农场工人。他们希望通过精心的哺育、教育,使孩子的前途比他们更好一些。
小孩满月的那天,青莲妈第一次将外孙女抱到门口晒太阳。孩子似乎集中了沐青莲和于刚的优点,很秀气,当外婆的自然很满意。她看着看着,忽然紧张起来:孩子脸部发黄。她着急地招呼青莲、于刚出门看。
青莲、于刚看到,阳光照射下的孩子脸黄得像涂了一层蜡。
“正常的孩子,一个月黄疸就褪得差不多了,个别的晚一点也不会黄到这个样子!”青莲妈说。
二人毫无这方面的知识,都急了:“怎么办?”
“赶快上医院,孩子这么小,耽搁不得!”青莲妈吩咐。
他们准备了一下,坐上村里的手扶拖拉机上了公路,再换乘公共汽车,一个多小时后赶到青莲分娩的那个县妇产医院。
接诊的是一位女大夫,头发花白了,问了情况后查看小孩子的脐部,接着又开化验单。老大夫的额头蹙起一个疙瘩:“脐部感染,败血症。”
败血症?这是个令人恐怖的病名。于刚、青莲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青莲妈面无表情。
“大夫,怎么会是这样的病?”于刚、青莲有点不大相信。
“现在不是查找病因的时候,而是赶快救治,有什么以后再说,住院——”老大夫说着,给孩子开了住院单。
住院手续办得还算顺利,但这没有减缓青莲、于刚的焦急:“大夫,败血症……有救吗?”
“我实话实说,败血症是婴儿要特别注意防止的病症……我们医院这些年救治的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十……当然,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
护士进来了,给孩子输青霉素,长长的针头猛地从小手腕上扎进去,孩子一阵尖哭。于刚、沐青莲的心也像被针扎了。
几天后,孩子手腕上扎的针孔太多,没法再扎,护士就从小脑门上扎。孩子受不了,每次都是一阵令人心悸的啼哭,直到嗓子沙哑哭不出声才慢慢停止。
天天打针输液,小孩子一看见穿白大褂的走来,就吓得小手紧紧抓住青莲的衣服,小脑袋拱进青莲的怀中,晚上也要沐青莲抱着才能入睡。半个多月后,青莲觉得腰部又酸又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为她后来腰间盘突出埋下了祸根。
于刚每天坐拖拉机、公共汽车往返于家里和医院,送去吃的、干净衣物,拿走需要洗的东西,回家洗好晒干。做这些事体力上的消耗算不了什么,但精神压力太大,这辈子没碰到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事。
这天,于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在青莲家门口的石凳上坐下,脑子里想了很多:要是不回上海,青莲到洛水县城分娩,会不会遇到这样倒霉的事?万一遇上,洛水医院束手无策,后果不堪设想了,可是到上海为什么偏偏遇到这样的事呢……青莲的母亲到医院看过几次,提出换换青莲。青莲不同意,她不愿母亲受这份累,再则自己照看更放心一些。
医院规定探视孩子不能进病房,于刚只能隔着玻璃窗看青莲和孩子。孩子一天比一天瘦,只剩下一个大脑袋、一双大眼睛。
于刚找到主管的老大夫:“孩子还有救吗?”
大夫面无表情:“现在……唉……”
青莲将孩子放到病床上,走到门口对于刚说:“你第一次到上海,进市里看一看吧。”
于刚无奈地摇摇头:“等孩子好了后再说。”青莲知道于刚的心里压着大石头,也就没再说什么。
二十多天后的一个上午,老大夫拿着一叠化验单回到办公室,皱纹密布的脸上露出笑容:“问题不大了,问题不大了!”
于刚急忙走进医生办公室,青莲也从病房赶来了。老大夫对照着化验单,一项项给他们讲,这项已经达到正常值,那项稍偏高……二人听着,脸上的愁容渐渐被吹散了。
“大夫,我们该怎样感谢你呢?”
“感谢什么?开始,我也没把握……”
于刚、沐青莲记下老大夫的名字,说以后要教育孩子,一辈子不忘老大夫的救命之恩。四天后孩子出了院。半个月后,二人带着孩子一路颠簸返回曼纳。
这次,车旅费、孩子的医药费花了一千多元。经公社和兵团领导特批,给二人报销了二百多元。剩余的七百多元,两人三年后才还清。
一九七九年,知青返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奔涌,大潮来势凶猛。“扎根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响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一下子被抛弃。在这些口号下垒起来的有形无形的建筑一下子倒塌了。
西连山农场的知青和支边青年大都准备返回,他们争着抢着地办手续,办完后就很快离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间间曾挤满男女青年的茅草房变得空空荡荡;橡胶林、稻田间没了知青的身影。曾经人喊马叫的西连山农场只剩下辛劳了二十来年的老工人,在烈日下、风雨里继续着惯性的人生。
作为西连山农场负责人的老姚,心里有些酸楚。自己这十来年做知青的工作,从他们的吃住到他们的劳动学习,哪一件不费尽心血呀!现在他们都要走了,这十来年的辛劳该怎么看呢?但是,老姚又是个很务实很善良的人,他早已看出,知青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不是靠具体工作能解决的,必须通过政策调整来解决;如果现在不返城,以后问题会越积越多;既然国家的政策是回去,就高高兴兴地送他们回去吧。
沐青莲好多天没去上班,也没办回城手续,她的动作、思维显得有些呆滞。
于刚下班回来,吃完饭,二人坐到茅屋前。于刚说:“青莲,我知道你心里怎样想的。”
青莲没吱声,把三岁多的女儿揽在怀里,亲着她那娇嫩的小脸。
“你还是要走……你和孩子回上海吧!我一个男人,在哪里不能待下去?”
“我带走孩子?”
“带走。我每月给你们寄钱去,每年都会去看你们的。”
青莲没吱声。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行,还可以考虑……”于刚话说了一半。
“考虑离婚?”
于刚迟缓地点了一下头。
沐青莲笑了,笑着笑着,竟哇哇地哭了起来。怀里的孩子不知所措,也跟着哇哇地哭起来。
于刚不知所措:“这不过是一种设想……不行就别这样做。”
“……我们结婚四年了,相识六年多了,容易吗?”
“……”
“我真心对你,你真心对我,如果说爱情,这就是爱情。这些年很多知青同居了,现在要回城,就谁也不管谁了,那算什么……我不能为了返城,把这个家撕碎,把我们的爱情撕碎……”
于刚被青莲的话震撼了:“你讲的这些都是心里话,我很珍重,也很感激,但是,政策是一堵墙,这堵墙我们翻越不过去的……”
“不管是墙不是墙,我们都要闯,而且要闯开。”沐青莲掏出手绢,擦干眼泪,抬起头,“要走,一起走!”
“一起走?”于刚惊讶,“按政策上海只会接收你,不会接收我的。”
“政策不接收你,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你,孩子不能没有你!”
这回于刚没吱声了。沐青莲放下孩子,把她抱进屋,拢进被子:“乖孩子,睡觉了。”
孩子很听话,伸手摸着妈妈的脸庞,慢慢地闭上亮汪汪的眼睛。
“回上海,户口……”于刚喃喃自语。
“办得了就办,办不了就算,现在办不了,总有一天能办得了!”沐青莲斩钉截铁。
“现在户口比什么都重要,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没有户口,就是黑人黑户,不仅什么正事也干不了,还会受到社会歧视……行吗?”
“不行也这样办!”
……沐青莲和女儿的返城手续办得很顺利,于刚的手续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公社负责办手续的傣族小伙子瞪大了双眼:“于刚,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们不能违反政策给你办出去呀!”
“这个手续要办不了,我们这个家庭就被撕裂了。”
“再说了,不符合政策,我们给你办了,上海也不会理这个茬儿的。”
“这次要不和我爱人的一起回到上海,以后人家就更不理这个茬儿了。”于刚咬紧嘴唇,“我可以写下书面保证,我的户口在上海落不下来,也不会再回曼纳麻烦你们,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保证书倒不必要,我们是为你负责。”办事员边唠叨边办手续。
他们将家具、厨具都送给撒瑞家,以示对两位好心人多年关照的感谢。撒瑞硬往沐青莲衣袋里塞了一百元钱:“……你们回去,什么都须重新添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安排工作?”
沐青莲没推辞,她知道要推也推不了,只是泪水不住地往下流。
于刚将小提琴包了又包,裹了又裹,提在手上。他伸出一只手要抱女儿,沐青莲笑指小提琴:“你抱她吧,那是你的女儿,这是我的女儿。”
于刚苦笑了。
一个星期后,一家三口在极度疲惫中回到上海郊区的浦清村。父母见他们回来,喜悦多于忧愁:“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他们仍住青莲分娩时住过的那间屋子,装粮食的木仓挪到青荷的屋子。青荷已分到上海郊区一家纺织厂当工人,平时租住附近的房子,星期天偶尔回来看看父母,晚上随便挤住一下就行。
简单地安顿下来后,二人带上档案、户口,去找到县知青安置办公室。公交车还像前几年那样拥挤,路面依然高低不平。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找到了县安置办公室。接待他们的是个老头,一副很和善的样子。“一个一个地办吧。”老头示意他们坐在长椅上,仔细地看起沐青莲的材料,看完递给沐青莲一张表。
沐青莲、于刚商量着填表,在“备注”一栏里填下了“请求接收丈夫于刚同志的户口,并给予适当安排”。
老头拿过表,看了一下:“你就在家等消息吧!休息一段时间。你们出去十年了,吃了不少苦了,不容易呀,不容易。工作嘛,是好是坏先干着再说……”
于刚觉得这老头很有点像勐罕公社管知青的唐大发,只是口音不像,肤色也白一些。
老头接着看于刚的材料,照样一页一页地细看。
于刚观察着老头的面部表情,这表情决定着老头的态度,态度决定着办户口的成败,户口的成败则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老头面无表情地看完后,将材料放进袋子,递给于刚:“这位,你不在接收范围。”
沐青莲拿出结婚证,用上海话解释:“我们结婚快五年,孩子三岁了,感情很深,他要落不了户口,我们这个家以后没法过了。”
老头抬头看着他们,表情木然。
“老伯,我们情况特殊,你就……”青莲说。
老头打断她的话:“落户的事要经过四五道关卡。下乡前非上海户口要办回上海,我们不能报,即使报了也要被打回来。”
“老伯,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我们?”沐青莲近乎哀求,又将材料交给老头。
老人嗫嚅着:“你们的处境、心情我很能理解,一个好端端的家……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你们年纪差不多,一个到内蒙古兵团,一个到黑龙江生产兵团,也都整十年了。我和他妈操了多少心呀!他妈落得个神经衰弱……二人上个月刚办回。”
“老伯,你……”青莲泪如雨下了。
“这样吧,你们把地址、电话留下,我尽力办。”老头将材料递给于刚,“情况我都知道了,材料你保管着,丢了就更难办了。”
于刚接过材料,千谢万谢。
回到家,青莲妈迎上来:“怎么样?”
青莲讲了在县安置办的情况,青莲妈反过来安慰:“不急,不急,急了管啥用!”
话虽这么说,于刚从青莲妈无奈的神情,读到老人的内心世界。这么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一下了增加了三个人,挤住在一起,而自己的户口太难解决了,她能不急吗?
晚上,于刚和青莲低声商量,将几年积攒的几百元钱交给母亲。青莲说,我妈不在乎这,等家里用得着时再拿出来。
于刚提出,能不能先找点零活干着。
“你不了解上海的规定,没有户口,就要有原单位的介绍,否则没人会接收你做零工的。你原单位是曼纳,户口已经从那里迁出了,还能到曼纳去开证明?”
不到一个月,老头打来电话,青莲的工作定了,到浦清小学当教师。于刚的接收问题,他反映过多次,上级说没有政策规定,不能接收。
青莲急了:“老同志,那……”
“……我是个办事员,什么事都得请示,领导同意了我就办,领导不同意我就什么也办不了。”话筒里传来的声音缓慢、苍老。
“这个、我们知道,不过我们连反映问题的地方也找不到。”
“这样吧,明天你们再来一趟,我们商量一下。你们也不要太着急了。”对方说完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到了县知青办。老头不紧不慢地提出,于刚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不是县区一级能解决的,可以写个材料,找一找市信访办公室,请人家向有关部门反映,作出特殊处理。
“找信访办……行吗?”于刚问。
“粉碎‘四人帮’后,各级政府都很重视信访工作,试一试总比不试好。”老头讲得很中肯。
二人心中闪动起希望的火星,一番感谢后返回浦清。当天晚上,他们按老头的建议,写成了书面材料,第二天一早出发,七找八找,中午时分送到了市信访办公室。
青莲到小学当老师,于刚在家里带小孩,等待市信访办的回音。
浦清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离大海二十多公里,刮西风时能嗅得大海的气味。村里都是菜农,收下菜交公社供销社,再运往市蔬菜公司。社员们都讲上海话,于刚大都听不懂,只好每天抱着孩子在房前屋后走来踱去。家里有什么活他抢着干,但做饭做菜总轮不上。青莲妈说,上海饭菜有上海的做法。
一个多月后,终于等来了市信访办的电话,说此事已向市知青办、民政局反映过,回答都说不符合政策,无法接收。于刚放下电话,仿佛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浇得心透凉。市里几个单位的意见都一样,还能找谁呢?
晚上,青莲从小学回来,刚坐下又起身,将小屋的门关上。回家以后,父母在户口问题上使不上劲,沐青莲觉得跟他们讲多了,只能使增加忧虑,因此商量事就尽量避着他们。
于刚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拖累你了,也拖累你们家了。”
“怎么又说这话了。”
“按现行的政策,确实不符合,还能有什么路……”
“今天在学校里,我想到一条路,与几位老师商量,他们都觉得应该试一试:我们去找找报社。”
“找报社,报社还能管这样的事?”于刚不大相信。
“这几年,报纸很为群众说话,管用不管用去了才知道。”
星期天一大早他们出发,中午时分找到市里一家大报社。挂在水泥柱上的黑字白底的大社牌,使他们感到威严和力量。
门卫告诉他们,报社星期天不上班,但群众工作部有人值班,值班室就在大门左侧的平房里。
值班的是一位身材瘦削、戴黑框眼镜的朱姓编辑。朱编辑给他们让座、倒水,请他们讲情况,听着不时微微点头。听罢,朱编辑颇为感慨:“不容易,不容易!你们的情况很特殊。这样吧,我写一份内参,向上级反映。”
于刚、沐青莲从挎包里拿出材料,递了过去。
“好好好。这样写起来就有依据了。”朱编辑将材料放进自己的公文包,看看天不早了,二人起身告辞。朱编辑说啥也要请二人到附近饭馆吃饭。其间,朱编辑很动情地说,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知青,很能体会他们的艰难,一定会尽力相助。末了还说“天下知青是一家呀”!
“天下知青是一家”,二人听着,心里暖暖的。
这次时间要短一些,也就半个多月,朱编辑很激动地给他们打来电话,连说“好消息,好消息!”要二人很快赶到报社,二人又惊又喜,两个多小时到了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