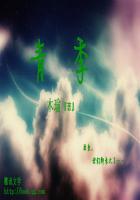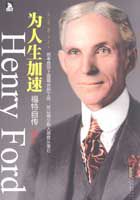前年回乌珠穆沁草原,顺便坐车去看乌拉盖河上的桥。那座桥是我年轻时的一道界线,分开不熟悉的南部几个公社。河流只是一道蜿蜒细水,但我们都知道乌拉盖河虽然缺水,但流得很长。
河边有一片废墟,同行的蒙古哥哥告诉我,这就是原先的旧庙。
我一怔。什么?旧庙?我只知道新庙!
哥哥指着斑驳的土块,一副资深牧民的表情。没有旧庙哪里来新庙?他那天好像个考古队员,有些自言自语。原来嘛,庙就在这儿,他说。
“是‘科尔沁八路’来的时候,庙烧掉了。”
“那是哪一年的事?”我惊醒般问道。
“好像是一九……几年?还是哪年……”
哥哥也记不清了。
后来我查了个头昏眼花。
最终弄明白了:我们的庙,是座乌珠穆沁的名刹。它像它统率的牧民毡包一样,迁徙数次。它的旧名是白音古秀苏木,大约曾依次在--乌拉盖中心的夏江淖尔、我们的道特大湖西岸的白音古秀,又经过一个红格尔敖包,最后定居在我熟悉的公社镇上,从而放弃了旧名,以新庙之名著称。这个名字和建筑都安稳下来的时间,据蒙文《道特淖尔史志》记载,是民国七年(1918)。
日本的信息大同小异。日文《大正时期的蒙古》记载:
“大正四年(1915),巴布扎布……经由喇嘛库仑,在白音古秀苏木遭支那军攻击。庙被战火烧毁,后来建起的庙被汉人称为新庙(シンスム)……巴军转至由库珠尔庙,支那军以大部队追击。”
大正四年(1915)得到川岛浪速支持的巴布扎布蒙古武装在白音古秀苏木被中国军队追歼,庙在战火中焚失。追剿巴布扎布的、新民国的北洋政府军队,就是日本资料所记的“支那军”。他们应该就是乌珠穆沁牧民所谓的“科尔沁八路”,这个词,我一直以为是指抗日的共产党蒙古武装,其实不是。
以前我不知从哪儿听来,是乌拉盖河洪水冲毁了旧庙。直到出版散文集《聋子的耳朵》时,我还以为:“新苏木营建的时间,一定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他在乌珠穆沁的东部打发掉自己青春的那段日子,正在旧庙被水冲毁,新庙尚未重建之间。”
其实错了,旧庙烧毁和新庙重建的时间,是民国初年。
史料中的“喇嘛库仑”和“白音古秀苏木”,都是东乌珠穆沁的佛庙。也许是因为--难道是服部老头强记暗诵了东乌旗东部的农乃庙、尕海庙,却让一座与他、确切说是与他那以扶立蒙古、瓦解中国为己任的恩师关系深切的庙,逸脱出了记忆?我记不清口不离庙的服部是否说起过白音古秀庙。难道老师没对弟子细讲么?恰恰唯有这座庙最要紧,川岛浪速曾在那里摔断了脚。
更可能是我的记忆出了毛病。在青春的六十年代,满嘴公社的新牧民我,虽然知道“我们公社的庙”叫做新苏木,但不知道白音古秀苏木即旧苏木其名。
--我依稀记得,服部对我说的“xin-sume”(新苏木)似乎抱着怀疑,他反复对我询问,而我则不耐烦地给他讲一通今天的行政地理。那么他是知道白音古秀失败的,老劳伦斯肯定给小劳伦斯诉说过家门史。他在琢磨我嘴里的新苏木。或许,就是为这股难忍的兴趣,他才走近了我!
而我,若想听见蒙古语冷冷说出“harqin baru”(科尔沁八路)这个新鲜词儿,更需等三十年的时光。服部没有料到,我也出乎意外--他最关心的一个地点居然真的就是我下乡的地点;我们的公社,它所以名叫新庙,只是因为旧庙在一场与日本人有关的战事中烧掉了的缘故!
没料到,这么巧--在我插队的公社,在我熟悉的河边,我曾徘徊其上的白音古秀苏木废墟,居然是一代日本浪人的折戟之地。
“地点”重合了。那苏木,不偏不倚恰在我家门之前,在我胡服蒙语、度过青春的地方!
多么想再和他深谈!……
现在,我知道从哪里谈起了。
我一直想,若是再次访问日本,我要找到他那位左翼女優,把当年的事问个究竟。我更盼着告诉他关于新苏木的变迁史,让他确认川岛浪速在大正年间的活动和思想。在讨论了日本右翼浪人的亚细亚主义之后,我要听听他在青海扶贫助教的思路。当然,也要谈及东乌珠穆沁的座座苏木以东,他和我的虽然相悖、却已经沟通的“青春位置”。
但是,当我重访日本时,却没去寻找他的家人。就像他不稀罕对他的宣扬一样,他在意的甚至不是理解。我早感觉到了:唯有一样东西值得重视,那就是人的气质。是的,若能做人不萎琐,举止有豪气,那么彼此之间的好感,渐渐一定导致理解和相知。
不误解,真相知,连说说都觉得太难。即便中国人能恢复古风知耻而勇,而且弃大国梦如粪土--与中国前定为邻的日本人,他们能与自己的代代出征的父兄师友,能与自己称霸亚洲的青春夙愿之地、鲜血淋漓之地决裂么?
这就是日本叙述的难处。
这就是日本情结的死扣。
我打算到青海去走走。我要到共和县、到海西州、到藏回杂居的村庄、到那些得到他援助的孩子们中间去--我将在他修葺过的学校门前坐下,慢慢琢磨他的谜语。但那片熟悉的土地,能给我以有力的启发么?我直面着巨大的悖论和矛盾。尕才让、法土麦、王小红,还有东乌珠穆沁、白音古秀、新苏木,你们能帮助我弄懂什么是“大亚细亚主义”,弄清什么是右翼、什么是志士吗?
我以为服部幸雄的故事,包囊了日本题目的一切范畴:
日本的近代、亚细亚主义、与欧洲竞争、满洲与蒙古、浪人和志士、知与行、感恩与谢罪、人的生命与精神……还有,这一切范畴中,左与右、美与丑、好与坏、罪恶与义举、歧路与正道……这一切的相悖与并存。
一介之人,因时代大潮的裹挟,会走过弯曲的路。不需说政治,最是政治的迷误无法闪躲!但在冲淘的时间里,一些人内藏的魅力会顽强地显示,不断地给人以或强烈或微弱的吸引。被扬弃的只是政治选择,那气质和魅力一定要挣扎,击败裹挟肉躯的历史,成全自我的轨迹。
--这就是我先讲了一个老人故事的用意。我需要预先申明叙述的难处,以及情感的纠缠。
读者不仅要对矛盾和悖论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还要有一份对泱泱中华天朝的反省,要准备读懂和迎面--由于漫长的失败史造成的精神萎琐,导致的对日本理解不足。
虽然并非很合适,毕竟算写出了一个引子。
我的日本涂抹可以开始了。
2006年冬初作于墨西哥普埃布拉。
2007年9月,赴青海参加服部幸雄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后回京再改。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之际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