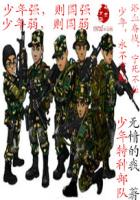大家都在吃饭,赵红雁端了一碗饭,挟了几块肉和一些菜肴去喂南宫妩月。她虽然很饿,但是牵动伤口,吃了一小碗就不吃了。陈然吩咐李三:“快去盛一碗肉汤过来,这位小姐受伤很重,不吃不行。”李三端了肉汤过来,陈然告诉赵红雁,你这位女友身体虚弱,必须补充营养。
战士们刚吃罢饭,陈然从里屋拿了个挎包出来。挎包上有外国字母,外形非常精致,打开一看里面有很多医疗器械。他对徐铮山道:“我学过战场救治,现在应该给受伤的战士治疗,否则他们会被感染,那就麻烦了。”徐铮山听了很高兴,回答:“我正为他们发愁,陈兄有医治本领真是再好不过了。”
陈然开始给战士们治疗,先给他们清创消毒、然后缝合敷药,很快包扎完毕。赵红雁在一旁见他的挎包并不大,但是里面医疗器械一应俱全,就连一些止血包扎材料也是现成的,扯开了就能用,很是新奇。询问:“你这些物件是那儿来的,救治伤员倒是非常方便,我们部队里从来没有这个。”陈然道:“这个是我德国同学寄给我的,德国军队里每个连队都有配置。战场作战伤员如得不到及时抢救是很危险的,有了这个挎包,伤员先做初步救治,然后送到后方医院,生存几率就要大得多了。说完这些,给受伤的战士包扎完毕。接下来该轮到南宫妩月了,这时陈然有点犯难了,他看出南宫妩月胸口受伤,要给她医治必须得解开衣衫,面对这样一个年轻艳丽的女子,他不知如何开口了。而她的伤势又肯定不轻,如果子弹留在体内就更加危险了,他只得朝赵红雁看看,询问她的意见。
赵红雁也看出了陈然难处,把南宫妩月搀扶到了陈然母亲屋里,让她在床上躺好。告诉她:“妩月,你的伤势很重,我想让陈然来给你治疗,你看怎么样?”南宫妩月紧锁眉头不语。赵红雁急了,又道:“这没有什么,他医术很好,你把他作医生看就可以了。”南宫妩月仍然不语,只是摇了摇头。赵红雁大奇,责备她:“你这是怎么啦?就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吗?不要忘了,即便我们顺利到达了根据地,给你医治的仍然有可能是男医生,难道你就不医治吗?”这回南宫妩月开口了,道:“那我就找女医生来医治。”赵红雁更奇,批评她:“南宫妩月同志,你的伤势很重,如果不进行治疗你的身体是支持不到根据地的。请你不要相信封建礼教,我们是革命队伍,新四军战士,早点治疗伤口,也是革命的需要。”南宫妩月脸面微红,眼泪泼喇喇掉落。赵红雁心软了,再次劝慰:“妩月,你不要想得太多,陈然是一个好人,我了解他,正人君子,你应该相信他的。”南宫妩月惶急起来,连忙摇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其实我是有难处的。”赵红雁又是奇怪,询问:“妩月,你究竟有什么难处,可以告诉我吗?”南宫妩月声音轻得像蚊子,道:“我,我胸口有一颗红痣。”赵红雁更加奇怪了,道:“一颗红痣?这又有什么,你怎么想得这么多?”南宫妩月涨红脸道:“你不知道的,这不是一般的红痣,我,我······”
话说到这里,赵红雁是一头的雾水,心想:“妩月这是怎么啦?难道就为了一颗红痣,不愿意让人看见,而拒绝疗伤吗?这不应该呀!妩月是上海人,又有文化,怎么会这么封建,这么迂腐呢?”她又劝慰南宫妩月:“别去管什么红痣黑痣了,你现在医治伤口要紧,这关系到你生命,你作好准备,我这就去把陈然叫来。”说完起身。南宫妩月急忙起来制止,抬起身子牵动伤口,婴宁一声倒下,喘息道:“不,不能的,情愿我承受苦难,也不能害,害了他。”赵红雁更是生气,道:“你胡说些什么呢?给你医治,你又怎么会害人了。”南宫妩月被逼急了,涨红了脸,央求道:“你如果一定要让他给我医治,除非,除非···”赵红雁立刻打断:“除非什么?难道让陈然蒙着眼睛给你看病?你就这么怀疑别人。”南宫妩月急得要流泪,又是解释:“不是的,你误会了,我是说有许多原因。”赵红雁也急得要跺脚,忍声责备:“妩月同志,现在是什么时候,万分危急,敌人恨不得立刻把我们消灭,而你却在这里摆什么大家闺秀,小姐脾气,真是不应该啊!”
两人说来说去,始终也说不到一块去,最后南宫妩月只得屈服了,她神情哀伤,低声道:“唉!怎么办呢?我听你的,就让他来医治吧!不过······”赵红雁总算嘘一口气,安慰她:“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关照他的,他也肯定会怜惜你的。给你医治过后,你很快就会痊愈了。”南宫妩月又想解释,一阵红晕上脸,想了一想,终究没有再说。
陈然随赵红雁来到屋内,感觉光线不够,吩咐赵红雁再去拿一盏灯来。轻轻解开南宫妩月外衣,看到渗出的血水已经将绷带和内衣粘连一起。他打开手术箱,拿出剪子,慢慢剪开绷带和衣服,揭去最后一层棉纱。顿时南宫妩月雪白的肌肤显现,躯体娇嫩,高耸的乳下一道伤口,一颗黄豆大的红痣,犹如宝石,晶莹剔透。陈然看见这颗红痣,微微一愣。南宫妩月紧闭双目早已经羞得满脸通红了。
陈然让赵红雁作搭手,脱去被污秽的衣服,南宫妩月雪白的酮体赫然显现,那白玉一般的光泽让人触目惊心。陈然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看待年轻女子,即便以前和董菌茹亲昵也没有如此。那天晚上在董菌茹房里董菌茹是关着灯的,而今天为了看清伤口赵红雁特地拿了两盏灯进来。他收敛心神,目不斜视审视创口,询问赵红雁:“你们是和日军突然遭遇,她被敌人打伤的?”赵红雁奇怪,询问:“你怎么知道?”陈然道:“根据伤口情况,敌人发射距离应该只在四五十米。”赵红雁道:“是的,敌人突然出现,她就被敌人击中了。”
陈然开始仔细检查伤口,轻轻触摸周围肌肤。南宫妩月忍受疼痛,胸口微微抖颤。
陈然长吁口气,告诉赵红雁:“不要紧的,子弹没有留在体内,只是贯通伤,这样就比较容易治愈了。”
陈然准备好了医疗器械,亲切告诉南宫妩月:“小姐,子弹只是斜向穿过,没有损伤胸腔,这样就不需要打开伤口,你忍耐一下,我给你消毒以后缝合,马上就会好的。”
南宫妩月默默点头,陈然随后清创消毒,接着缝合伤口。当他触及那颗红痣时候,又是凝思起来。针尖穿过乳旁嫩肉,南宫妩月微微皱眉。陈然又是安慰:“小姐,不会很疼的,因为你伤势不重,所以我就不给你用麻药,这样伤口就会好得快。”陈然缝合了伤口,拿了家里祖传的膏药轻轻敷上,给她打了抗感染针剂,再次鼓励:“小姐你放心,我给你用了最好的药膏,过得五六天,保证你就能痊愈了。”南宫妩月轻声谢过。陈然随后给她包扎,包扎时须托起她身体,他尽量轻微,抱起她身子就像抱一个襁褓的孩子。待一切处理完毕,就像当年安排赵红雁休息那样,去拿来了家里最新的被子,吩咐赵红雁给她覆盖胸口,告诫尽量不能受风。
南宫妩月见陈然额上渗出许多汗珠,目光很是怜惜,朝赵红雁示意,赵红雁见了,马上拿出手绢给陈然擦拭。
安顿好了南宫妩月,两人出来,赵红雁询问:“陈然,你说她受伤不重,很快就会痊愈,这是真的吗?”陈然道:“我没有骗她,幸亏子弹是近距离射入,如果是几百米以上那就反而情况严重了。”赵红雁很是疑惑,问道:“怎么远距离射中反而更加严重了呢?”陈然道:“日军三八式步枪有效射程八百米,一百米之****中身体子弹会贯穿而过,而如果是三百米以上,子弹就会在体内翻转和留存,这样反而会造成更大面积损伤。她是被敌人子弹斜向射入的,也没有洞穿胸腔,所以我估计再有五六天休养,她应该就会基本痊愈了。”
赵红雁吁一口气,道:“这样我就放心了,之前我还担忧,我们马上就要突围,她怎么坚持呢!”赵红雁放下心来,心情变得愉悦,笑问陈然:“刚才我见你看了她那颗红痣,怎么变了有点古怪了呢?”陈然有点尴尬,笑道:“你怎么观察这么仔细,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有一种古老的说法······”
赵红雁更加奇怪:“怎么他也变得扭捏起来?”再问:“怎么啦?有什么神秘吗?”
陈然连忙摇手,道:“不是,不是,如果今天有其他人来给她医治那就没什么了。”赵红雁再问:“你医术这么高明,为什么你就不适合呢?”陈然又是摇头,道:“不是这个问题,除非···除非···”
赵红雁大奇,刚才南宫妩月也是这样说的。她连续追问,究竟怎么回事?可是陈然再也不肯说了。
安置好了所有伤员,已经是午夜两点了。徐铮山召集了大家开会,商讨以后的行动方案。
赵红雁和徐铮山向大家谈出一个计划,告诉大家:“同志们,小分队出发前军部机要科曾经给过我们一个地址,是地下党组织在江都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告诉我们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去联络点寻求帮助。”他们又询问陈然是否知道一个叫三榜镇的地方,如果前去是否安全。陈然道:“三榜镇不远,西去二十多里地,如果你们想去的人伪装一番,应该没有问题。”徐铮山总算放心,当即决定,明天就由陈然护送赵红雁去和秘密联络点同志接头。告诉大家:“联络点和游击队有联系,如果得到游击队帮助,那么我们再去根据地就要顺利多了。”大家听了很是高兴,赵红雁乐道:“同志们,明天有我哥哥保护,你们就听我回来好消息吧!”
开完会大家准备休息,陈然带了小虎出门,告诉徐铮山:“我们这里地形特殊,哨兵可能不熟悉,我应该去看看。”徐铮山要求同去,被陈然劝阻了。
陈然走了,赵红雁坐在桌子一旁却不想动。徐铮山看她脸有忧色,询问:“赵红雁,还有什么问题吗?”赵红雁道:“陈然不知道我们有秘密任务,形势又这么危险,我想是否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这样他就能够更好帮助我们了。”徐铮山沉吟道:“情况还没有到最危急的时刻,按组织规定是不能说的,不过我还是想根据情况再作决定。”鲁大勇牛得草两人听了想说什么,但是犹豫了一下仍旧没有表示,随后大家都去休息了。
来到村头,陈然看见了哨兵,笑嘻嘻对哨兵道:“兄弟,你站在这里虽然视野开阔,但是你照顾不过来的,如果敌人来了,反而很远就能够发现你。告诉你一个诀窍,我们这里的地形很特别,你主要盯住西面路口就行了,其他地方敌人是无法进来的。”说完他指着另一个地方建议哨兵过去。哨兵跑过去一看,果然不错,连忙道谢。陈然又道:“我这狗很有灵性,我把它留在这里了,对你肯定有帮助。”说完作一个手势,小虎果然跑到哨兵的身旁蹲下,一双眼睛虎虎有神。哨兵看了大为高兴。陈然和他道别,又四处察看无恙,这才回去休息。
第二天早晨,徐铮山在家留守,赵红雁陈然扮作夫妻模样,出门走在前面,鲁大勇苏振明扮作伙计随后,四人出门上路了。
这天天气很好,太阳已经完全升起。走在干硬的泥地路上放眼四望,远处一簇簇树丛掩映的茅屋农舍,近处小河蜿蜒,波光粼粼。田野里冬季的庄稼,小麦片片葱绿。晨风吹拂,泥土芬芳,水露滋润。
赵红雁已经摆脱了昨晚坟地的困扰,今天心情特别轻松。一路走来,欣赏田野景色。细细打量义兄,涌上一阵爱怜:“哥哥比以前瘦了黑了,已经有了沧桑之色。”她关切询问:“哥,你这两年多来一直在干什么?”陈然道:“那年我们分别以后,我本想去追赶自己部队,但是已经太晚了,部队早已撤往湘鄂内地。我又打算去投奔徐州会战后撤退的汤恩伯部队,可是由于日军追击,汤恩伯一些国军急于逃跑,竟然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他们是想以此来阻挡日军,黄河决口,一泻千里,整个河南,苏北,顿时泛滥成灾。几千里里平原顿成泽国,河泥淤积几层楼厚。当时我刚入河南,就碰到了大批逃难的老百姓。得知前行无路可走,没办法,我只得又退了回来。”说到这里陈然神情肃穆,他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千里黄泛区一片汪洋沼泽,老百姓溺殍漂浮,凄惨一片。不由得慨叹:“妹子,你没有看见,那是多么凄惨的景象啊!日本侵略者凶狠,而政府又是何等的荒唐啊!”
赵红雁看他不悦,知道哥哥心地善良,为灾民难受,只得转移话题:“那后来你又如何了?”陈然道:“后来我去找到了国民党在江苏的韩德勤部队,本想和他们一起打鬼子,可是韩德勤打日本人没有心思,却和新四军搞摩擦格外起劲,为此我非常痛恨,上个月借口给母亲作三周年祭扫,请假回家,决定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