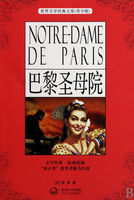却说寿娥领了一班娘子军,长驱大进,直捣香巢。进了门,恰巧梁冀又不在内,只有两个仆役在外边洒扫。只见她们凶神似的直往里拥进,忙大声喝道:“何处的野婆娘,胆有天大;你可知此地是什么地方,擅自闯进来?”他还未说完,寿娥娇声喝道:“给我掌嘴。”话犹未了,猛听得噼啪几声,又轻又脆,早将那两个仆役打了一个趔趄。有个丫头泼口骂道:“你这死囚,开口骂谁,不要说你这两个狗头,即便是梁将军来,我们奉着太太的命令来,谁也不敢来干涉的。”那两个仆役听说这话,吓得倒抽一口冷气,赶紧一溜烟的走了。寿娥忙喝道:“这两个狗头不要准她走;她一走,马上就要报信去了。”众人连忙喊她站住。她们只得努着嘴,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寿娥骂道:“我把你们这班助纣为虐的畜生,今天谁敢走,先送谁的狗命。”两个仆役也不敢翻嘴,只得暗暗的叫苦。
寿娥此刻火高万丈,领着众女人径到友通期的卧房门口。寿娥将帘子一揭,瞥见友通期坐在窗前,正自梳洗。寿娥不见犹可,一见她,把那一股无明的醋火,高举三千丈,再也按捺不下,泼口喊道:
“来人,给我将这个贱人打死了再说。”话犹未了,门外轰雷也似的一声答应,霎时拥进了一班胭脂虎,粉拳玉掌,一齐加到友通期一个的身上。友通期见了她们,已经吓得手颠足摇,不知所措,哪里还有能力去和她们对抗呢,只好听她们任意毒打了。不一刻,将一个绝色的美女打得云鬓蓬松,花容憔悴,满口哀告不止,寿娥打了半天,还未出气,忙命仆妇将她的八千烦恼丝,完全付诸并州一剪。霎时牛山灌灌,丑态毕露。友通期此时被他们一班人毒打,要怎么便怎么无法退避,欲生不得,欲死不能。寿娥见她仍是哀告不止,霍的将剪刀抢到手中,向她的樱口中乱戳,恶狠狠骂道:“我把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强占人家的男子,在这里成日价贪欢取乐,可知捞到你太太的手里,你这条狗命,也许是要送掉了。”她一面骂,一面戳,只戳得友通期满嘴鲜血,不一会,连喊也不喊了,呜的一声,向后便倒。众仆妇劝道:“这个狗贱货,差不多也算到外婆家去了,太太请息怒回去罢。”寿娥点点头,复又用手向她一指,骂道:“颇耐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在老娘的面前还装死呢;今天先饶你一条狗命,识风头,赶紧给我滚开去,不要和我们梁将军在一起厮混,老娘便和你没有话说。万一仍要在一起,轮到老娘的手里,料想你生翅膀也飞不去的。”她说罢,便领着众仆妇,打着得胜鼓回去了。
再表梁冀早上本来是要到工程处去监工的。他到那里指挥着众人,搬砖弄瓦,手忙脚乱的,一些儿也不让众人偷闲;到了巳牌的时候,肚子也饿了,正要回去用饭,瞥见一个守门的仆役,飞也似的奔来。气急败坏跑到梁冀的跟前,张口结舌,只是喘个不住。梁冀见他这样,料知事非小可,忙问道:“什么事情,便这样的惊慌?”他张着嘴,翻起白眼,停了半天才冒出一句来道:“不不不好了。”梁冀又追问他什么事情?他涨红了脸,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吞吞吐吐的说道:“不好了,夫人被大夫人带了许多女人,不由分说打死了,请将军回去定夺。”梁冀听说这话,好似半天里起了一个焦雷,惊得呆了,忙问道:“你这话当真么?”他急道:“这事非同小可,怎敢撒谎?”梁冀飞身上马,霎时腾云价的回到香巢,下了马,赶到房里,瞥见她睡在地上,满口流血,一头的乌云已经不翼而飞了。
梁冀见了这种情形,好不心疼肉痛,又不知怎样才好;像煞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团团转得一头无着处,蹲下身子,用手在她的嘴上一摸,不禁叫了一声惭愧,还有一丝游气呢.他命人将她从地上移到榻上,又命人去买刀疮药替她敷伤口,喊茶唤水的半天,才听得她微微的舒了一口回气。梁冀见她苏醒过来,不禁满心欢喜,忙附着她的耳朵旁边,轻轻地唤道:“卿卿!你现在觉得怎样?”她微开杏眼,见梁冀坐在她的身边不禁泪如雨下,绝无言语。梁冀又低声安慰她道:“卿卿!这都是我的不是了;如果我家教严厉,她们又何敢这样的无法无天呢?”她叹气答道:“将军休要自己引咎,只怪奴家的命该如此罢了。”梁冀忙问道:“卿卿!你现在身子上觉得怎样了?”她柳眉紧的答道:“别的倒不觉得怎样,可是浑身酸痛和嘴上胀痛罢了。”梁冀千般安慰百样温存。
友通期本来不是寿娥等一流人物,虽然这样的受罪,她却毫不怨尤他人,只怪自己的苦命。隔了几日,伤势渐渐的平了。因为自己的头发被她剪去,她便灰心绝念,决意要入空门,不愿再与梁冀厮混。可是梁冀哪里肯放她走呢。友通期求去不得,无计可施,便向梁冀哭道:“要得妾身服侍将军,非要先和你家大太太讲明了,得了她的准许才行呢,否则既来一次,难免十次百次,长此下去,是活活的将奴家的一条性命送去了么?”梁冀听她这话,只气得怒目咬牙,按剑在手,忿忿的对她说道:“卿卿!你尽放心,那个夜叉早晚都要死在我手里的多。我今天就回去问问她,她如识相,暂时一颗头寄存她的肩上,否则一剑两段,看她凶不凶了。”友通期哭道:“将军事宜三思,千万不要任性。你纵一时气忿,将她杀了,无论如何她是个正室,别人全要说我使撺掇的,居心想膺居正位呢。”梁冀道:“谁敢来说呢,请你不要过虑,我自有道理。”
他说罢,径自上马回来。进了府,早有丫头进去报与寿娥。寿娥笑吟吟从里面迎了出来,见了梁冀便道:“将军辛苦了。”梁冀便笑道:“自家的事情,有什么辛苦可言呢。”说着,手携手儿进房坐下。寿娥向他笑道:“前天错听人家一句话,带了许多人,到友姐姐那里,一场胡闹,过后我细细地想起来,着实无味,万分抱歉。这两天我本预备前去到姐姐那里去赔个罪,一来教她消消气,二来将军的面子上也好过去了。不想将军今天回来,我却先给将军赔个不是,明天再到姐姐那边去赔罪罢。”梁冀听罢,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哈哈大笑道:“我早就料定了,夫人是一定错听人家的话了,不然,永不会做出这没道理的事来呢。既是错了,好歹都是自己人,什么大不了呢,明天也用不着夫人亲自前去。我便替你说一声就是了。”
她笑道:“随便什么人,自己做错了事,当时都不会省悟的,过后却能晓得错处了;即如这事,理论起来,她不是和我合作一副脸么?我将她糟蹋了,岂不和糟自己的面子一样么?”梁冀听她这些话,真是喜不自胜,忙道:“夫人休要只是引咎,这事只怪我不好,我要是不去和她娇识,也不致惹夫人生气了。”她笑道:“将军哪里话来,一切的不是,都因我的脾气不好,才有这场笑话的。官宦人家,谁没有三房四室的呢;总而言之,只怪我的器量太小了,不能容人罢了。”
看官,这寿娥本来是个淫悍非常的泼辣货。她和友通期还不是成为冰炭了么?焉能又就说出这番讲情顺理的一番话来呢?读者一定要说小子任意诌张了,原来有一个原因呢。那天寿娥将友通期毒打了一顿,打得奄奄一息,胸中的醋火,也算平了,回得府来迎面就碰见了庆、雪两儿。寿娥谁都不怕,大模大样的将他们带到房中饮酒取乐。雪儿对她说道:“我们在家里度日如年的,何等难过!你现在也不想回去了,所以我们无法可施,只得前来就你的教了。但是长此下去,一个天南,一个地北,一朝想念起来,真要将人想杀了呢,无论如何,都要想出一个良善的方法来才好呢。”她沉吟了半晌,便向他们笑道:“有了!你们先住在这里,等他回来,我自有方法,将你们留在府中,好在他多半不在家里,那时我们不是要怎么便怎么吗?”他两个听了大喜。今天寿娥听说梁冀回来,心中暗想:
“如今我将他的心上人儿打得这个样子,料想他必不甘心,他回来一定是替她报复的了。我反不能去和他撑硬,只好先使个柔软的手腕,来试验试验,如果他服从,那是再好没有了,万一不从我的话上来,再作道理。”
她打定主意,见了梁冀,说了一番道歉赔罪的话。梁冀哪知就理,喜得眉开眼笑的。她见梁冀已中圈套,趁势又用许多想煞人爱煞人的甜蜜米汤,灌了一个畅快。把个梁冀弄得乐不可支,手舞足蹈的,对她笑道:“我梁冀并非是自己夸口,像我这样的艳福,满朝中除却万岁爷,恐怕再也寻不出第二个罢。”她笑道:“我有一件小事,要奉烦将军。”他忙道:“什么事,只管说罢!我没有不赞成的。”
她道:“就是我们老太太,前次我在家里的时候,她曾对我说的,我既然蒙将军的福泽,身荣名显,但是别人家每每因着女儿飞黄腾达的,可是我们的家里,也没有三兄四弟,所以也占不着你的光。不过我们太太现在收了两个义子,满心想请将军提携提携,他们得到个一官半职,也好教她老人家欢喜欢喜。那时我却未敢答应,今天特地来告诉你,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呢?”他顿脚道:“你何不早说?前天我手里还放出两个县缺去呢。且罢,教他们来到我府中,在这里守候着,不上三两月,一有缺,我随便就替他们谋好了就是了。”她假意谢道:“将军肯体凉家母的心,妾身也就感谢不尽了。”他笑道:
“这又何必呢?我替你家效一点劳,还不是应当的么?”他们又谈了一会子,天色渐晚。这夜梁冀便留在府中住宿。到了第二天,梁冀临走的时候,向她叮咛道:“教庆、雪两儿早点来要紧。”她假意应着,其实早已到府中了。梁冀还在鼓里呢。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又到八月间了。梁冀只恋着友通期,寿娥便与雪、庆在府中厮混着,各有所得,绝不相扰。梁冀因为自己有了心上人,寿娥的私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知故昧的让她们一着。寿娥在六月间,得着封浩,便是植帝封她为襄城君,仪文比长公主。这一来,寿娥越发骄横得不可收拾了,在私第的对面,又造了一宅房子,周围二十多里宽阔,楼阁连云,笙歌匝地,说不尽繁华景象,描不出侈丽的情形。
满朝文武,十有八九都是梁、孙二家的私人。她心还未足,将和熹皇后从子邓香的女儿邓猛,进到宫中。桓帝见她的姿色,足可压倒群芳,便封为贵人。寿娥暗地里却教她改姓为梁,伪言是梁冀的女儿。原来邓香中年就弃世了,单单留下邓猛一人,所以寿娥为保固自己的根基起见,便将她改名换姓的,进与桓帝。她只有一个亲眷,便是议郎尊。寿娥深怕被他知道,可不是耍的,暗地里与梁冀设计去害尊。梁冀道:“这尊生性不苟,深得桓帝的欢心,万不能彰明较著的去陷害他。要想将这个贼子除去,只有暗中派刺客,将他结果了,那才一干二净的毫无痕迹呢。”寿娥道:“这计好是好,可是有谁肯去冒险呢?”梁冀沉思了一会,便向她说道:“我们这里不乏有武艺的人,可是这事太险了,恐怕他们畏缩不前;依我的主意,将他们完全带来,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有谁肯将尊结果了,赏绢五百匹,黄金一百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寿娥拍手道妙,随命将府中所有的家将,完全请来。梁冀将来意对大家说了一遍。
那些家将好像木偶一般,谁也不敢出来承认。
梁冀好不生气,正要发作,猛听得一声狂笑,屏风左边转出一个人来,满脸虫髯,浓眉大眼,紫衣找扎,大踏步走到梁冀的面前,躬身说道:“不才愿去。”梁冀闪目一看,却是侍尉朱洪,心中大喜,忙道:“将军愿去,那就再好没有了,可是千万要小心为好。”他笑着,用手将胸脯子上一拍说道:“请将军放心,只要小人前去,还不是探囊取物么?”
他说罢,在兵器架上取下单刀,往背上一插,飞身上屋,径向尊的府第而来。到了他家大厅上,他伏着天窗,往下面一看,只见邮尊和众人正自在那里用晚膳呢。他纵身落地,一个箭步,跳进大厅。
众人中有一个名叫寅生的,他的眼快,忙大声喊道:“刺客!刺客!”
慌得众人连忙钻入床肚。
这时尊府内家将,闻声各拖兵器,一齐拥了出去,接着他大杀起来。自古道:能狼不如众犬,好手只怕人多。朱洪虽有霸王之勇,也就无能为力了,不多会,一失神,中了一刀,正砍在他的腿上。
他大吼一声,堆金山、倒玉柱的跌了下去,被众人横拖倒拽的擒住了。尊升坐询问。他起首还嘴强,不肯直说,后来熬刑不住,便一五一十的将梁冀的诡谋完全说了出来。
尊勃然大怒,便命人将朱洪拘起,就在灯光下修一道奏章,又将朱洪词抄录一通,更不延留,立刻将朱洪带到午朝门外。黄门官便问他何事进宫。他道:“现在有紧急的要事,烦你引我到宫。”那黄门官见他深夜前来,料知事非小可,便向他说道:“请大人稍待片晌,等我先进去通报万岁一声。”丙尊点首。那黄门官脚不点地地进去了。不一会,复行出来,对他说道:“万岁现在坤宁宫里,请大人进去罢。”他又吩咐御林军,将朱洪守着,他自己一径向坤宁宫而来。
到了坤宁宫的门口,只见植帝与邓贵人正在对面着棋。他抢近俯伏,先行个君臣之礼。桓帝忙呼平身,便问他道:“卿家深夜进宫,有何要事?”尊道:“请屏退左右,微臣有奏本上读天颜。”桓帝拂退残基,龙袖一甩,左右退去。丙尊便将奏章和朱洪的供词呈上请阅。植帝看罢,大惊失色,忙道:“卿家有什么妙策,可以铲除这个欺君贼子呢?”尊奏道:“万岁德被四海,仁驰天下,所以将这贼子骄纵得不可收拾;现今此贼威权并重,眈眈有窥窃神器之野心,万岁若再不施以决裂手段,恐怕向后就要不堪设想了。”桓帝道:“孤家何尝没有这样的用意,可是这贼根深叶密,耳目众多,只怕事机不密,反生别变,所以迟迟至今,都未敢贸然发作,如今这贼的野心愈炽,却怎生应付呢?”尊奏道:“依臣愚见,要除此贼,须用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计划才行呢。最好今夜派人前去将他捉住,然后那班奸贼群龙无首,眼见得不敢乱动了,未知万岁以为如何?”桓帝瞿然答道:“卿家之言,正合孤意。”邮尊又奏道:“此事刻不容缓,缓必生变,他既派人来刺微臣,再停一会,他不见朱洪回去,必起疑心;疑心一起,势必要预防,那可就棘手了。最好请万岁即发旨,差御林军前去兜剿,他一个措手不及,才是千稳万安的计划呢。”桓帝大喜,便星夜下旨,将九城兵马司张军召来,命他领了三千御林军,前去捉拿梁冀;又另命扬威将军单超点五千御林军,把守各处禁口。张寸军带着御林兵,直扑梁冀府而去。
再表梁冀将朱洪差去之后,便和寿娥商议道:“如今朱洪去了,能将邮尊结果了,是再好没有;万一发生意外,那怎么办呢?”寿娥笑道:“将军大权在手,朝中百官,谁不是你的心腹呢?就是有什么差错,只消动一动嘴唇皮,硬便硬,软便软,还不是随你主张么?”梁冀听她这番话,正要回答,猛听得人嘶马吼的,呐喊的声,不禁心中疑惑道:“这夜静更深,哪里来的人马声音呢?莫非是巡城司捕捉强盗的么?”他正要起身出去探看探看,瞥见一个家丁,一路飞了进业,大叫祸事来了。梁冀不由得大惊失色。这正是:
刀兵加颈犹嫌晚,死到临头尚不知。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