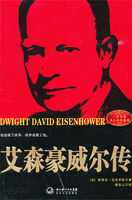中秋节转眼就到了。八月十四的这天晚上,桂兰买来了两包月饼和十斤苹果,准备给婆婆送过去。于是,如柔也买了两包月饼,和婆婆一起送了过去。当然这两包月饼也是她和小硕口舌之争赢得的胜利品。
第二天,王茵没有去赶集,因为秋杰来,这不,她高兴地在嫂子那屋看着电视,突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便走了出去。
不多时,秀琴进来了,对也正要出去的如柔说:“给你拿几块月饼和几个苹果来了。”
“奶,留着你吃吧,不用总惦着我。”
老人一笑,更显满脸的褶皱。“家还有忒多呢。指着你爷我俩该吃多少了哇。”说着,就向外走去。
“奶,你不呆会儿?”
“不了。”老人回头一笑说,“呆会儿该来打麻将的了。”
把老人送出去后,如柔就看着那四块大月饼和六个大苹果发呆。想了一会儿,她就又找了一个袋,往里装了两块月饼和三个大苹果。见小茵又进来了,忙说:“奶给咱们姐俩拿几块月饼和几个苹果来了。见你没在家,就放我这儿了。给!”
小茵看了一眼,纳闷地说:“她今天可不发啥善心了?”
上午十点左右,宏远和他的同事高增保来了。这个高增保是天津的,高高胖胖的,长得挺帅,穿着也很阔。订亲、结婚,如柔都见过的,一见他来了,她忙走过去,亲热地和他打着招呼:“高叔!”
增保一看,笑呵呵地说:“侄媳妇儿胖了。”
她微微一笑,又和刚刚进来的秋杰打了招呼,便把他们迎了进去。本来不大的屋子更显得狭小。她给他们沏了几杯茶水,见他们亲热地聊着,便退了出来。
赶集买菜的小硕也回来了,大家便忙起了饭。
如柔把丈夫抻到了外面,说:“顺便把爷奶也叫过来吧。就是添两双筷子两个碗,还显着好。”见他略显不满,又小声地说:“老公,答应我,我好给你生个胖小子。”
他被她逗笑了。
她撒娇地冲他皱皱鼻子,去叫二老了。
午饭很是丰盛,也很是热闹。增保一边喝酒,一边和二老说话,还不时地跟宏远、秋杰、小硕干杯。桂兰呢,也一边吃着饭一边和婆婆说着话。如柔也不时地给爷爷奶奶、高叔夹菜。只是在这活跃之中,也有着一丝丝的不和谐:小硕和小茵对爷爷奶奶的到来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明显带着反感。
傍晚,高增保走了。于是,热闹了一天的小院也霎时宁静了下来。
如柔和小硕刚刚吃完饭,忽听北门响,忙去开门:“呀,二婶,快进来!”
云霞进来了,环视了一下,坐在了沙发上说:“小硕,如柔,我听你奶说秋杰来了,你们说,他要是不来,二婶这个委屈到啥时候也不能说。今天他来了呢,我得跟你们说说。”
如柔给她倒了一杯水放在了她跟前的茶几上。
“当初,秋杰给小茵来电话,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费啥心了呀,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秋杰在那头怎么骂我,咱们不说。就连你妈和小茵,她们娘俩都不来搭理我的呀。小茵在集上碰见我,碰出个大疙瘩她也不来和我说话的呀!你们说,我这个二婶哪点儿对不起她们呀!”她抹起了泪,“反倒像欠她们的了!我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今儿秋杰要是不来,这话到啥时候我也不能说,我委屈也没委屈别人身上。今天秋杰来了,你妈要是会办事儿,要是和我说一声,把小茵和秋杰叫到我跟前,把这事儿说开,啥事儿都好办了。”
“二婶,你别生气了。我妈呢,是不会办事儿。这事儿,我跟秋杰说说。”小硕说。
云霞抹着泪说:“那最好不过了。不然我这个二婶成啥了呀。”
云霞走后,小硕和如柔去了倒座。没想到刚一进去,本来躺着的桂兰就从炕上爬起来,指着他俩说:“我告诉你们,反正我和他们是不走着了,就看你们了!”
在椅子上坐着的宏远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地说:“这事儿呢,她要是来和我们说,也就啥事儿没有了。这么一来呢,这个疙瘩反倒越来越解不开了。”
“小茵从那屋都直哭呢,说秋杰刚来,她就闹闹哄哄地找来闹哄。”桂兰说。
“妈,人家没闹哄,也只不过是她的嗓门大了些。”如柔解释。
“咋还没闹哄呀!开着窗户,听得真真的呀!”宏远说。
“我看你跟他们好像忒近,那你跟他们走着吧!”桂兰说这话的时候,拿起了一把扫炕的扫帚就把那堆放在炕角的嗑完的瓜子皮子发泄似的扫在了地上,也扫在了宏远的腿上,它们就那么地在那里呆着;也扫了如柔一身,即刻又掉了下去。
如柔只好愣愣地看着他们,似乎在看着他们赤裸裸的丑陋的灵魂。
而小硕,看着母亲动怒了,又不禁冲如柔嚷:“你给我滚开!滚得远远的!”
这晚是八月十五,月儿好姣洁,也好“圆”。
如柔伤心地回到自己的屋,给他留下了一封信,走了。信是这样写的:
王硕,我恨你们的这个家庭!这里没有温暖,没有爱。有的只是狭隘与报复!为什么你们不学着去理解别人、宽容别人呢?那样也将会带给你们快乐!恩恩怨怨何时了!你们不觉得累吗?难道你们快乐吗?我好羡慕、好羡慕那一个个和和美美的家庭。那里满是温暖,满是呵护。我羡慕极了,难道你不羡慕吗?
王硕,我在你们的这个家庭中生活了将近一年,你知道带给了我什么吗?只有不安和痛苦!我过够了这种日子。更不愿意我的孩子一出世就受到这样的熏陶。这样的孩子,心理是不健全的。就像你!
王硕,我们离婚吧!我再不能够承受。
她独自走着,突然发现天黑了。只因有月,才使得一切东西都清晰可辨。但这一发现也突然使她感到了毛骨悚然,听,那窸窣窸窣的声音。她赶紧快走,又总感觉脚后面有什么东西跟着。她知道那只不过是自己的脚跟碰到了什么东西,或者纯粹是想像。好在时不时地看见一两个或许是上班的夜行人,尽管他们都会奇怪地看她一眼,但她并没有害怕,反倒感到一些轻松。这时她才明白:她拒绝的仅仅是黑暗。她就这样地走着,走着,也不能不地想起小硕:他是否发现了那封信?他是否在找自己?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小硕因为她走,也因为母亲的气愤,在找她的时候碰见了秀琴,而把一切责任都怪在了这个老人的头上。他的谬论是,如果她不告诉云霞秋杰来了,云霞就不会来他家了,母亲也就不会生气了,她也就不会走了。当然,如果他不碰上他的奶奶,他也不会去找她理论这些,只是不巧的是偏偏让他碰上了。于是又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虽然没有血淋淋的事件,但每个人的心都会滴血。好在她没有目睹这个场面。她带着那种解脱般的轻松。好不容易走出了这条羊肠小道,踏上宽阔的柏油马路,这时她笑了。她看见了出租车,虽然只有一辆。
一见到女儿,学强和秀丽不由得又惊又喜,但明显吃惊远远大过欢喜。秀丽打量着女儿说:“你咋来了?小硕呢?你怎么这时候来了?你哭过吧?”
如柔再也忍不住:“妈,我想离婚!”说着,扑到了母亲的怀里。
“傻孩子,离婚也是随便说的。告诉妈,到底怎么了?”
听完女儿的哭诉,学强气得胡子茬都跟着乱颤:“我怎么把你给这么一家子人家了呀!唉,如柔,你也别哭了,不是离婚嘛,爸支持你!”
“离婚也是说着玩的?”秀丽嚷。
学强吹胡子瞪眼地指着秀丽嚷:“你挑的好女婿嘛!来了当个宝似的。你听你闺女说的,你也听见着!又让你闺女滚着,又让你闺女死去的!”他发泄了一通,看见女儿还在哭,又冲她嚷:“你也是!让你滚着,你怎么不家来呀!那时家来的话,孩子小,打去就算了。现在你都该生了,你跑家来干啥呀!”
秀丽瞪着丈夫说:“你说这个有用呀!”
学强的火气依旧旺得很,冲着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睡眼惺松的如雪说:“你搞得那个对象,那家子人家也得好好挑挑,别像你姐似的!”
如雪揉了揉眼睛:“我才不像我姐这么傻呢。我才懒得管他们的那些事呢。”
“你们爷俩少说句中不?没人把你们当哑巴卖了!”
学强看着秀丽,不禁说:“你闺女这么委屈,你这个当妈的倒无动于衷。”
秀丽一下子掉了泪,瞪了眼丈夫:“你!”
学强不再言语,但看了看如柔,又忍不住说:“你也别哭了,孩子生下来给他们送去。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有的是。”
“你!你不教给闺女好话!”
“我说的是差话呀!我闺女既然做出离婚的决定了,那就一定有她非离婚不可的理由。再说我早就说过,小硕那孩子,根本就不适合我闺女。我闺女既懂事儿又稳重,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王硕不配我闺女一个角儿!如柔,爸支持你离婚!”
秀丽瞥了一眼他,对如雪说:“带你姐过去睡觉吧,很晚了。”
真难想象,一夜之间天公就勃然变色。早晨,已是乌云密布,雷声轰轰。看来,一场暴风雨是在所难免了。
秀丽正忙着拾掇院子里怕雨淋的东西。
雨说来就来了,大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打下来,打在那未来得及拿开的水盆里面“叮当”作响,打在地上,成了一个个深褐色的斑点。顷刻,地面全湿了。
学强站在门口,唠叨:“什么鬼天气?昨天晚上大月出着,还特别晴呢,今儿早起就下这么大的雨?”
“不下雨怎么种麦子?”正在扫地的秀丽说。
“玉米棒子还没擗呢,就种麦子?”他冲她吼。
她也嚷:“你怎么了?玉米棒子这不就可以擗了嘛,擗了不就得种麦子吗?不下雨怎么种?你还得等雨。”
学强自然明白自己怎么了,看见心爱的女儿深更半夜跑回来,他几乎一夜未合眼,怎么可以有人这样对待他的女儿?那是他怎样乖巧的女儿呀!王硕这个王八蛋,怎么可以这样不珍惜他的女人呢!一想起王硕,他就恨得牙根痒痒。他走回屋内,坐在椅子上抽着闷烟。
这时,隐约听见雨声之外有三马子的“突突”声。
如雪忙说:“妈,一定是我姐夫来了。”
学强一听,霎时来了精神,站起来指着如雪说:“别给他开门!让他在外面浇着!”
这时,外面的门响了,而且越敲越响。
如雪走了出去,把门开开一条缝,看着那从头上直往下淌水的小硕说:“你来干什么?”
小硕一抹脸上的雨水,着急地问:“你姐在不在这儿?”
“我姐?”如雪眉毛一挑,说:“我姐已经好长时间没家来了,怎么跑这儿找我姐来了?你去别处找吧,我姐不在这儿。”说着,“啪”地关上了门。
小硕“嘭嘭”地敲着门大声说:“如雪,你姐昨晚上就走了,我知道她一定家来了。如雪,如雪,告诉我,我很担心她。”
如雪冷不丁地一开门,使小硕打了个趔趄。如雪说:“你也知道担心她?好吧,我告诉你,我姐确实来过这儿,但她跌了一跤,被我爸妈送进了医院。好了,你走吧。”她刚要关门,门被小硕抓住了。
“如雪,是真的吗?那是哪家医院,我要去见她。”
“哟,堂堂的大孝子,也知道心疼媳妇儿了。你早干什么去了?给你怀着孩子,侍候着你,还得受你的气!你还让她滚着,让她死去!你还有没有人性?现在,我也告诉你:你给我滚着!”如雪又要关门,但门还被他抓着。
雨地里的小硕冻得直发抖,他说:“如雪,你说什么都可以,你让我见见你姐,我就踏实了。”
如雪又要说什么,却见父亲走过来说:“让他进来!”
刚才就一直想出去却被丈夫拦着的秀丽见他那瑟瑟发抖的样子,一边找衣服一边说:“快把衣服脱下来,换上件你爸的,不然感冒了。”
小硕顾不得换衣服,径直走到里屋,见到如柔,一把抓住她的双肩,上下打量着:“你没跌跤吧?”
如柔狠心地把他的手从肩头拨了了下去,走进了另一屋。
小硕换过了衣服,还是冷得直发抖。
学强铁青着脸说:“如柔为什么回来?”
“可能,可能是因为我二婶他们吧。”小硕含糊其辞地说。
把小硕的衣服晾在外屋的秀丽进来说:“你们那一大家子的事儿也说不清谁对谁非,反正一个巴掌拍不响。都稀里糊涂的,啥事儿都过去了。要是啥事儿都计较,谁也弄不好。我们如柔就是想让你们这一大家子和和睦睦的,谁知道净受夹板儿气了。再说你当孙子的,给他们和和稀泥,啥事儿也都过去了,你可倒好!”
小硕不爱听了,顶撞着说:“昨天中午刚刚叫的我爷我奶,昨天晚上我奶还说没我这个孙子呢!”
“你们那一家子的事,你也别说了。”学强冲他摆摆手,“你就说说我们如柔怎么样吧?”
“她挺好的。”
“你知道她挺好,你还骂她,让她滚着,让她死去!你说说有没有这么回事儿?”一提起这事儿,学强就恨不得把面前的这个男人撕碎。
“我,我不记得了。”
学强依旧铁青着脸,就似天边那浓浓的云,“你别含糊其辞地说。你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
小硕看了看岳父,心里有些犯憷。他知道他的脾气,也知道此刻的他就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如果哪句话说得不当,火山就会爆发,那时将会一发不可收拾。他怯怯地说:“爸,我错了。其实我就是脾气不好,我对如柔……”
“你对如柔还挺好的,是吧?”学强一下子站起来,那速度快得就像是被弹起来的一样,他瞪着眼说:“你对她好,30里的道儿,她这样的身子,大深更半夜的,她跑家来,想跟你打离婚!”
小硕不由得后退了一步,但后面是张桌子,他只得又把身子往外挪了挪。
秀丽走上前来,把丈夫按在了炕上。又转过身来对小硕说:“这回儿如柔家来,我这个当妈的也很难受。虽说俩口子过日子,都得有个磕磕碰碰的,但说气话也别说过分了。你让她滚着,万一道上有个闪失,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你后悔呗?让她死去,万一她真想不开,小心眼上来真死去,以后你还惦着过呗!啥事儿呢,都商量着办。再说,如柔也不是不懂事,也不是我向着个人的孩子说。”
看着瑟缩的女婿,学强也突然想起二十几年前,自己也曾这样地站在岳父岳母面前,几乎一样地情形。不禁竟有点儿同情起他了。他语气缓和了一些说:“如柔呢,她就该填了。这时候她有个气顺气不顺的,你让着她点儿,别老跟她打架。别人也笑话。你也该当爸了,啥事儿都考虑考虑,别别人说个啥就是个啥。”
站在这里,就好像一个进劳教所的失足青年接受再教育一样,令小硕感到窒息得要命,他想逃。“爸、妈,如柔在这儿呢,我也就放心了。我走了。”
“你吃完中午饭再走吧,再说还下着这么大的雨。”
“不了,我现在就回去,让如柔消消气,过几天我就来接她。”说着,跑了出去,把车开动了,走了。
而学强正在数落秀丽:“你真是丈母娘疼女婿——实打实的。这么个混蛋,瞎白六九,你喜欢他干啥?还是惦着等着他干啥呀!说给你,如柔他是接不走!”
“哪家两口子不打架呀。说说这个,再说说那个过去就中了。好像就你家有闺女!”
“不是就我家有闺女,他们那是个人家?”
“就你们家是人家!中了吧。”
学强哭笑不得,冲秀丽摆摆手:“你快该做啥做啥去!不跟你吵了。呆会儿做饭了,把那个白条鸡给如柔炖了。”
在娘家住的日子里,如柔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做女儿的幸福: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也都可以不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做,不想做的事也没人强迫自己做。她又想:女儿过的是一个人的日子,而媳妇儿过的却是一家人的日子。但女儿迟早也是要担负起家庭沉重的十字架的。这样一想,她就释然了。但于每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又有一股忧伤,无法排遣的忧伤困扰着她:如果回到那个家庭,就又将面临着那个家庭几十年解不开的矛盾之中,就又将面临着和他无休止的争吵。她真希望那种日子到此为止。而如果离婚,孩子怎么办?不能让他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呀!虽然和他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爱好,但她不能否认的是她爱他,这应该足够了。
于是,当小硕接她来的时候,她回家了。
一回到家,她突然发现自家窗跟下用砖码起了一个猪圈,里面蹦跳着一群小猪。她不觉很是纳闷,也很是心烦。走进屋内,她问他:“怎么在窗跟下养起了小猪?”
“你走的那天当晚,我就和我奶他们又打了一架。结果第二天妈去喂猪,我奶前门闩后门顶,不给开门。没有办法,我跳墙过去了,打开了大门,和爸妈顶着那天的大雨把大猪弄了过来放进了猪圈里,就把小猪圈在这儿了。”
已经没有能力再问他为什么又和他们打架的她此刻听着那么多小猪嗷嗷乱叫的声音,心烦得落了泪。说:“怎么没养在东屋的窗跟下?”
“东屋的窗跟下向阳儿,过两天就该擗玉米棒子了,等把玉米棒子剥了,惦着把玉米棒子晒那。”他说着,走近她,环住了她的腰,轻轻地摸着她的腹部说,“好在现在不用开窗户了,也听不到臭味。如柔,委屈你了。”
她不作声,只是掉泪。她能说什么呢?也许,接受了王硕这个男人,就必须接受他的这个复杂的家庭。什么对的,什么错的,什么矛盾,统统都得接受。也许,这就是爱屋及乌吧!只是在小猪饿得嗷嗷乱叫的时候,在小猪把砖码得围墙撞倒一面,相继跑出来,那条“赛赛”又冲它们汪汪乱叫的时候,在下雨的时候,尤其是在每个宁静的夜晚,小猪叫起来的时候,她感到特别烦躁不安,想哭!
转眼就是秋收季节,一年之季在于春,一年之季也在于秋。这时候,农民们虽然感到了收获的繁忙,却也体味着收获的喜悦。
农家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上的柿子也红透了,挂在那已经开始往下落叶子的树上,是那么好看,又是那么诱惑人。只是,挂在树上的柿子很少。有的,是熟透了掉在了地上;有的,是还未熟透的时候就被摘了下去。于是,那挂在枝头的零星的几个大红柿子,就更惹人眼馋。
桂兰和如柔正在院子中剥玉米棒子,忽听“啪”的一声,原来是一个柿子掉到了狗窝的附近。
桂兰忙喝住正要往柿子那儿去的“赛赛”,跑了过去,捡了起来,啃了几口,扔进了垃圾桶里。看着树上挂着的那几个红柿子,对如柔说:“咱们把那几个也够下来吧,不然掉地上都白扔了。”
她应了一声,忙取来那个带着套儿的大竹杆,递给了她。
桂兰仰着头,好不容易地够下来一个,递给她。
她接过,洗洗,就边吃边看着她够,说:“等我们的宝贝儿出世了,也一定爱吃柿子。”
桂兰笑着说:“随你呗。”
她也笑了,说:“不行是随她奶。”
娘俩儿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