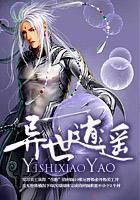杜云飞在警察来之前就离开了,这说明他的到来是不能公开的,那么,他要找的是什么?
我狐疑的趴着窗口看着他快速的跑进北洋剧院后院的巷子里,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事儿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的,而且,小哲平一郎和杜云飞突然赶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这间屋子里,那就说明,这间屋子的主人很有问题。
我正胡乱思索着,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身后的门被突然拉开,一股巨大的力量便将我整个人向天花板弹起来。我触不及防的被弹起,下意识的低头看了一眼,正对上小姑姑那双讳莫如深的眸子。
她,看得见我。
我知道,她看得见的。
“小。啊!”一股巨大的拉力拖着我,将我朝天花板使劲儿拉去。
……
“醒了?”
我愣愣的睁开眼,“殷泣?”不懂为何鼻尖发酸,但大概是九死一生助长了心底的那一丝惊恐和骇然,所以已经顾不得矜持和礼数,只是用尽所有的力气去抱住面前的人,脑中不止一遍的会放着在海水冲破玻璃窗的一瞬间,他扑到我身上的画面。
海水很红,我不太敢想象他是不是受了伤,伤得重不重。
在梦境中,尽管我还能淡定的去思考,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甚至怕我自己永远也出不来了。
“殷泣,我没死对不对?”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从他怀里退开,“我没死对不对?”
他叹了口气儿,伸手拍了拍我的头,“死不了。不是说了,祸害遗千年么?”
他这安慰人的手段真的很不讨巧,可又有什么比他能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哪怕是损我几句更好的事儿呢?
我破涕而笑,吸了吸鼻子,这才有时间看看自己到底身处何处?“这是哪儿?”
殷泣一脸嫌弃的拍了拍被我荼毒的衬衫,冷笑道,“旅馆。”
“饭店?”我这才注意到,不止他身上的衣服换成了一套黑西裤和白衬衫,连我身上的旗袍也换成了裤装。“你?我?”
“你觉得呢?”
“我,我觉得什么?”我会退一步,后背抵在冰冷的墙壁上,脸上一阵阵火烧火燎的感觉。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会真有什么吧?
殷泣抿了抿唇,转身朝门外走。
“唉!”我连忙叫住他,“真的没什么么?”我脸红脖子粗的问,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快要烧起来了一样。
殷泣突然转过身,伏底身子看着我,“还是你希望有什么?”
我囧得满面通红,指着他的鼻子半天说不出来话。
从旅馆出来后,我才知道,我这一睡,其实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医院,他说现在所有人大概都以为我们死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离皇姑区九号不远处的一个小巷里的差棚里喝茶,从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皇姑区九号的一切动静,包括三楼敞开的窗户,还有站在窗内正在大肆打砸的女人,我的小姑姑曹琪。
我恨不能就此找个地缝转进去,一旁的殷泣笑得很是得意,“她已经砸了三十四件东西。”他慢条斯理的说,微微弯起的眉头充满讥讽,对曹家的,对小姑姑的。
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为小姑姑祈祷,希望殷泣的索赔价格她能承受的住。当然,曹家人从来不差钱,但殷泣这个人,他未必就是钱能摆平的。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我心怀愧疚的看着小姑姑,但心里明白,现在是有人要杀金四喜,或则是我和殷泣。我们是同乘一部车子的,所以破坏车子的人的具体目标也许是金四喜,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和殷泣。
这个时候,如果我和殷泣诈死,那么,对于整个事件来说,我们就落到了暗处,更容易行事。
稍早之前,我已经将梦里发生的事儿都跟殷泣说了,他默了好一会儿,得出的结论很让人唏嘘——杜云飞和小哲平一郎同时出现在那间房间里,肯定是为了找什么东西。
“先去北洋剧院。”他抿了最后一口茶,放下杯子,抬手整了整头上的瓜皮帽,站起身往外走。
我连忙丢了两个铜板给老板,跳起来追了上去。
天已经渐渐阴沉下来,路上因昨日的大雨显得湿漉漉的,偶尔有几条刚从泥土里转出来的蚯蚓很穿马路。
越往前走,地上的蚯蚓越多,到了后来,竟然几乎到了无处下脚的地步。
我苦着脸看着地上的蚯蚓,嘴里嘟囔着,“这天儿也不知是怎么了?蚯蚓都出来了。”
他低头看了我一眼,“蚯蚓有移动,瞧样子又是在大东方,怕是有异动。”他敛着眉,脸色不太好看的看向大东方。
“能有什么异动,肯定是快要有大雨了,都出来搬家了。”小时后听家里的煮饭婆婆说过,乡下的时候,要是遇见蚯蚓大迁徙,估计是要发洪水了。
殷泣摇了摇头,从腰间抽出一把不大的小刀,弯下身挑起一根小孩手指粗细的大蚯蚓,放在面前上上下下打量一番。
“你到底在看什么?蚯蚓而已,全上海到处都是。”我有些嫌弃的离他远一点,没办法,我天生怕这些软体的东西。
殷泣扭头看了我一眼,我总觉得他把我看得很透彻,以至于我的所有反应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用匕首轻轻在那根粗大的蚯蚓身上点了一下,巨大的蚯蚓瞬时疯狂的扭动着,被匕首点了一下的地方伸出血红色的液体。
“血?”我愣愣的看着地上疯狂扭动的蚯蚓,胃里一阵翻滚,“这,我记得蚯蚓没有血啊!”蚯蚓的身体就是个大写的蛋白质,体内干重的一半以上都是蛋白质,并没有血液成份的,可这蚯蚓身体里竟然溜出红色的血液,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我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些成群结队的蚯蚓,细思极恐,浑身的汗毛都炸开了。
“它们可不是蚯蚓那么简单。”他淡淡的说。
“那是什么?”我踮起脚,给这些迁徙的家伙腾地方。
“血离。”他淡淡的说,踮起脚尖避开这些蠕动的爬虫往前走。
我已经从他口中听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了,实在是不能再过于的惊讶了,只是这种爬行的蠕虫实在是让我不喜且恨不能敬而远之,所以竟然觉得毛骨悚然。
他一边走,一边招呼两辆黄包车,上了车,夏日的风急急的从耳边刮过,仿佛只温柔得手,温润而安慰的抚摸。
他说,血离是一种奇特的蚯蚓,因为生存环境不同,通常有血离出现的地方,方圆三十里之内必有人祸。说白了,就是哪里有死人,哪里私人多,哪里就有血离。
蚯蚓的习性是生活在潮湿的土壤中,而血离则喜欢出入墓地,或是大规模的集尸地,靠吸食墓地里尸体分解的腐烂物质而生。
血离极为稀少,也很少出没,一般人很难分辨出血离和蚯蚓的区别,血离如此大规模的迁徙,一来说明皇姑区附近,或是地下有丰富的尸源,二来说明,在血离即将迁徙的地方亦会出现为数不少的尸体。
“大哥,你可听说,最近附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儿?比如死人,还是什么的?”我状似闲谈的跟拉车的车夫说了几句。
车夫是个健谈的,一开始还有些拘谨,后来大概是见我频频没话找话,便也乐于跟我闲聊几句。
“倒是听说那么一件。”车夫沉吟一声,好一会儿才说,“前段时间军队里不是说抓了一批马匪么?昨天在西郊的城隍面后面的林子里给枪决了。据说一口气儿崩了三四十号人,就地挖了个坑就给埋了。整个林子里到处都是血。”车夫说得绘声绘色,我侧头看了眼跟在我旁边的殷泣,他正微微闭着眼睛假眠,倒真像一个流里流气的大少爷。
因着要诈死,容貌上便不能不做改编,之前在黑街里搞了一些易容的行头,这一番改头换面下来,倒像是一对儿刚刚新婚不久的小两口儿。
车夫的脚力很快,过了不多一会儿便到了北洋剧院。
殷泣付了车前,往门口一站,单臂微微弯曲,我红着脸把手跨在他手臂上,顺着看戏的人群往里走。
前两天剧场才出了大事儿,虽然还没停业,但客人也不多,一连死了一个青衣和一个旦角,还能坚持继续捧场看戏的,那就是彻彻底底的票友了。
今天早场的客人不多,跑堂的愁眉苦脸的端着瓜子挨个桌填瓜子,连有些客人随手给了小钱都没能扯开他的嘴角。
今天唱的戏目是铡美案和长坂坡,都是男角戏份重的。戏还没开场,班主蔡政就在在大厅右面的角落里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人?
我和殷泣买了靠窗的票,位置偏远又不易察觉,很适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
戏开场了,台上的演员唱得很卖力,但显然是不在状态,总有那么一两个要害的地方唱得不好,底下的看客已经略有布满,更有甚者,竟然伸手抓起桌面上的瓜子,用力往戏台子上扔,一时间场面有些混乱,几个跑堂的连忙过来安抚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