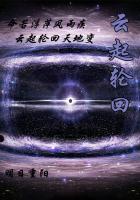眼面前的沈云卿朝服未脱,只见一身大红罗圆领袍,长至脚,内穿罗裙,腰束黑带。看着陌生,可面如冠玉,剑眉星目,一如记忆中那个温雅到让人如沐春风的少年。
两人眼对眼的,江书棋当下不由自主向着沈云卿挪了挪,江母不明所以倒也没有阻止。紧接着江书棋再看向沈云卿,稍稍犹豫着,这时沈云卿应是看出了江书棋的顾虑,当即要身后的一列官差退出十步远。见此,江书棋这才大了胆子,朝着沈云卿走去。
等江书棋走到沈云卿的面前,当即被沈云卿带到了身边,两人靠得极近,先是彼此相顾无语,随即才开始小声交谈。可这两人,分明都是压抑了内心底快要喷薄而出的相思之苦,江母看在眼里,不忍上前打断,就挂着一脸的疑惑,看着面前的两人。她先是见沈云卿轻轻地问了句什么,江书棋顿时使劲摇着头,面色惶恐得差点就要哭出来。再来沈云卿看似安抚了几句,却不知最后说了句什么,江书棋当即身形一顿,眸光深深地看着沈云卿,缓缓地点了头。
江书棋虽是点了头,但又回到了之前那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江母还是不明所以,顿时在一旁着急得很。这时就见沈云卿伸出双手捧上江书棋的脸,他微微弯着腰,拿过自己宽大的衣袖直接给江书棋抹眼泪。随即,沈云卿转身跟江母道了别,就要带着江书棋回去的意思。
“云卿,来都来了,不如留下来一起吃个饭?”江母见小两口瞧着是和好如初了,自然乐呵着招待起沈云卿来。
可沈云卿的样子,似乎后头还有要紧事,江母想着沈云卿刚回来应是哪边招呼都得打通,所以也就不再强求。两人走的时候,江书棋破天荒的矫情起来,死赖着沈云卿不撒手,好在沈云卿不予计较,转而以护犊的姿态反手拉过江书棋。
所以怎么说床头吵架床尾和?只怕小别胜新婚,瞧这小两口甜腻着呢!
江母这厢暗自庆幸着,好在之前没跑去沈府撒泼,像沈云卿这么好的女婿——颜帅,人好,又是状元之才,只怕在这整个苏州城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可她不知道的是,沈云卿这次过来,不是把江书棋接回沈府去,而是直接带进了大牢。沈云卿的性格如此,这样的男人永远都是为别人而活,却唯独对最亲密的人严厉。但他的温润如玉,他的超凡孤高,他的牺牲奉献却又让人忍不住沉沦。你与他最是心灵契合,能够彼此理解,志同道合,同仇敌忾,相知相惜,那么在一起仍会很开心。其实细算起来,沈云卿做得也没错,眼下不管江书棋有没有把人推下山崖,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指向她,可若是心下越怕越是逃避,这些无端的罪名,只怕就要陪着江书棋过一辈子。最后就算江书棋明明什么都没错,也会被压得不敢再吱声。
事不宜迟,沈云卿先拐了一趟衙门,之后就带上了几个换上便装的官差一起去了胜山寺。当然,他不是来还愿,而是直接来到了后山,也就是白绾绾坠崖的观海亭。不过要想还江书棋一个清白,这一趟显然并不容易——因为白绾绾出事当晚就下过一场大雨,虽然第二天一早出晴,犹如昨夜的雨声只是一场梦境,但一切痕迹都已冲洗彻底。说起来也怨不了谁人,当时沈母顾忌着江书棋,是以没能第一时间报案,眼下第一现场里根本找不到一丝线索。
叫大家四下仔细搜查,而沈云卿站在观海亭旁边的空地上,负手而立,眺望着山下的梯田海潮,不禁眯着眼暗自思忖道:“如果说陷害小棋,谁能直接得到第一利益。”
正此时,一个便装打扮的男子,看着身形娇小,胆色倒是大得很。他一听沈云卿这么问,当即眼眸一转,凑到了沈云卿的身边。
“一定是弟妹!”开口便知是江书棋,她见沈云卿转过脸看向她,这厢也很是有自己的说法,解释道,“因为我和苏苏怀疑她是假孕,她一定是怕我们揭穿她,这才先发制人。”
沈云卿看着一脸不服气模样的江书棋,也不将诧异,看来江书棋明显是在他安排下一起跟过来的。倒是没看出来,如沈云卿这般一板一眼的人,竟也会有坏了自己规矩的时候。
闻言,沈云卿有片刻的晃神,随即追问道:“可有证据?”
江书棋摇了摇头,锁了眉头,无奈道:“本来是有个钱大夫可以证明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他。”
沈云卿低下眼帘,见江书棋面色不痛快,暗自眸光一深,忍不住伸过手揉了揉江书棋的头顶,赞同道:“的确可疑。”
再而,两人竟都生出几分拘谨来,却又不禁彼此惦记。而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五大三粗的官差奔了过来,在他的手上却拿着一个别致的珠簪。
一奔到沈云卿面前,这人当即把珠簪捧到了沈云卿的面前,虎头虎脑的完全无视了江书棋,对着沈云卿献宝道:“爷,我在草丛中发现了这个。”
不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珠簪,这胜山寺来往的女香客不可谓不多,眼下看着是被雨水打淋后,在此刻的阳光下显得更为明亮。除此之外,又哪里有什么可疑之处?
“看着好面熟……”倒是一旁的江书棋在看到珠簪后,几步凑在眼面前,偏偏就是反复念叨着,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突然江书棋眼前一亮,急急道,“这是知夏的。”
“可是知夏的?”沈云卿见江书棋皱紧了眉头,一副快要想破脑子的模样,这厢不由得看着她问道。
谁知两人同步,闻言,沈云卿不禁眼眸一深,江书棋反而身形一愣,她抬起头来,讷讷地问道:“相公你怎么知道?”
“二娘跟我说的。”沈云卿解释道,随即望着眼面前的珠簪,心思活络起来,他说道,“这样看来,知夏失踪的时间,跟弟妹出事的时间十分接近。眼下知夏的珠簪又出现在这里,我们走,去发现这支珠簪的地方看看。”
说完,这五大三粗的便服官差当即反应过来,带着沈云卿和江书棋往一处走去。
发现珠簪的地方就在这附近的一片矮草丛中,那是块四周由矮灌木围成圈的草地,距离观海亭并不远。一到这处,三人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突然江书棋有了新发现,她本是四下查看着,此刻转身忙叫唤起沈云卿:“相公快来,我发现这里有两个泥脚印。”
江书棋是在草地外面发现了这两个脚印,看得出来应是在下雨后有人来过这里,之后天气出晴,才叫这些脚印干成了土块。不过这个地方并不显眼,可能也正是因为不显眼,此时此刻才会有这两个脚印留下来。
见沈云卿过来,江书棋伸手指了指这些泥脚印,随即捧着脑袋假设起来:“应该是有人在这个地方带走了知夏,从这个角度看向观海亭,我觉得知夏很有可能目睹了当时的一切。只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带走了知夏的人,又会是谁呢?每天在寺里进进出出这么多的人,我们又要从何找起?”
沈云卿一时也回答不了,当下先蹲下身,他看着地上这一左一右的脚印,不禁皱起眉头思忖起来。
江书棋低眸见沈云卿这般模样,这厢便蹲在了沈云卿的身边,这个时候沈云卿伸出手指着泥脚印,对江书棋说道:“你看这两个脚印左边深右边浅,深浅十分明显,有可能此人右脚并不利索,我们去问下寺庙中的小师傅,看看这几天有没有类似右腿不方便的香客上过山,相信一切很快就会有个答案。”
这两个脚印看着是在寻常走路的时候留下的,是以一般来说,一左一右不该有这么明显的深浅。沈云卿这般判断虽说不能百分百的确定,但相信八九不离十,他当即起身找来一个寺中的小和尚问了些问题。小和尚的回答是——出了沈府表小姐莫名坠崖的事情后,这几日寺中往来的香客少了很多,至于施主问的右脚不方便的香客实是不曾注意到。不过,在我寺中负责上下山担柴木的张老辉,倒是跟施主说得甚是符合。
这张老辉年尚二十七八,可惜是个丑无盐,父母全亡加上一个破茅草屋,根本没有姑娘愿意嫁他。偏偏几年前又摔伤了右腿,是以一些劳力活不再愿意招他,方丈大慈大悲才每月定期收他一些柴木,付他一些银钱聊以度日。出了白绾绾这事后,当日下午这张老辉就上过一次山,他如往常一样将柴木给了小师傅,就从观海亭旁边的那条道下山去了。
听这小和尚说完,沈云卿和江书棋两人下意识互相望了望,眼下看来张老辉的嫌疑最大,不过这张老辉估计与白绾绾坠崖的事情扯不到一块,他可能就是捡了个媳妇回家去了。呸!他居然敢捡个女人藏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