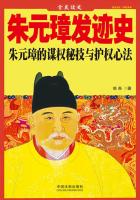“你不必自责。”
“妾身鲁莽了。”荣宓俯身行礼,心中虽有些疑惑这位,既然对方不愿意吐露真实身份,她也不便过多问话,又说,“请恕妾身还有事在身,先行告退了。”说完便带着锦云匆匆地从他们身边而过。
待她们走远,高缙远远地望着她们主仆二人的背影不解地看向自己的主子,“爷,您怎么不向这位主子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他宫里的主子见着您,都变着法儿赶着往您身上凑,今儿可倒好,唯独这位主子例外,奴才倒是头一次见着这样的怪人。”
朱允洛看见她匆忙离去的背影,倏地勾唇一笑,“去查一查她是哪个宫的,朕瞧着似乎有些眼熟。”
高缙忙不迭一的作揖道,“奴才遵旨。”
“去传毓秀宫传朕的旨意,就说朕朝务繁忙走不开,让容贵嫔不必等朕用晚膳了,再去内务府挑些水头好的珠翠送去她宫中,让她好好养胎,朕改日再去看她。”
“是!”高缙领了命便朝着东二长街的方向走去。
气喘吁吁回到长乐宫的荣宓立即招来苏晟苏公公,一番附耳密语,苏晟连连点头,旋即一路小跑的出了长乐宫。
用过晚膳后,已经是掌灯时分。
苏晟来报说今日怡亲王的确进宫给太后请过安,荣宓这才放下心来由锦云在寝殿内服侍着重新梳妆。
此时,亮若白昼的慈宁宫却流淌着一股浓浓的母子情。
佛堂里弥漫着淡淡好闻的檀香,明黄色的蒲团上,萧太后闭目正虔诚的跪着,戴着金色镂空护甲的手中不停的转着一串碧绿的佛珠,嘴里默念着经文。
身后有人走近,轻声细语道,“太后,皇上来了!”是侍候了她半生的芸若。
萧太后点头,缓缓地睁开眼,目光锐利,令人不可小觑,良久她握着佛珠的手一顿,轻笑,“还不快让他进来,外面天寒地冻的。”
朱亦渲走进来的时候,面色不太好看,“儿臣见过母后!”他很清楚这个时候,太后找他是为了何事,心中不免有些阴郁和烦闷。
“免礼吧,皇帝这么久不来看哀家,是因为心里还在置气么?”萧太后继续捻着手里的佛珠,面色平静,淡淡的说道。
“儿臣岂敢?”朱亦渲微眯了眯双眼,漆黑深邃的眸中闪过一丝不可捉摸的精光,他也懒得再废话,于是直奔主题,语气不善的说道,“怡亲王,是您召回来的吧?”
此前,他明明下过圣旨,怡亲王朱逸尘非帝王之召不得擅自回京,母后竟会直接下懿旨昭他回京,这,犯了他的大忌。
萧太后默然片刻,眉心微低,略带愁容道,“明太妃身子快不行了,哀家召逸尘回来只是为了让他尽尽孝心,毕竟哀家与明太妃也曾是一起长大的。”眼中流露出的忧伤一闪而过,不易捉摸。
自先帝在世时,萧太后还是萧皇后,与明妃是要好的姐妹,在后宫一路扶持,相伴二十载,其中的姐妹情分不是三言两句就能说得尽道的明的。
她只是希望,在明太妃生命的最后一程,让她自己的儿子能在身边侍奉着,尽管亦渲心中一直忌讳着逸尘,她还是擅自下了懿旨,将远在邕州封地的逸尘召了回来。亦渲来之前,逸尘特地前来慈宁宫问安,这令她老怀安慰不已。
朱亦渲看着神情微怔的太后,不自觉的叹了口气,幼年他也没少受到过明太妃的恩惠和照顾,于是他稍稍缓和了语气,朝太后微微一鞠,浅笑道,“恕儿臣多心了。”
萧太后微微一笑,扶着芸若的手缓缓站起身来,每日跪一个时辰,念诵经文,已然成了她不可必少的习惯。
朱亦渲跟着太后的脚步一前一后出了佛堂,来到敞亮恢宏的后殿,萧太后坐在檀木椅上,接过宫女递来的热茶,轻轻吹着茶碗中的绿沫儿,不动声色的问着,“皇帝,秀女已经册封多日,为何你不见你召人侍寝?”
淡淡的语气里包涵着一丝责问和不悦,选秀乃至封妃皆是由她亲手操办,亦渲不召新入宫的妃嫔侍寝,这岂不是在打她的脸?
问起这事儿,朱亦渲脸色微变,忙避开眼,双眸不自然的瞥向别处,漫不经心的说道,“儿臣朝政繁忙,无暇顾及后宫。”
萧太后凤眼微挑,青葱玉指轻扣瓷杯,缓缓摇动手中的茶水,心知肚明亦渲的借口和托辞,她却不挑破。敬事房的册子,萧太后早已翻阅,一个月,苏绿萼就侍寝了六次,而身为后宫之主的皇后却只有仅仅两次,这不免令她有些不悦。
不管怎么说,皇后沈丝吟也是自己亲妹妹的女儿,她的亲侄女,怎可被一国之君冷落?传出去岂不贻笑大方,亦渲厚此薄彼,令她气恼不已。
“皇帝,你不论多忙都得顾及点身为皇后的脸面,暂且不说她为你辛苦诞下一双儿女,连整个后宫的担子都压在她一人的肩上,于情于理,你都该多陪陪她。”萧太后轻轻望了一言不发的亦渲,拍了拍他的手背,口气软了下来。
在后宫待了二十几年的萧太后,是最清楚对一个女人而言最需要的是什么,没有宠爱的嫔妃只能在这寂寞的深宫墙垣,独坐对着红烛泣泪,直到天明。
朱亦渲被这一席话说到动容,只见他微微侧目,勾唇一笑,“儿臣谨遵母后教诲。”沈丝吟,记忆中的丝吟,温婉贤淑,虽然不似芙蓉那般艳丽,却有着兰花的圣洁,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父皇就极为看重沈丝吟身上那抹不凡的气度,便指给他做了太子妃。
萧太后含笑看着陷入沉思之中的亦渲,心中终于松了口气。
朱亦渲陪着又坐了片刻,便宣称有事早早的离开了慈宁宫,临走前,萧太后很清楚的听见亦渲对高缙吩咐着,“去长春宫。”
那样的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像极了当初她的大儿子明轩,被十年前一场无情的瘟疫夺去了生命,至今她仍处在悲痛之中,亦渲越来越像明轩了。
一阵阴风从未关好的朱窗猛地灌了进来,芸若见太后有些瑟瑟发抖,她心中哀叹一声,不由走向窗棂关上了窗户,毕竟是和相处了几十载的人,太后的一个细微的眼神,芸若都了然于心。
十年前,太后失去大皇子那一天,芸若还记忆犹新。
长春宫。
此时,月心趁着夜色端着一碗漆黑浓稠的汤药,小心翼翼的推门走了进来,只见她垂首恭敬道,“娘娘,药熬好了,快趁热喝吧。”这副太医院开的药汤,月心足足熬了四五个时辰。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味,沈丝吟漠然接过,捏着鼻子一饮而下,舌苔溢满了苦涩的滋味,像极了她此刻的心。
她不禁摸上平坦的小腹,低垂着眼睑令人窥探不了她此刻的内心,喃喃自语着,“月心,这副汤药真能令本宫再怀孕么?”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和惆怅。
月心上前一步,笑吟吟的说道,“这副汤药是太医院的原判乌靖元太医研制的,娘娘大可放心。”娘娘求子心切,她作为心腹应该无时无刻为了主子的利益筹谋着。
沈丝吟微微松了口气,拿起剪刀挑着烛芯,火光瞬时明亮了起来。
这时,寝殿外传来一道高喝之声,“皇上驾到--”往日觉得刺耳尖细的嗓音现在听来却犹如踩在了云端,有些飘飘然。
沈丝吟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同样满怀欣喜的月心,唇畔泛起一丝久违的笑容,这一刻,她等了太久,太久。
沈丝吟对着铜镜随意的梳了梳发,确定妆容无误,披上一件织锦皮毛斗篷打开门匆匆走了出去,朝向迎着琉璃宫灯蹁跹走来的明黄袍男子,福身行礼,“臣妾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
朱亦渲伸手微抬,淡淡勾唇,“皇后不必多礼。”瞧了一眼站在廊下一袭素衣,披着长发的沈丝吟,他微微一怔,见惯了平日里端庄的皇后,今日未施脂粉却耳目一新的她让人心口猛地一震。
“夜里风大,皇后还是随朕进去吧。”说完,朱亦渲便执起沈丝吟的玉手,牵着她含笑踏进了寝殿。
看着恩爱的帝后,月心朝皇后朝扬了扬唇角,心里是乐开了花,这样的场面,她倒愿意天天瞧见,哪怕隔三差五也好,外面不知谁乱嚼舌根,暗中诋毁皇后,不论宫中流言蜚语再猛烈,今夜一过,一切无中生有都会烟消云散。
天底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也没有无孔不入的眼线。
只须一炷香的功夫,皇上驾临长春宫的消息不胫而走。这让一直隐隐企盼着皇上到来的云贵妃苏绿萼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
她亲手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只为等待皇上的到来,与她一同庆贺生辰。是的,今日是她的寿辰,满心欢喜的盼望却换来满腔的悲凉,这便是身为后宫女人的悲哀,没有人可以独享皇上心尖宠。
就连宠惯六宫的苏绿萼也摸不透猜不着皇上的心思,皇后受冷落多时,六宫众人谁人看不出,只是苏绿萼却怎么想也想不透,皇上何故好端端的跑去长春宫……
她抬眼瞧了这一桌凉透的菜色,朝蕊心挥了挥手,她真的心很累很累了,所以她懒得再发脾气,走向床榻,和衣翻身躺下,头有些发痛,闭着眼心中默叹,不知此刻的毓秀宫又会是何种情形呢?
处在盛怒中的容贵嫔容斓月却拿着殿内上乘御用的瓷器较劲,谁人不知,毓秀宫的每一件物什儿都是顶好的。
宫女兰心站在一旁怎么苦口婆心的劝也都听进去,干瞪眼的看着暴躁的容贵嫔发脾气,站了满屋的宫女皆垂首,战战兢兢的立在两侧,唯恐会牵连到自己。
眼见着还剩下最后一件极为昂贵的冻青釉双耳瓶,兰心赶忙上前抱住,死死不松手,“娘娘,这是皇上御赐之物,砸碎了,皇上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兰心悄悄看了一眼微怔的容贵嫔,继而言辞恳切的说道,“娘娘,您这样对腹中的胎儿不利,孕期切记不可动怒啊!”兰心时刻记着胡太医的嘱咐,从未敢遗忘。
听兰心这样说,容贵嫔这才松了手,摩挲着隆起的腹部,冷笑连连,“沈丝吟究竟是用了什么狐媚手段,令皇上对她旧情复燃!她感到有些心慌意乱和难以言喻的挫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