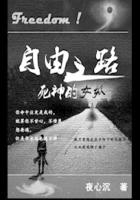起来去,还是她当时太过草率了,这后宫心机谋略,她自知并不擅长,可是在宫中打熬了这么多年,她多少也略通一些,无论如何,她必须要守住现今的地位。
“娘娘,那位郭才人,奴婢私以为定要防着她些才好。”云若剥完了最后一颗荔枝,一字一顿了下着结论。
“嗯,本宫知晓了!”锦瑶吐出栗色发亮的果核后,抬手揉了揉略微酸胀的太阳穴,随即挥手命云若将果盘撤下。她心里明白,如今唯一能牵住皇帝心的,唯有她所出的大皇子了。
别院内,夜风轻拂,携着院花草馨香随窗而入,顷刻间吹散了一室暑热。碧游近日来偏好折腾,早先将窗边的凉榻撤了换成了躺椅,前不久又将凉榻换了回来,现如今又把躺椅给挪了回来。好在跟前伺候的那群人倒没有丝毫怨言,由着她性子折腾了三两次,随着她身子一天天地发重,伺候得越发的殷勤周到了。
玲儿觉着碧游的身子越发不便,便提议在要内室外头支架屏风,晚上好歇在殿中方便照顾。谁知碧游偏不领情,还嫌她啰嗦得像个老太婆。无奈碧游是主,她是仆,除了听命,别无其它选择。
夜色越发的深沉,碧游遣退了殿中伺候的下人,独自坐于窗边的躺椅上把玩着手中的碧青竹哨。离上次应仕出现,现已十日有余,算起来离颖王离京的日子也没两天了。那日应仕所言,让她预感到风雨欲来之势,若是楚宣得知如今的颖王韩时便是上官简,想来定不会让他活在这世间。不过,若让他一直这么下去,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她不愿楚宣受到任何威胁,也不愿上官简有什么三长两短,因此她信中恳求他给上官简最后一次机会,无论如何,要也给他一条活路。
其实,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太过天真,父王当年曾说过,帝王政权容不得半点侵犯。那些挤破了脑袋踏入仕途之人,皆懂得放与收,若非如此,如何才能在官场上打拼?虽说军中不及官场那般尔虞我诈,却也是暗潮汹涌之地。如今上官简百般挑战楚宣的耐性,他能忍的,也都忍了,照理说,若是治他死罪,也是他罪有应得。只是他是父王上官清唯一的子嗣,她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若是就此将他弃之不顾,他日到了地下,她如何面对从小对她百般疼爱的父王?因此,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她也要为之努力!
百般纠结了许久,她终于将竹哨凑向唇边,刚呼气要吹响,却听窗边有人声外入:“娘娘此时吹响竹哨,就不怕院内众人生疑?”
碧游听见那再熟悉不过的低哑男音,不由欣喜地撑起身去瞧,见应仕果然站在窗下,长身玉立,颇有风姿。
“你且进来,我有话要问你!”想起上次他的态度,碧游不由沉着脸低声吩咐道。
面具下的应仕闻言,不由挑了挑唇。他早就深刻地体会到面具的各种好处,不会让别人察觉自己的情感变动,更不会让不能直接面对的认出,他恰到好处地运用着面具将自己包裹严实,好与她保持适当的距离。说来说去,他只是不知该如何面对她。
碧游见他纹丝不动地立于窗边,不由微微蹙眉,继而朝他瞪大了双眸显示她的怒意。
应仕见之无奈,只得抬手往窗抬一撑,下一瞬稳稳地立于房内。
“不知娘娘有何事要吩咐?”他朝她抱拳一揖,恭敬地问道。
碧游见他如此,也不与他兜圈子,她紧紧地捏着手中竹哨,抬眸看着他,郑重说道:“我想请你救个人,想来依你的身手与手段,定是不难吧?”
应仕似乎早已料到她的心思,因此他并不惊讶,不过他却不认同她的想法,所以极谦逊地答道:“娘娘实在是高估微臣的能力了。”
“高估?你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所写的信函交由皇上,想来定是有些手段的。现下我只问你,这任务,你到底是接还是不接?”碧游不能完全摸透他的心思,却也知他心里头想些什么。她也知她的吩咐太过强人所难,可是如今除了他,还有谁能够救得了上官简?
“不知娘娘要救何人?”应仕并未接她的话茬,而是直接开口发问。
“我所要救的人便是颖王韩时,听闻他两日后便要离京前往封地,届时他若遭遇不测,还要你出手相救。”
碧游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有些事情,他虽然不说,但她还是知晓的。他从往日的沉默寡言到如今高深莫测,可不管怎样,她始终还是信任他的,这信任来自于她的直觉。尽管相处时日并不太长,可他就是值得她信任也依赖。
“颖王爷只是前去封地,途中亦是有大批护卫相随,娘娘为何会认为他会遭遇不则?再者,娘娘与颖王爷并无瓜葛,为何要如此挂心于他?若真是如此,只怕是于礼不符吧?”
面具下的应仕眉头紧蹙,忍不住反问道。他也知她担忧的理由,只是她若一直这般,却从未顾虑自己,到往日只怕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他因心急而口不择言,甚至连声音也忘记了伪装。
碧游因他这番质问而愣了半晌,也未曾注意到他的声音变化。她只是一味的担心上官简,也未曾顾及其他。她默然沉思片刻,说道:“你只管照我吩咐做便好,至于符不符礼数,并非是你过问之事。”
“微臣只是遵照约定护娘娘周全,至于保护其他人,并不在微臣的职责之内。”应仕换回了沙哑的声音,却仍止不住内心的焦急。况且根据他近日来的调查,上简官的身份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算如此,那么皇命你总该听的吧?”碧游虽知是强人所难,可她却不甘心,随手扯下挂于腰间的九龙玉佩扔到了他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