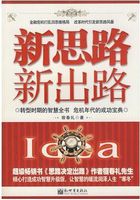玲儿哄了皇子入睡后,将他抱到了房内摇篮,随即走到正坐在窗边翻看厚厚医书的碧游跟前。
因玲儿刻意加重了脚步声,听见动静的碧游侧过头瞧了她一眼,张口问道:“可是有事要说?”
玲儿讪讪笑了,见她翻看的并不是医书,而上放于医书上的一张写满潦草字迹的纸。她本欲凑上前瞧,却未料碧游竟捏起宣纸一角递到了她面前,说道:“你且瞧瞧,这上面所写的事情始末,可是有什么关联?”
玲儿虽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乖乖接过看了看。上面所记之事皆是她这位主子回宫后所发生之事,但见这纸上由上而下按着时间之序记了下来,且还将有些事情以圈叉做了记号,并在空白处作了简要的分析。
玲儿捧着这张字迹潦草看了半晌,又瞟了一眼最下端的结论,顿时面色微变。但见她抿了抿唇,佯装不解地说道:“娘娘可是对皇贵妃一案有什么眉目了?”
碧游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敲打着黄花梨木制成的书案,微眯的双眸穿过雨过天晴色的纱窗望向虚空。末了,她轻叹一声,这才将目光由外移向玲儿秀气的面庞:“有些事情,兴许你比我还了解,不是吗?”
玲儿被她灼灼的目光盯得心慌意乱,她大胆地看入碧游的幽深的双眸,极力抑制心内翻涌而上的情愫,答道:“请恕奴婢愚钝,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碧游见她不肯实话实说,却也不恼,反倒是温言细语地说道:“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有些事你心知肚明,只是瞒着我而已!”
她虽是柔声细语,可听在玲儿耳中,却带着别样的冷意。她轻咬着下唇,扑通往地下一跪,诚惶诚恐地说道:“奴婢断不敢欺瞒娘娘!”
“哦,是吗?我只觉得如今的你与往常有些不同。算起来,应是打皇子出生之后,你便越发的谨慎了。自回到这碧棠殿后,这院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皆交由你去打理,一应繁杂事务皆处理得极为妥贴。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应是有人暗中指点吧?!”
碧游听她矢口否认,仍是不急不缓地说道:“不管你承不承认,现今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要见那个人!”
“娘娘,你真的冤枉奴婢了,这宫内事务并不繁杂,虽说奴婢愚钝,但处理这些琐碎之事还算是驾轻就熟。若说真是有人指点,也不过是往日教导奴婢的嬷嬷从旁相助。奴婢偶有不懂的地方,皆是向她请教。”
因韩时以她性命威胁,玲儿只能硬着头皮撒谎。她也是个知轻重的人,就算是眼前主子怪罪,她也绝不能松口。毕竟颖王亡故已成事实,若是她贸然说出他仍存活于世,只怕要引发一场大乱了。
“哼,无论你是实言相告,还是巧舌如簧,本宫给你三日时间,若是三日内那人不曾现身,休怪本宫无情!”
碧游言罢,狠狠地剜了玲儿一眼。她心知这玲儿向来忠心,也知她欺瞒于她不过是身不由己,可若不如此,那么真正的韩时断不肯现身相见。其实她早该料到,他消失许久不曾相见,并非是心倦离开。打从德妃赵青鸾与柳洵出现,他便悄然设下了精妙一局,这一局,不为别人,只为她一人而设!
碧游自以为韩时会先沉不住气,孰料过了两日,他仍是不曾现身。正当她思量要以何种方式逼韩时现身时,宫里头却掀起了另一阵风波。
话说事情还是两日前,京兆尹拿下了个在京城街头行骗的游医,说是可以将貌丑之人变得美丽。这世道自是有不惜金钱而求貌美之人,据说某位员外家的小姐慕名将他请至府中为其医治塌鼻斜眼之症,孰料他施针治疗时一时失误,差点儿要了那位小姐的性命,于是这官司便打到了官府。
再后来,又听闻他攀扯与宫内的一位贵人有什么渊源,这事便传到了刑部侍郎杨哲的耳中。他最近被这后宫的案子弄得焦头烂额,但凡一点线索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好在是上天怜见,竟真让他查出了些眉目来。他亲自提了犯人关于刑部大牢,又命较牢靠的人员看守着,随即便进宫面圣。
楚宣万万没有想到,被刑部侍郎杨哲视为救命稻草的线索却成了重新将他打入愧疚深渊的巨石。当他看完杨哲呈上的供词时,只觉心头寒意蔓延。这不过是深秋时节,却让他如坠寒潭。他以为郭玉兰是上天对他的救赎,而今看来,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的笑话。
为免再出现像锦瑶那般的冤假错案,楚宣并未有所动作,而是连夜亲自提审那名游医。由此不仅揭穿了郭玉兰的真实身份,更是牵扯出了孝贤夫人。当年吴昭容亡故,不过是另一场阴谋的开始。说到底,是他的不对,是他被别人抓住了弱点,才会有机会加以利用。思及现今如同废人的孝贤夫人,楚宣心头难免涌上无限感慨,他怎能料到像她那般的人,在事情败露之前便有了后招,她的心机,确实大大地出乎了他的意料!
无心理会这些后宫杂事的碧游等到了第三日,终于是按捺不住,一早安顿好皇子之后,便叫了玲儿前来盘问。谁知还没问上几句,便听殿外传来声声通报,声音未落,便见一身朝服的楚宣挑帘入了房内。
碧游见是他来,瞥了旁身的玲儿一眼,却未上前迎驾,只是端坐着冷冷瞧着楚宣走近。
楚宣见她这般冷淡模样,倒是不曾见怪,反而是对她心生愧疚。他知她心思灵透,想必已是猜到他那晚留宿碧棠殿的缘由。
他走到碧游坐着的暖榻边,朝玲儿使了个眼色,见她识趣地退下后,这才执了碧游的手,温言轻语说道:“近来宫里头发生的事情,想必你已是知晓了。”
碧游闻言,暗想是宫内新近传得沸沸扬扬的游医能改人容貌之事。她虽不知其中内情,但多少也能猜出些来。在这节骨眼上,能有这手笔的,想来便是她千方百计要见的人。
“臣妾近来忙于照顾奕儿,并不知宫内发生何事。”她递给他一抹虚假的笑,漫不经心地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