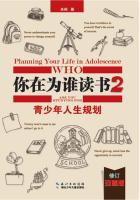在一条没有路灯又杂草丛生崎岖不平的小径上,我被脚底的一块石头绊倒,单肩背着的旅行包也摔在地面,荡起一层飞扬的尘土。我几乎是整个身体都重重地摔在地上,地面上的一些碎石生硬地刺进膝盖和手掌的皮肉,疼痛火辣辣地蔓延全身。
我趴在地上起也起不来,连挣扎一下都不能。身体和心上的疼痛拧成一股,轻而易举离间了我最后所持的一丝力量。眼泪是为这最后无处可逃的绝望所酝酿,一滴一滴打在地上,入土为安。
就在我哭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叶青蕊气喘吁吁地赶过来,脸上有细密的汗珠,她慢慢蹲下,声音有些虚弱地向我道歉,“染茉,对不起,可真得不是你想的那样,江远——”
“你住口!”我撕破嗓子吼着不要她再讲下去,尤其提到江远岸,我情绪异常波动起伏。
青蕊没再说下去,想把我扶起来,我却顺手一推把她颤巍巍的力量打了回去,她顺势倒坐在地上。我咬着牙忍痛起来,然后一瘸一拐继续向前走去。
摔倒时脚被崴了一下,我不得不艰难又速度极慢地挪动步伐,这样的速度足以让青蕊跟我相跟着。她还是想用手搀扶我,或者想帮我背起身上的旅行包,但还是被我毫不留情地甩开。虽然哭了一场,但我不认为自己的心态会随着哭出来的愤怒而稳定许多,可情绪上的障碍有所减轻,起码轻到可以用语言去表达。
青蕊连续不断地向我解释,每每在她还没说到三个字就被我吼着坚决制止。我活脱像个被激怒的恐怖分子,容不得她半点轻举妄动。她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着什么,我就不厌其烦地打断她——用一种玩弄式的,带有折磨意味的。这是此刻我唯一能做的让自己感到有些痛快的事情。到后来,青蕊也索性不再说话。
心里的伤痛张牙舞爪成一只血淋淋的怪兽,再软弱地悲伤下去就全无尊严。我已经被嘲弄的够多了,每个人都假惺惺地带一张面具。但若这样看来,饶初梦还算磊落,至少,比这个从小一同长大的所谓情深似海的姐妹要坦白敞亮得多,她把所有的欺侮都放在明处;而叶青蕊,她在暗处一定笑得大快人心吧。
这件事最初缘于那只风铃,那么就从风铃开始问起。我声色凄厉:“那风铃是你亲手做的?”
“是。”青蕊一点都没避讳。
“也是你亲自送给江远岸的?”
“嗯。”语气中不含任何遮掩的成分。
这样的直接干脆让人既痛快又厌恶。
也就是说,她并不是在她生日那天才返回学校的,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为亲自送给江远岸一只风铃而赶来,然后一直潜伏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直到她生日的那个午夜,才装模作样地出现在我面前。这样一来,记忆被逐渐完全打开。我记得发现风铃的时候是个下着大雨的旁晚, 我颜子名的别墅出来折回远岸的出租屋,而当时他并没有在家,直至晚上才一身湿透的回来。现在想来,那时他已经背着我跟青蕊一起……难怪他当时说话支支吾吾神情飘忽,好一个“学妹”就敷衍而过。
难怪在江远岸拒绝叶青蕊外出旅行时她哭得那么义愤填膺,那么伤心委屈,原来是两人早有私情。那天所有的古怪在今日都得以解释——当我敲开江远岸的房门为何只有叶青蕊独自一人;为何在她见到我脸上却写着惊慌失措;为何江远岸回来后跟她有那样云里雾里的对话;为何在她想向我说明什么时候他匆忙转移话题。也许在那个时候她就想挑明,却被远岸某个强烈的暗示挡了回去。我始终记得他夹在我和叶青蕊的中间,背对我,面向她,他们所有默无声息的对视都被江远岸的后脑勺巧妙地遮挡。所谓提着啤酒最后出场的冯知恩也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和帮凶。他是早就知道内情的,却还死心眼地喜欢叶青蕊;难怪他向她大吼要她说出实情,而她哭他也跟着哭,现在看来那样纠结的场合也只能令苦情的他崩溃。
但只有我一个人不明就里,所以哭得伤心至极的叶青蕊跟我说的所有话都是弦外之音,而被蒙在鼓里的我丝毫听不出这言外之意,还心疼不已地帮她止泪。真是太悲哀了,原来饶初梦的嘲笑是真知灼见的。
我和叶青蕊之间的情谊竟是这样疲软而薄弱。是我们辜负了这二十年来的相亲相爱?还是这漫长的时光对我们幼稚的情感早已倦怠?风起云涌一把便瞬间垮塌,可说起来也不过是为了一个男子。
这怎能叫人不哀伤?我抽抽搭搭一瘸一拐继续往前走去,心中无限的怅然和凄凉——她是曾经给我欢笑慰藉的、任我相依为命的、给我山高水长的、让我肝胆相照的最好最爱情深意重的姐妹。
“一直以来,我都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因为我真得不想再对你隐瞒下去,但好几次,已经完全斟酌好的语气想好的话语一到嘴边就没了章法,觉得怎么说都会伤害到你……”叶青蕊小心地说着。
我冷笑一声,因为真的可笑,事已至此,还假装什么客气!我反问她:“怕伤害到我?所以你干脆就趁人之危趁火打劫?”
“我没有!你刚才看到的——”她是语重心长又耐心致志的。
“你住口吧!”我打断她,却是极其不屑的。但心里的痛已积劳成疾一般容不得敷衍。
我强忍着痛楚,举重若轻地讽刺着:“都已经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江远岸的祖上到底哪座坟头冒了青烟?竟让他有这样的桃花运!新欢旧爱还一团糟地没完没了呢,又一竿子打来个‘小学妹’!可是叶青蕊,哪儿有像你这么痴心的,人家都要当爸爸了,你还这么贱兮兮地投怀送抱!不过江远岸也太不是东西了,果真是来者不拒哈!”
连我都要惊讶于自己的这番阴损毒舌,自己都觉着寒心。就像一把没有柄的双刃剑,一头已经插在自己的心口,想要对彼方造成重伤,最快捷简便的方法就是不顾一切冲过去,让剑的另一头也刺在对方的心上,但这样一来会有一股更强大的力再作用给自身。因此谁最用力、最想把剑更深地刺入对方的身体,谁就流血最多也伤得最深。
所以这是明摆着的,这样的话伤人伤己,但此刻一旦看到敌人也中招,我反倒颇有种虱子多了不怕痒的无赖心理。因此,月色之下,叶青蕊被气得浑身发抖的样子让我心里好不顺畅痛快。
她颤抖的嘴唇已经说不出话来,慢慢地,她神情痛苦地蹲下身去。我也歇住脚步,看着她怎么还击,以一种无可救药的姿态等待着鱼死网破你死我活的相仇相杀的局面。
终于,她低着的头慢慢抬起,红红的眼睛里除了溢满的泪水还有深深的痛楚,她就用这样的目光狠狠投入我的眼中,她声音颤巍巍的:“颜染茉,你知不知道,那么多年来你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呵!”没想到她竟会这样说,我故作轻松,像是听一个笑话那样很无所谓地看着她:“愿闻其详!”
谁知她浮起一个轻蔑笑来,缓缓地,用一种规劝的态度说:“都是你自找的。”
这句话何其狠毒,我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她便又说:“你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尖酸冷漠又恶毒刻薄!”她一句句的,语气逐渐加重,可两行清泪却翻涌而出,在月光下晶莹剔透凄美动人,她边说边缓缓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没有放过我。
“好像全世界属你最可怜最忧愁,总是把自己扮成一副惨兮兮的样子就开始顾影自怜,人前又是一副冷傲漠然的神情,孤家寡人似的落落寡欢格格不入!正常点儿好好活着不会吗?演给谁看啊!不就是你爸妈离了次婚嘛!用得着从小到大成天到晚的悲天悯地吗?至于吗啊?人死了爸妈的都没你这么爱惆怅的!你不快乐根本就是你自作自受自寻烦恼,都是你自找你活该!迟早有一天你会为你的固执和狭隘而付出代价!后悔也来不及的代价!”青蕊最后吼了出来。
我声音颤抖到说不出话来,紧紧攥着拳头咬住牙关。
就这样被人举重若轻地戳到死穴,什么叫“不就是你爸妈离了次婚”?其实他们离不离婚都一样,反正从一开始就长年累月地见不着爹妈,早就家不是个家了,也许离了更好,各自为营互不相干。
从某种意义上讲叶青蕊说得对,是我太爱惆怅了,我早就应该完全不用在乎的。那么在乎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呢?根本就一切都回不去,我在这儿有什么可悼念可哀愁的?最后还被人说成是自影自怜自找苦吃。
是,我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