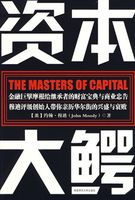是了,这便是她为曾经的胞妹所留的余地,一切命运都源于邹清音的选择,也应了道家之言:天道循环,善恶承负。善行者得富贵,为祸者自贫贱。老天爷那里有一本账,邹清音逃不了,新入杨府大门的小娘子逃不了,而她九丫亦然。
自回临安后,九丫一直在思索,当年自已对信阳所做的,是否也应是了循环之道。她自知有过,活该受到报应,可为何累及幼子。
负俗园花厅中,茗玉点了安神的香。她是一个多月前回临安的,一则是想看看大志,一则是带回余有年的书信。那是余有年的第一封信,而后又收到三封,但信中的内容大致相同:努力地找寻,模糊的线索与没有结果。“阿九,我亦觉得你如今该做的是离开临安,至少你不用对着一堆信函唉声叹气。你自已去寻,即便没有结果,也无愧于心,无愧于菜菜。而且还有一事只怕你尚不知道吧,昨日早朝皇兄下令修史,不料杨宇桓当面斥责皇兄失德,若非一众老臣劝着,只怕你便要去牢中见他了。”
那日柴胡前来府中时,九丫正心血来潮地摆出笔墨练字儿,闻得这话,手中的笔生生地捏断在指间。朝中的事,她自然不如柴胡清楚,而杨宇桓近来也不愿给她提及这些。默了许久,她才悠悠地回过神来,开口应声:“当日初回临安,我在宫中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不知皇上可有上心,是否着人查过杨攸?若不弄清,我不能安心。”
如今的九丫,再不是当年城前巷子那个无忧无虑的小丫头,即便那时她也不是个以德报怨之人,如今面对谋害幼子的杨攸,她又怎会放过。柴胡叹了口气,答道:“阿九,以皇兄的性子,你应当知道他定会让人追查的。不过若能让你安心,我愿意走这一趟。”
正如柴胡所言,九丫知晓乾宁的多疑。几月前她故意设下“有人意欲挑拨君臣关系以谋渔利”的陷阱时,便想到无论是真是假,乾宁都会因此而与杨攸生隙。她才是挑拨之人,谁教乾宁信任她多过满朝臣子呢,谁教乾宁整日想着男人会夺他的权而女人只会绣花呢。
三日后,果如九丫所料,柴胡暗地里打听到几月前便有大理寺官员前往驿站,而后抓了几个江湖浪人,据说关了一个月才放人。依柴胡之言,大理寺拷问罪犯向来有一套,只要进得那私牢,便没有不开口的人,更何况最后还放了。这些动作皆是私下进行,是皇帝口谕,能得到这些消息,他这魏王没少下功夫,还险些被怀疑图谋不轨。幸而他与乾宁关系有目共睹,否则也进了大理寺的私牢了。
“如今,你可以安心了吧。”柴胡道。
九丫没有应声,直到柴胡离开后茗玉进来添茶时,才唤回了她的神儿。
“小姐,您已经坐了半日了,可要去外面走走?这个时节,即使日头当空也不觉得热了。”茗玉见她发呆,止不住开了口。
九丫揉了揉太阳穴,有些疲惫地收拾如桌上的书信,跟着茗玉跺出了负俗园。
前院的木芙蓉今秋竟早早地开花了,没有香气,粉白色的花色并不显艳丽,但再过些时日便会由白转粉,直到凋落时花色已艳红。杨宇桓说杨家的先辈将此花种在前院,便是告诫子孙红极必败这道理。然而盛极必衰的自然之理,又皆是谁能左右的。杨家在经理了三代的繁华后,无论传至杨宇桓手中还是杨攸手中,大约都逃不过没落的命运吧。
在树下吹了会儿小风,九丫便觉得无聊,于是领着茗玉去别处看看,埋着头走了不多时,竟转到了一处园子外,仔细一瞧竟是当年琴姬所居之处。
“小姐,如今这园子是大公子新入门的小娘子住着。”茗玉的声音适时传来。
九丫微怔,喉咙中“嗯”了一声,便要转身离开,步子将将挪了几尺,却有人叫住了主仆两人。左右一瞧,着声的是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九丫见过她,几月前在那小娘子的住处。
“三夫人,我家姑娘谁你去亭里坐坐。”丫鬟指了指不远一处凉亭,亭中坐着的不正是杨府的新人。
比起不久前,眼下这小娘子穿着并无改变,只是那神色大方得体了许多,毕竟从前是金屋里藏着的娇,此时是进了门的姨,加之杨攸正房空虚,如今她算做了大。
小娘子颇懂礼节,福了福身唤了声“三夫人”后亲自给九丫倒了杯茶,“今日好巧,竟能遇上。昨日我还在想向去负俗园向三夫人道谢呢,只是碍于大公子与三公子近来生疏,怕行事太过张扬,三夫人会有难处。”
明明是自个怕引人非议,却说成是她九丫怕事。这话说得实在漂亮,比起烟花巷的楼子里的姑娘还能说会道些,不过这小娘子也是那巷子里出来的。
且她的故事,可算精彩得能上说书先生的册子。自她与邹清音闹上后,临安城也将她的身世挖了出来。什么其母十多年前是某楼的头牌,因意外怀上了她而成为昨日黄花。什么她自小在楼子里当丫鬟无意卖身,可老鸨硬是要将长得水灵的她拉去接客。什么她很有骨气地用酒瓶砸了客人的头,于是好巧不巧地遇见了打抱不平的杨攸。
多少可怜,多少无奈,多么纯洁的好姑娘。九丫在醉仙居听人谈及小娘子的命运时,便有茶客如此评价。而听得撇嘴的柴胡却问她:“你如何看?”
“真是与杨攸绝配,一样的矫揉造作。我倒没打听到这么多的事,只听说她给过教养过琴姬的老鸨一笔钱。你不觉得她许多地方与琴姬太像了吧,长相倒是天生的,可神情神态却是做出来的。”
九丫那日便是如此说的,今日更觉得像,但只要是造出来的,皆有打回原形之日。喝了小娘子的茶,九丫清了清嗓,随后笑道:“倒是让姑娘操心了,你说得很是在理。夫君与大公子不合,我们为妻者也当避嫌。我喝了你这茶,怕是没机会再请回来了,日后想来也少有来往。”
小娘子哪里想得到九丫如此坦言,不禁干笑了一声,“三夫人言重了,同在府中皆能少有来往,这茶定是有机会喝的。其实若没有三夫人,我难入杨府。这人情,有一日定会还的。”
九丫应了个笑脸,心头暗叨着,杨攸不知能富贵多久,她此时进府可算是祸福难辩。人情?自已实在不敢应。“谈不上什么人情,自然也不用还。”
一壶茶已经见底了,九丫已与小娘子故扯了许久,看准时机,她起身告辞。小娘子也不留她,笑着将人送出了亭子,临到九丫离开时,她忽想起什么似的,开口又道了句:“三夫人,邹家小姐离开杨府时扬言要报复,我命贱,倒无所谓,但她似乎知道你曾找过我。所以,也请三夫人小心一些。”
听过小娘子这话,九丫觉得可以换作另一句,那便是:如今我俩是同一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什么报应,也有你的份。这是威胁还是提醒?她难得去管,因为不多时,她兴许已不在临安。
不多时是何时?九丫虽有离开临安之心,却迟迟定不下离开的日子,借口总是能找到的嘛。然而就在一拖再拖之时,秋已过半,也是这时让九丫铁了心离开临安。其中原因是因一封信,邹淼自庐州寄回的亲笔信函,信中言及数日前他们得到菜菜子的消息,颇有找到的希望,并请她前往庐州一趟。
与邹淼做了十多年的兄妹,九丫已经熟悉那一笔一画,从前只觉得那字写得邪性女气了些,而信中的墨迹如今落在九丫眼中却是那般的秀丽端庄。
这次的信,九丫没打算告诉任何人,包括茗玉。此次离开临安,也许不会再回来。她不能让茗玉徘徊于跟自已出走还是留下与大志长相思守的抉择之中。这样的选择太过残酷,曾纠缠了九丫数月,她又何忍茗玉再受其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