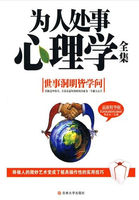茗玉确了解杨宇桓,若平日他定捱不到傍晚便会登门要人了,可眼下他却皱了下眉,又咬了咬唇,终于摇头答道:“由着她吧。”
由着她!茗玉听清了这几个字,愣了许久,直到杨宇桓进了书房才缓过神来。
“我没听错吧,姑爷从没说过这几个字。”她沉下眉来,心里带着微酸。
大志也叹了口气,“大约是因为其他事分了公子的心,不过事过之后便会好的。”
事过之后?那是何时,又是何事?
因为昨夜宿醉,杨宇桓差大志去请了一日的假,独自用了午膳便去了书房。茗玉进去添茶时,他正拿着卷宗看得仔细,应是听到脚步声,开口便道:“阿九,架上第四排的律典能递给我吗?”
茗玉手中的茶盘晃了晃,知道姑爷是忙糊涂了。她没好意思打扰他,只得捏手捏脚地挪到了书架下。然而站了小片刻,却不得不承认,第四排的书名没有她认识的字。逼不得已,她只得着了声:“姑爷,哪一本是律典?”
杨宇桓正要落下的笔顿时晕出一圈墨印,这才记起今日九丫不在府中,而且似乎这几日都不在府中。他拧了拧眉,指了指某一本册子示意茗玉拿过来。“你家小姐还没回来?”他只是随口问,接着又顺口说,“算了,由着她吧。”
茗玉抽了抽嘴角,觉得姑爷定是昨日酒劲未过,脑袋也有些不好使,她可听大志说过姑爷醉酒后会干歹事,于是远远地抵上册子后,她忙着退出了书房。
人一去,书房又静了下来,过了秋,蝉也不再闹。杨宇桓忽然觉得这种静有些瘆人,总归有个说话的人还是好的,他紧阖上双眼,清了清头脑,最终在心里暗叨了几遍“会习惯的”。
会吗?如此简单?他心知肚明,若真离得开她,兴许早绑了她运到远离临安之处。临安不会安全,很快。
再睁开眼,窗外的一阵急风吹得树叶微颤,他重新坐正身子,拿起架上的笔随意落下,随意开口:“站了这么久,还不进来?”
半掩的窗没见动静,房内却已多了一人。
“我只是怕扰了你的心神。”霍昀进来后也不客气,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抓起茶便喝下肚去,以慰藉连日来的辛劳,那可比军营里苦多了。
数月前,他来了临安,先是跟着九丫满街转,他本以为已经够受罪了,然而真正的苦差却在一个月前找上了他。
“阿九你不用再跟着了,派两个得力之人便可。你,帮我做另外一件事。”当时他这唤了二十多年“哥”的兄弟便是如此讲的。
飞檐走壁,对他霍昀来说确是容易之事,可是若那檐壁是皇家的呢?于是半月之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再见到杨宇桓时,忽然有了解脱之法。
“哥,我觉得比起窥探监视皇帝,不如直接解决掉,那样更干净利落。”
杨宇桓当时正擦着一支剪,闻言手上一用力,将之拆成了两段,“你也当我想弑君自立?”
霍昀眼见不对,忙收了笑脸,再不敢开这样的玩笑。
直到几日前他大约知道了其中原因,杨宇桓似乎想明确皇帝是否可信。然而今日,他才知道了真正原因,杨宇桓等的是一个“你不仁,我不义”的借口。
“半月后的北山围猎,皇帝在山中设下陷阱,势必要诛杀你。”这是他在皇宫的横梁上伏了数日亲耳听到乾宁吩咐近臣的话。
他果然等不及了,正如杨宇桓所料,长久的压抑之下,乾宁不会再退步,而昨夜的酒宴,只是缓兵之计。他与乾宁的角逐,一如高手对决,谁先沉不住气,谁就会露出破绽。
“半月,足够了。”杨宇桓轻勾起嘴角,不经意地露出一抹笑。半月,足够了,够他破解对手设下的局,够他重新造一个反败为胜的局。届时,乾宁会因为马上要得逞而疏于防守,这是绝好的机会。
霍昀看不懂他的表情,只在最后问了句:“哥,还需要我做什么?”
杨宇桓并未多想,答道:“阿九去了迦南坊,你帮我照看着她。在围猎前五日,再带她离开临安。”
就算有万分之一的意外,他也不会让她冒险。如此,此时此刻那些“习惯”便会有意义。
虽然一直惦念着九丫,但因为所谓的适应与暗自盘算的计划,杨宇桓接连有几日没见过她了。都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杨宇桓细数着秋去秋来,终于等到五日。
五日,九丫该回来了吧,然而从清晨一直到日头落了山,却没等到回府的人。不仅阿九丫回来,连霍昀也没回来。
“不会是私奔了吧?”前往迦南坊的马车上,杨三公子忽听得车外传来一个声音。
刹那了间,他眉眼一坚,已经阴沉了一日的脸顿时重获新生般地鲜活起来,不过这鲜活却是闪着一丝恶意。同车的大志看得清楚,眼见他要起身下车,忙一边催着马车快行,一边推在自家公子的肩头上,“公子,不过是路人闲话而已,你冷静点。”
杨宇桓闻言,如遭棒击,木讷了片刻,扯出张笑脸来,“本公子怎会不知,刚才不过是换个坐姿而已。”
大志抽了抽嘴角,看着他手中还未及放下的短剑,默默地闭了口。他想,这几日自家公子是太慌乱了,不仅要编排围猎之事,还要担心三夫人。那一颗心正吊在十万八千丈的悬崖上,脆弱得很,声音稍微大一点只怕也会震断了心头那根弦。所以,去迦南坊这一路,他提心吊胆,将喊得出名的菩萨皆求了一遍,只愿不要出什么岔子。
实则大志此人却没什么信仰,平生从来没有烧过香拜过佛,所以关键时刻哪有神仙显灵,加之预感这东西有时颇为邪门,越怕发生的事总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