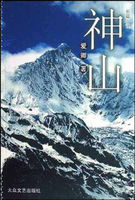)第一节 你穿了哪个女人的袜子
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大水以为他是可以达到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境界的,他相信他自己。结婚前他能做到,结婚后面对另一个女孩的真情表露,他也做到了。他不想凭借着感情的名义伤害哪一个人。
的确是一双女人的袜子。
头天的夜里,大水回来得很晚。厂里经常加班,回来晚,算是正常吧。躺在床上的高丽丽也还没有睡去,一边等着大水,一边想着小可。今天是星期几呢?高丽丽掐了掐手指,怎么才星期三?又掐了一遍,还是星期三。唉,时间太老了,老得走不动路了。真想推他几下,扶着也行,只要能走得快点。快点到星期六吧,这样就能见到小可了。刚学会走路的小可越发地顽皮了,小胳膊小腿受点小伤,快成家常便饭了,害得母亲连厕所都不敢去,时刻让小可在视线之内。上个周末回娘家,母亲抱着小可在门口迎着高丽丽。老远,高丽丽就看见小可的脸上打了一块补丁,淘气的结果。高丽丽心疼极了,却又不能过度地表现出来,因为她发现母亲又是满脸的歉意了。每次小可受伤,母亲都是一脸的歉意,为自己没有尽到看护的责任而不安。最近,小可都把母亲累瘦了。有时,母亲会逗着小可说,看你这个小东西,还不如耪二亩地舒服呢。
眼见着母亲消瘦,高丽丽真想辞了学校的工作,帮母亲带着小可。只是想想吧,母亲绝不会同意的。两个月前,婆家村里的书记找到高丽丽,说村里的小学校缺个代课的老师,问高丽丽去不去。事情来得很突然,高丽丽说我考虑考虑。书记临走说,村里好几个人在争呢,只有你去最合适,不服气,也写个诗歌给我瞅瞅。
先和大水说了。大水挠挠脑袋,事儿是好事儿,小可咋办呢?
再和母亲说了。母亲很是斩钉截铁,去,咋能不去呢。回去和孩子的奶奶商量商量,奶奶愿意带着孩子最好。实在不行,就把小可放我这儿。地里那点活儿不愁,学校不是总放假么。
母亲当然不会让高丽丽放过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是高丽丽的,更是母亲的。再说,代课教师对高丽丽也是具有一定诱惑力的。土地那么的拒绝她,她也深刻地不喜欢土地。虽然代课教师不是她的最爱,但比起土地来,总归要亲近许多。这个职业,可以让高丽丽只挂着农民的头衔,远离一个农民日常的粗糙的劳作方式。那就去吧,去学校吧。唯一的痛是要忍受七天之中有五天和小可的分别。
先是给小可断了奶。高丽丽学着村里奶孩子女人的方法,在乳头上涂抹上紫色的药水。这是背着小可做的。小可再掀开衣服时,就看到了和往日不同的一对乳。
小可,它们生病了。高丽丽吸溜着凉气儿,一副痛苦到极致的样子。
盖盖!盖盖!小可赶紧合上高丽丽的衣服,小身子也跟着盖上去,护住妈妈的两只乳。两只小眼睛紧张地四下搜寻着,唯恐有外来的力量伤害妈妈生病的乳。
妈妈就骗你这一次。妈妈就骗你这一次。高丽丽的下颚抵在小可的头上,泪如雨下。
白天很容易就过去了。小可一想吃奶了,就掀开高丽丽的衣服。病病,病病,然后不舍地放弃。晚上,小可太过思念甘甜的乳汁了,久久地不肯睡去。嘴上不说,也没有什么行动,只是让两帘挂着泪珠儿的睫毛轻颤着。
委屈了,你就哭出来吧,我的宝贝。高丽丽在心里呼唤。
还是轻颤着睫毛,泪花儿莹莹烁烁地闪。高丽丽的一颗心便粉碎了。
每晚都会重温这一幕。小可不在的日子里,她在温习中,等待着大水,听大水的摩托车由远而近地响起。一天的工作,一天的思念才告一段落。
上床,大水哎哟了一声。
高丽丽正欲拉住睡眠伸过来的那只手。
又一声哎哟。大水脱衣服。
你咋着了?高丽丽松开睡眠的手,问大水。
你还关心我?大水的责备。
原来,大水也会责备。深更半夜的,大水为什么要责备呢?高丽丽很是迷惑。
你到底咋着了?
挨摔了!
你不说,我咋知道你挨摔了呢?摔坏了么?伸出一只手,高丽丽扭亮了台灯。
大水右腿的一块皮不在了。疼么?高丽丽去摸,却被大水拦了回来。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然后,大水躺下,背对着高丽丽。
真是莫名其妙。大水这是怎么了?哪根筋没搭对?
直到看见那双女人的袜子。
咋回事?高丽丽咄咄逼视着大水。
不就是一双袜子么?有啥可大惊小怪的。我把袜子摔破了,就穿了平平的。不行啊?
平平?这个名字第一次从大水的口中说出来,可高丽丽觉得叫平平的那个女人已经在大水的生活中存在了很久。至少,叫平平的女人至少在精神上已经俘获了大水。而且,大水学会了比较。他在把平平和她高丽丽放在一起比较。
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平平是谁?是谁!
)第二节 我来告诉你平平是谁
平平是一个长发飘飘的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女孩,比高丽丽小两岁的从外地只身来打工的女孩。平平就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风把她刮到哪里,她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平平是聪明的,绝顶的聪明。大片的土地是在男人的掌控之下的,因此,要想拥有自己的土地,必须征服男人,叫男人心甘情愿地把土地割让出来。征服男人,首先要懂得如何去操作男人。这个能力,平平有。
平平懂得如何去操作男人,不同的男人使用不同的操作手段。她的操作是隐性的,全部潜伏在平静之下。操作男人们的同时,也操作自己。把她自己操作成一个清水出芙蓉般的人见人爱的小可怜,使得落在她身上的各类男人的目光疲惫不堪了,依然硬撑着不肯离去。平平在这样的目光群中轻松得意地游走的同时,对目光的发源地投去的是最诚挚的蔑视,即便它是厂长又如何。平平是独特的,她会在轻易获取一个清闲的职位后,灵巧地摆动一下身子,成功地从想品尝她味道的刀下逃生。这个游戏是危险的。平平也知道游戏的危险性,可是,越是有难度的游戏越是给人成功后的享受。不动声色地玩着游戏的平平,目光一直在游戏之外,她在寻找一个非游戏,这才是平平做游戏的初衷。
适时出现的大水,就是平平要找的那个非游戏。无论多么智慧的女人内心都是脆弱的,都需要非游戏给予她的支撑和宁静。寻找非游戏,其实就是寻找女人心灵的家园。
平平开始把心思往大水身上迁移。她知道要想俘获身置游戏规则之外的大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越是简单的事物就越是坚定和强势的。但是,简单一旦动摇了,极可能发展成永恒。不怕,慢慢来吧。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小可。
果然,一提到小可,大水的话多了起来。上次去小可的姥姥家,小可还不会唱歌,只隔了几天,小可真是了不起,会唱歌了呢。
小可那么棒,一定是随了爸爸的。平平不会忘了由衷的赞扬。
平平的话,大水听着很顺耳。听着顺耳的话,多听一些,是有益的,起到一个愉悦精神的作用。平平那么善解人意,那么愿意倾听和分享大水生活的点滴。大水能拒绝这样一个平平的走近么?他也的确需要一个人的倾听和分享。
这一时刻平平和大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除了正常,没有不正常的成分。能正常就好,大水能接受平平的正常走近就好。平平不着急。
大水是一个允许任何人走近的人,从来不拒绝任何人的友谊,男人的和女人的。因为他对任何人都不构成伤害,所以,大水的人气是相当旺盛的。只负责检验成品的平平有时间走近任何人,当然也有时间走近大水。想走近谁,完全取决于她个人的喜好。平平走近别人,或许会很快招来非议,走近大水就另当别论了。尽管大水来这家新厂的时间不长,但他已经像一件合格产品一样快速经过了人们的检验,并且,人们给大水贴上了合格的标签。大水的标签是“无坏心眼”牌的。
这样一个品牌的产品,是不轻易被异化了的。
这种环境下,平平离大水很近了。初为人父的大水,此刻需要释放为人父的快乐,以及为人父的小疲惫、小琐碎。平平及时地与大水分享了。大水为人父的所有情绪如一床被子,在不知不觉中被平平拉过一角盖在自己的身上。于是,这两个人呼吸着同一床被子散发的味道。
当初为人父的喜悦与疲惫等等美好的情绪逐渐被另外一种情绪取代时,大水沉默了。寂寞,这个不太受人欢迎的家伙要和大水结伴而行了。
大水的寂寞来源于高丽丽。当大水试图在高丽丽的心里寻找他的位置时,他发现,他的位置早被女儿占去了。高丽丽的心里已经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地。女儿把高丽丽的心灵空间占得严丝合缝,大水即使扁着身子也挤不进来。好不容易盼着高丽丽带着小可回家一趟,高丽丽的漫不经心,高丽丽的目中无他,最伤他尊严的是高丽丽的催促。他什么都不说,因为他深深地爱着。他爱是他老婆的高丽丽,这是从看见她第一眼就决定了的。高丽丽无论怎样,他都会宽容她,他都不会停止对她的爱。
大水却制止不了寂寞的侵入。
平平是何等的精明,她看出了大水的寂寞。寂寞的情怀揣在大水的怀里,平平尽量避开它,不去碰触,只装作没有看见,心里却是乐开了花儿。寂寞是男人的软肋,只要有寂寞就好,它将是平平走进大水内心的一个缺口。
平平想走进大水的内心,需要借助一个很现实的道具。没有这个道具,平平也会利用其他的道具。利用它了,是因为它的恰好存在。它是大水新买的摩托车。
平平说,我害怕。
平平说,要你用摩托车送我。
平平软软的眼神,软软的腔调,是大水无法拒绝的。
不就是接送一个女同事上下班么?他大水的摩托车又不是没坐过女同事。她们和男同事一样,只要有什么需求,第一个被想起的人,除了大水还是大水。好像大水就是为了随时被人需要才存在的。
平平不住在厂宿舍,在距离厂子四五里的地方,租了一间平房。
初时,大水的确为了平平说的那个害怕,只在厂里加班时才接送平平的。后来,接送平平竟成了习惯,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反正,接送平平的路线和自己上下班的路线基本是一致的。大水如是对自己说。
平平坐在大水的身后,两只手臂软藤般缠住大水的腰,两坨酥胸压在大水的后背上。手臂的缠绕和胸的压迫都是大水不可拒绝的,那是一个坐在摩托车上的胆小女孩子的正常反应。一帘长发被风的手掀起来,在大水的身后高高飘扬。
不就是一双袜子么?我都没有进她的屋子,是平平拿出来给我的。
大水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这是大水的可爱之处,也是大水的可恨之处。
大水无辜着,为他保持了身体上的清白。大水虚弱着,为他的心里除了高丽丽,有了平平的位置。
高丽丽围着大水转了好几圈儿。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她的男人么?是那个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太起眼的大水么?他有着那么多吸引女人的地方,自己怎么就没发现呢?莫非自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还是长了一只狗眼?
哈哈……高丽丽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大水毛骨悚然。
要不我今儿不上班了,在家陪着你?
去吧,人家还等着你送呢。再说了,我不上班,班里的孩子谁管呢?你管?你上过几年级呀?
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起我,一直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她们把你放在眼里,对不对?把你装进眼里,得多大个的眼珠子呀?哈哈……
你这样,我没法上班了。
大水沮丧而又无奈地看着高丽丽。
高丽丽过来推大水,走吧,走吧,我没事的,就是觉着好笑。
真没事?
真的。
真没事——才怪。大水的摩托车声犹豫着远去了。笑容僵在高丽丽的脸上,想褪去,却又接不到大脑的指令,只好原状待命了。
刚才笑的那个人是谁?是自己么?自己为什么要笑?难道发生了很可笑的事情么?
高丽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脑拒绝工作。她只是机械地去了学校。
学校里的学生怎么都变成了小虫子呢。无数条的小虫子蠕动着,往高丽丽的皮肉里钻,往高丽丽的眼睛里钻,往高丽丽的大脑里钻。连骨髓里都钻满了小虫子,胀痛难忍。一只小虫子的袜筒套在校服裤子的外边。不对,是两只小虫子。三只、四只……小虫子在蠕动,袜子在飞舞。
对,袜子,是袜子,可笑的袜子。
她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了,因为袜子。
谁让你们这样穿袜子的!
高丽丽一声断喝,小虫子们吓得把袜子藏进裤腿里。
高丽丽也被自己呵斥得清醒过来。眼前的是她的学生,不是小虫子。
抱歉,老师不是故意要批评你们。
学生们嘻嘻地笑了,表示了对高丽丽的谅解。
没有心思讲新课。高丽丽给学生布置了作业,坐在讲桌后边发呆。脑细胞依旧做静止状。时间不长,第一颗脑细胞开始活动了,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它们决定不再受高丽丽的控制,不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男生A、白袜子、吻、大水、小可、一双女人的袜子……活跃着的脑细胞轮番出现它们的影子,转瞬即逝,哪一个也抓不住。它们在和高丽丽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一片混沌、混乱。
混沌和混乱霸占了高丽丽。霸占了白天不算,夜晚还要继续。它们要高丽丽还回原来的清晰。
梳理是一个异常缓慢和艰难的过程。
高丽丽终于支撑不住了,她需要睡眠。在清晰恢复之前,混沌和混乱手牵着手坚守着,高丽丽只好借助安眠药的力量来驱逐坚守者。
村里的老赤脚医生那里只剩下十粒安眠药片。高丽丽说,您都给我吧。
她拿了装着十片药的瓶子回家。饭未吃,衣未脱,吃了两粒药躺下。不小心,推到了小药瓶,余下的几粒药散落在床头的写字台上。不管它,睡吧,睡着了一切烦恼都没有了。
大约八点的样子,大水回来了。
)第三节 瓶里的安眠药呢
大水先看见了倾倒在写字台上的药瓶子,然后是昏睡的高丽丽。
大水抓起药瓶子,晃了几晃。晃动的结果是惊骇。弃了药瓶儿,去摇高丽丽。高丽丽深深地沉在睡眠里,丝毫感知不到外力的作用。大水急了,掐着高丽丽单薄的小肩膀,更加猛烈地摇动。醒醒,你给我醒醒!
高丽丽用力地将沉甸甸的眼皮撑开一条缝儿,我困,别理我。
我问你,瓶里的药呢?大水的眼角都快瞪裂了。
我——吃——了。高丽丽的眼皮又合上了。
啪!大水的巴掌甩在高丽丽的小脸上。
天啊,我打了她!我怎么可以打她?!一个大水说。
我必须要打她,把她打醒,否则她会睡过去的,永远永远不会醒过来……一个大水说。
啪!啪!啪……
有红艳艳的汁水顺着高丽丽的嘴角淌下来,高丽丽的眼依旧紧紧地闭着。
你给我醒过来呀!醒醒啊!
大水哀求着高丽丽,巴掌一个接着一个地抽过去。
突然,大水的手掌来了个急刹车。高丽丽的一对媚眼,睡意全无,冷漠地注视着大水。
我就知道,会把你打醒的。大水弱着声音,软绵绵地摊在床上。
——还打不?
——不打了。
——打够了?
——打够了。
该我打你了。
说着,高丽丽跃上大水的身子,十根手指柳条般拂上大水的面庞。大水痴痴地笑,不躲不闪,承受着纤细的涤荡。
终于,高丽丽被自己累到了,伏在大水的身上喘息着。
——累了?那就睡觉吧。
——不困了,我想和你说说话。
——你下来,躺着说。
——就在这儿说,这个地方多舒服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