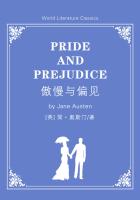院子里有葡萄架,葡萄枝叶沿着几根木支架攀爬到房顶边缘,屋檐下因此有了一片宁静的阴凉;阴凉的葡萄架下,有一张半米高的方桌和几只矮脚凳,一只花猫卧在矮脚凳上打呼噜;院落一角有块菜地,种着绿油油的蔬菜,我认得出的有芹菜与西红柿;菜地中央,一株叶片肥大的绿树懒洋洋地伸展着枝条,我歪了歪头,透过叶片间的缝隙,看见几枚如同婴儿脸般挤在一起的无花果,才知道这是无花果树。推开玛丽亚家用旧木板拼合的院门时,玛丽亚的妈妈正在葡萄架下泼洒清水,见到我,她苍白的脸颊绽开笑颜,柔弱的笑容朝我流过来,像一勺在微光中慢慢融化的冰淇淋。那只正打呼噜的猫被我吵醒了,它支起半个身子,不屑一顾瞥我一眼,然后躺下继续睡觉。玛丽亚的妈妈不会说汉语,她看着我只是微笑,末了,白皙的下巴轻轻一启,头向一侧窗户微微转过,喊了一声“玛丽亚”。
院落里一片安宁,时间仿佛逆流而上,抵达一个我所陌生的旧时空。在这片旧时空里,我侧耳倾听,玛丽亚妈妈的声音如同落向湖面的一枚树叶,在下午几近停滞的光线里轻轻旋动。接着,我被玛丽亚领进她简单静谧的小房间。房间里的摆设我几乎都给忘记了。我只记得黄昏到来前的大半个下午,我与玛丽亚坐在她的小书桌前,一本接一本翻看我带来的小人书。
玛丽亚的爸爸是欢乐的源泉,当他推开门扉走进院落,整座房屋都在低低地欢笑。
玛丽亚的妈妈在厨房准备晚餐,我与玛丽亚紧挨着坐在前室里的一块色泽黯淡的地毯上说话,玛丽亚爸爸洗完脸擦干双手,墩厚的身影从我们身后一闪,就坐在我们对面了。许多年过去了,玛丽亚爸爸的容貌也像被时间侵蚀的许多事物一样,在我记忆里只剩下几缕粗略的印记,但他坐下之后随即展露的神情却至今如镂如刻。他漆黑的深眸惊喜地凝视我和玛丽亚,如同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大秘密。玛丽亚爸爸在欢喜中抹了一把并不浓密的唇髭,开口道:
“愿珍,你叫愿珍,告诉我,你的名字有什么意思?”
“不知道,妈妈起的。”
“啊,我可是知道,以后,我就叫你买尔瓦依提汗吧,珍珠,珍珠的意思。”
“太长了,我记不住。”
“我能记住,买尔瓦依提汗,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买尔瓦依提汗了。”
“玛丽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那可是个圣人的名字……玛丽亚是我的圣人啊,呵呵。”
玛丽亚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妈妈告诉我,这都是因为玛丽亚妈妈的身体有病。
“说说看,你们下午都做了什么?”
“看小人书。”我把手里的两本小人书递给玛丽亚爸爸。一本是《狼牙山五壮士》,另一本是《铁道游击队》。
玛丽亚爸爸随便翻了几页,很快合上书,抬起头,扬着眉毛对我说:
“怎么,玛丽亚下午没有给你讲故事吗?玛丽亚的小脑袋里可是像圆圆的石榴一样,装满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啊,那些故事都是从我这儿得来的,他快要把我肚子里的故事掏空啦。”说完,玛丽亚爸爸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玛丽亚,怎么样,给我们的买尔瓦依提汗讲一个故事吧。”玛丽亚爸爸伸手取过茶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大口。
玛丽亚笑了,抿着嘴摇了摇头。玛丽亚的眼睛漆黑而清朗。
“好吧,你还是要听我讲?”
玛丽亚点点头,以同样的喜悦回望着父亲。
一种向时光中搜寻记忆的沉迷之色浮现在玛丽亚爸爸的脸上。我从未听过如此陌生与新鲜的语句。但我又知道,这些语句的内容并不陌生,它就在我看到的世界里。但我们从来不这样说话,大人们几乎不提及它们的存在,倘若说起,也是用一种无法再带给人联想的口吻和词语。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使事物变成一个硬块,复原几乎不可能,而像玛丽亚爸爸这样,以一种新的秩序招唤和排列字词,使事物像花朵一样绽放,或像迷宫一样延伸,那简直无可想象,也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一种着迷的讲述,我完全被拽进玛丽亚爸爸的声音里,汉语在他口中像一块烫嘴的食物,需要在舌头上滚动一番才能下咽。但这多么有趣啊,那些以一种新的秩序招唤和排列的字词,像烤热的豆子,在他的嘴里神气活现地蹦跳着。
时隔多年,我已经无法原样复制玛丽亚爸爸在那个夏日黄昏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但我还是愿意蒙上双眼,取消现实的视力,一次次跃入记忆的深潭,努力采撷那个黄昏的声音与气息,因为那个黄昏乃至那个夜晚我所听见、看见的一切,完全改变了从此之后我观看和感知外部世界的感官的性能,甚至主宰了我的生命。
“一位大毛拉被国王请去做客,为了表示他对美食及享乐的不屑一顾,他在筵席上故意吃得很少;到了做礼拜的时间,他也有意多做几拜,为的是使大家对他增加一份敬意。回家后,一踏进门槛,他就心烦地大声吩咐家人铺开餐布赶快用饭。用饭时,他焦急地大口嚼咽,把羊肉抓饭的米粒也糊在了胡子上。大毛拉有个儿子很聪明,说:‘爸爸,你不是刚才在王宫吃过饭了吗?’大毛拉说:‘是的,但是,我当着他们的面吃得很少,不管用。’他的儿子说:‘那你做的礼拜也得重做了,因为你的礼拜也全是不管用的。’”
讲完故事,玛丽亚爸爸跟着哼唱了一首歌:
把长处托在手掌上,
把短处藏在腋下的人呵,
别自欺欺人吧!
在你归天的时候,
用假银子买些什么?
不善使用造物赋予你的恩赐,造物会将它取回。这也是那天晚上我得到的一个智慧,虽然彼时彼刻我并不理解它蕴藏的深意。也因为这句话,我如此揣想:一定是这些年我思考问题的方法出现了许多错误,否则,造物不会使我的记忆在如此重要与永恒的事物上衰退,否则,我一定可以用玛丽亚爸爸的口吻,在这里为你们复述更多像星星一般闪烁的小故事。而事实上,我只大概记得其余几个故事的名字:《白天看星星》、《大象和公鸡打赌》、《饭菜的香味与铜板的响声》……
晚饭我们吃的是一种光滑的面条,它长长地卷曲在白瓷碗中,与西红柿和芹菜一起,进入那天晚上我无比快乐的胃腹。
晚饭后,那块花毯摊开在我眼前的一瞬,整个灰朴朴的房屋就变成了宫殿。
那是玛丽亚的舞毯,一块织着方形和菱形几何图案的红底黑山羊毛花毯。
之前因为被邀请讲故事而羞怯退缩的玛丽亚这时候一改静默的神情,未经任何提议,已从自己房间取来花毯,又不声不响把它摊开在我们眼前。
我并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满眼疑惑看了看屋里其他人。只见玛丽亚的爸爸一只手端起茶碗,若有所思呷着茶,一只手指轻轻叩击膝盖,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只手形状粗犷,像是给石头雕刻出来的,仿佛历经沧桑,抚摸过一切柔软和坚硬的事物;而玛丽亚的妈妈,抱着膝盖坐在地毯上,面容安详,柔暖的笑容挂在嘴边,仿佛历经了几百个世纪。
站在花毯上的玛丽亚像中了魔!
铺开花毯,玛丽亚已经站在了花毯中央。忽然,她身体一挺,朝我俏皮地甩了一个眼色,就将双手举过头顶,接着是脖子与腰身,接着是双腿与乌黑的辫梢……转眼之间,她的身体突变成那些之前与她无关的事物,变为一切瞬息里我能想到的事物,溪涧中的水草,湖水里的游鱼,春天的梨树,徐徐降落的雪花,弹跳的火苗,天边的彩虹,摇曳、旋转、点足……谁知道那些手与腰与腿的节奏来自哪里,没有音乐,但音乐显然从她的每一个动作中流出;没有节拍,但节拍自然地在我耳边响起……玛丽亚的脸从未如此明媚过,亮如宫殿里的水晶灯,而玛丽亚的眼神,每一次经过我,都跟飘舞的丝绸从我脸上滑过没什么两样。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玛丽亚!,校园里的她,只是一个名字,而眼前的她,却是一切美好的事物……那花毯让玛丽亚中了魔!
玛丽亚的爸爸用自己的语言唱起了歌,玛丽亚听到了,一扭头便调整了身体的拍子,将节奏贴在了歌声之上……歌声像是在回忆,旷远的时光随着歌声浮出这个粗朴小屋的四壁……唱到动情处,玛丽亚的爸爸常常闭上双眼……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情不自禁地立起了身体,踏上玛丽亚的花毯,与玛丽亚一起跳起舞来……跳着跳着,玛丽亚的爸爸来到她的妻子面前,躬下腰,伸出双臂,说:来吧,我的帕里黛(仙女)姑娘,来和我们一起跳吧……玛丽亚的妈妈把手放在丈夫手中,挑了挑眉毛,又给了我一个大方的笑,便在丈夫的搀扶下,费了一番力气站直身体,然后缓慢地加入了舞蹈……玛丽亚快乐极了,她温柔地围着妈妈轻舞,将动作的韵律压缓放慢,舞步飘移,好似晴空里的烟云,直到附合了妈妈迟柔的节奏……而玛丽亚的爸爸,像只飞翔在天空中的雄鹰,展开的双臂以一种几乎静止的旋律庇护着他的两个仙女……
后来,我盯着那块花毯发呆,玛丽亚一家三人在花毯上的欢乐与沉醉,让我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畏惧:他们都在花毯上变了模样!原来的他们没有任何预兆,便遁形了。他们的手臂与腰身,面颊与眼眸,接连不断变成了一切我能说出名来的大自然:波纹、急雨、大渠旁的柳树、发白的芦苇、月亮下的小白兔、夏天裂口的哈密瓜,清晨寂静的沙土路、沙漠的炽热、悬在空中的老鹰、踩踏碎石发出的声音……小镇在秋天堆起的高高的棉花垛……花毯赋予他们魔力,驱使精灵潜入他们的身体,多种精灵,奇异又美好;而我又无法不困惑:当精灵潜入他们的身体之后,他们与那些精灵之间,是谁召唤了谁?我分不清到底是谁左右了谁,似乎彼此都招之即来,又挥之即去,似乎彼此都成为了对方。
后来,玛丽亚的爸爸和妈妈跳累了,他们挨着我坐下来。玛丽亚一个人留在了花毯上。她一个人在跳,她从芦苇变成流水,从风变成滚烫的沙子,接着变成急雨,变成紫色和大红色的指甲花,变成院子里的葡萄藤,变成从葡萄藤枝蔓间落到人脸上的星光……玛丽亚停不下来了。玛丽亚被花毯施了魔法!她手臂的动作,她脚下的舞步,一个接一个地变幻,一次比一次迅速,一次比一次急骤,没有过渡,没有停顿,不意不谓地陡变,以至于每一次转换都如电光般缭乱了我的眼睛,也使玛丽亚气喘吁吁。那些最初被我意会的舞姿,到了这一刻,我一概都看不清楚了。不光是我,我能感觉到,玛丽亚也几乎不暇应接了,每个舞姿都急如星火,骤如闪电,紧接着又惶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