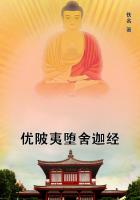确实我来四川,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山水风光的吸引,也就是自然环境。那时我想,要是有一个所有季节都盛开鲜花,到处一片葱茏繁茂的地方,能够让我静静住下来,在那里安心地生活,该有多好啊!
我还幽默地说过,自己是逃荒,而来到四川的。
这荒,我指的是沙尘暴。
正是离开故土那年,赤峰大地上起了沙尘暴。当时不知道它是沙尘暴,只感觉那个春天的风沙尤其大,去上班的时候,风衣大大的帽子必须拉起来,将头脸严严实实裹住,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
当知晓这三个字,初始内心是侥幸的,觉得自己也许是那个神尤为眷顾的不幸而万幸的人,你看,沙尘暴来了,我也走了。至今能回想起初来川时,那种被花草树木所迷失的情形。从塞外的春天出发,正好走进天府之国的夏天,便一下确定自己是来到了满意的地方,那些无处不在的树啊,它们令我的心掉进忧伤一样逼真的快乐。开始本是住在城中间的,但城外的花和树那样抢夺着我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城市外面的整个大地都开满鲜花,油菜花儿、豌豆花儿、蚕豆花儿、萝卜花儿、樱桃花儿、苹果花儿、梨花儿、桃花儿、杏花儿……每天我都得去看望它们,不去就不能得安生,去了就忘记回来,痴痴地在那花的海洋里游啊游啊游啊。后来索性搬到了城外去,推开窗便是田野,上面忽而花朵绚丽,忽而稼禾青青,而四围水杉高洒,竹簧密簇,芭蕉、枇杷、梅、海棠,点缀如画。
但是,渐渐地,我喜乐的心上,云烟样起了哀愁。
便是那古往今来诗歌里所吟的,乡愁。
最早是因母亲而起,当迷醉于鲜花,尤其是深冬里的花儿,我那样痛切地想到母亲。在记忆中,没有比母亲更爱花儿的人了,要是她也能够来到这天上地下都是花儿的地方,这深深冬天里仍香花绮丽的地方,她该笑出怎样的舒心啊!然后是手足、朋友、故旧,然后是整个故乡。当这温暖之土最美的梅和海棠盛放之时,我亲爱的故乡正是飞冰扬雪,地冻天封,最酷寒的时节。看着巴蜀大地如涌如漫的绿色,我总是想到故乡那些几乎寸草不生的高悍山脊,那些在凌厉的风中顽强摇晃着的小老树。
小老树,是故乡给自己那些永远也长不大的树们起的名字,它们立在山梁上,或是坡谷、旷野之间,永远在努力,永远不能够长大。它们是树的侏儒。
便想起故乡那些挥锹举镐,风餐露宿,年复一年,在大山上、在荒漠中,与风沙殊死搏斗的人们。
21世纪是生态的世纪,生态文明是21世纪最重要的文明。早在专家学者们这样的声音响起之前,赤峰人就开始行动了。到21世纪的曙光在地平线上耀然闪亮,赤峰人生态建设的战役已激烈地进行了近半个世纪。是的,他们开始得早,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在人人谈之色变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他地方的人们做着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那块土地上的人也尽可能地寻找机会造林植树。哪怕政策要求把树林砍倒,他们也随即在没有树木的地方悄悄地重新挖坑栽苗,让绿色再艰难而奇崛地忽闪、蔓延。
幸而,改革开放的东风浩荡而来,这种劳动更加气势雄伟,可歌可泣了。
一度,生态建设成为赤峰市的市策,举全市之力向荒山进军,从官员干部到百姓黎民,全部到山上去,从七十老翁,到稚稚少年,全部到山上去,真正是全民参战,全民皆兵。
任《赤峰日报》记者时,我对治山治沙、生态建设尤为关注,抓住一切机会去采访,每每面对那些震撼人心的劳动场景慨佩横生,热泪盈眶。本书里写到的“双臂皆无,只能靠两个胳肢窝夹着铁锹挖土,每挖一锹,身子艰难地一晃”的残疾人张金余,和“只有一臂,便用一只手和另一个胳肢窝持锹取土”的残疾人李金铎,现实生活中,我都看见过他们,只不过,他们是叫着不同的名字罢了。还有“任务所在的山坡,土薄得像一层皴,根本无法栽树……他就用柳条筐从一里半路以外的阴坡一点儿一点儿把土背过来。”利用歇工时间从远远近近的地方背来石头,在山坡上砌成“第一经济沟”大大字样的退休教师雷万均;弯腰驼背,耳聋,腿残,已过花甲,一人承担五个人任务的老人赵文;还有抡着比自己轻不了多少的铁镐,挥汗如雨干着的,年仅十二岁的没有名字的瘦弱女孩……这些人我都见过。他们每个都不止是一个,都是无数中之一。在大山的高处,只有石头没有土的地方,锹和镐都用不上,只能用凿子,一点儿一点儿把石头凿碎,再一点儿一点儿用手把它们捧出来,十个手指全部磨得鲜血淋漓,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搭个窝棚在山上住下来,天一放亮就爬起,直干到星月满空,渴了,喝几口装在塑料桶里的冷开水,饿了,啃几口装在塑料袋里的窝窝头,下雨了,披上块塑料布照样干——这是寻常的情景,只是,当它们是由年逾古稀的老人们演绎时,格外刺心。
我写了许多饱蘸深情的文章,通讯报道、报告文学、散文、杂文。我要为他们歌唱,为那些挥汗洒血、舍己忘我、重建绿色家园的人们,那些淳朴的、勤劳的、几乎不知个人享受这类词字的父老乡亲,我要把自己全部的激情和崇敬献给他们。
我做了当时所能做的全部,内心却愈来愈不满足,因为觉得那些文字不能发挥所希望的作用,它们只是刊登在《赤峰日报》上,收进赤峰市所编的书籍里,那是些不能摆脱地域和时间限制的书刊,上面的文字难以为外部世界看到,几乎没有与时光同行的能力。
这,便是我来四川的另一大原因了。
我要来到这具有强大文化力量的土地,吸纳,提升,使自己获得一种理想的文字表达能力,写一本能够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书,让所有的人们,远方的、未来的,让那些人知道在塞漠的土地上,人们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曾经和正在进行着怎样的殊绝的搏斗。是的,这搏斗一直在进行,年年,岁岁,因为那片土地是那么阔大,又是那么难于使树木成长,栽下去的树,有时好多年不能够长起来,只能不断地重栽,一遍又一遍地栽。
这是需要关注、鼓励、支持和帮助的事业,尽管故乡的人们,热情和坚毅是与生俱来而如星辰一样永不减弱光芒的。这事业其实不光是故乡人应为之献身的,它关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因为,正如已经人人皆知了的那句话,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
郑舜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却是故乡人性情禀赋的一个缩影,塞外大地上,这样勇于担当、擎天托地的男子汉如夏季草原上的青草一样举目可望。女作家胡文焉八年后返乡所见到的“今日曼陀草原”是一种想象,或者说是热切希望。多么希望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北京兴达集团第一副总裁常春佑”这样的人,能够把发展和责任的眼光、把巨大的资金力量投放到塞外草原。草原在呼唤,呼唤具有博大爱心的人们,献出自己的力量,去和那里勇敢淳朴的人们一起,还复她昔日的美丽容颜。
赤峰大地曾经是非常美丽的,我母亲出生的贡格尔草原曾经是浩瀚的原始森林,只要翻开志书,便可见到“千里松林,绿涛浩荡”、“花繁原野,长风送香”之类的文句。贡格尔草原便是席慕容魂牵梦绕的那“母亲的草原”,她常常在梦里见到的那条大河,真的存在过,只不过它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瘦削再瘦削,已几近消失了。
但是它会回来的,那清澈浩渺的水波,那蓝得如梦的湖,那平地松林千里,那野花儿一直开放到天边,都会回来的。只要我们献出劳动、智慧和爱,只要我们不懈地努力、努力。
这部小说基本挖寻出了塞外草原绿野变荒漠的根本的、历史的原因,也道出了还其往昔美丽容颜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这是我喜欢它的缘故,也是我欣慰的地方。这是我为故乡而写的一部书,因为倾注了巨大的深情、忧患和爱,相信它拥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祈愿有一天,自己能够像书中的胡文焉那样,乘清风而返故乡,带着献给那片神奇土地的赞助和吉祥。
故乡,你是每一个游子生命最深的牵挂。
你永远与心脏是同一个地方。
2009.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