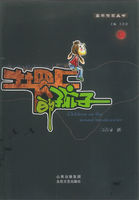第二天一早醒来,常乐伸伸胳膊腿儿,感觉自己生龙活虎,就好像昨晚其实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
真是神奇啊。
他仔细感觉神火宫,意念渐渐沉入黑暗世界,但见到的仍还是重重迷雾。
迷雾中有一点光,有隐约形,但就是不见神火宫的清晰模样,不论他如何向前,也总到达不了。
算了。
摇摇头回过神来,出了房间。
虽然老人告诫他不要再缺课,但他还是让朋友们帮自己请了假。
出了家门,来到刘家那边。
刘家宅子已经上了锁,他站在外面看了一会儿,才去问邻人里长家的位置。
里长是位挺壮实的老人,得知常乐是刘思友的同窗,想要祭拜后,二话不说,亲自架上驴车带常乐出了城。
常乐一再说告诉自己位置自己去找就好,老人还是把常乐送到了刘家四口的坟前。
三鞠躬之后,常乐半晌无语。
他不知说什么才好。
就这么在一家人坟前呆坐了好一阵子,他才坐着里长的车子回了城,心情复杂地回到学楼。
一路向上,来到阁楼,推开门后,不由怔住。
只见四个少年都笔直地坐在椅中,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一个个眼珠瞪得老大,眉毛拧得吓人,一另咬牙切齿的模样。
这干啥呢这是?
常乐吓出一身冷汗。
前方讲台上,一位银发老人坐在椅中打着哈欠。
老人清瘦,矍铄,一头银发不束,直接披于身后。
常乐瞪大了眼睛。
所谓时机一到……就是这个?
听到门响,老人并不转头,莫非转了转头,老人手中便立时飞出一道白影,准确地打在莫非额上,疼得莫非好一阵龇牙咧嘴,却不敢出声,急忙再次盯住前方,面目一时狰狞。
常乐一阵好奇,缓步走过去向前看,只见前方墙上挂了一幅画,其上密密麻麻满是鸟兽,怕得有上千只,有密集恐惧症的人肯定看不得。
“老人家……”常乐看了看盯住那画不敢移目的四位伙伴,转头冲老人拱手。
“你叫我什么?”老人皱眉,望向常乐,目光凌厉。
常乐本想笑,可感受到那目光,却不知为何怎么也笑不出来。
“昨夜……”他说。
“姓名。”老人沉声说。
“啊?”常乐怔住。
“姓名!”老人皱眉。
“常……常乐!”常乐急忙答。
“常常乐?”老人笑,“这什么名字?”
“是常乐。”常乐说。
“时常乐?”老人又笑,“怎么这么逗趣?”
“常乐!”常乐高声答。
“常乐?嗯,是这个学房的学生。”老人缓缓点头,“不过课都上完了一节,你怎么却才来?滚到角落里站着去。”
“您……”常乐张口要问。
老人瞪了他一眼:“不知称一声先生吗?”
“您原来是学楼里的先生?我怎么从没见过您?”常乐瞪圆了眼睛问。
“上课时间,先生可没工夫和你啰嗦!”老人面色一沉,手中白光一闪,常乐立时觉得额头剧痛,跟撞在铁柱上似的,咧着嘴捂住额头,二话不敢说,直接跑到角落里站直了身子。
怪不得他们连头也不敢转……真疼啊!
“给你说明一下——今天练眼力。”老人缓缓说道,“谁先从这幅画中找出十八只黄白色的猫,谁便能先休息。”
这个好!
常乐眼睛一亮,立即收敛心神,望向那画。
片刻后,掌中神火宫燃烧火焰,热浪一层层涌动中,常乐的目光变得与众不同。他盯住那画,于千只鸟兽之中仔细寻觅,不多时,一只只黄白色的猫便出现眼前。
一只、两只、三只……
他仔细地数着,终于数到十七只,却再不见最后一只。
不可能啊!
我这眼力不说天下无敌,也是万中无一吧?还有特异功能在,武者的拳脚轨迹都能看出,别人的暗中心思都能看破,怎么就差一只猫找不着?
常乐较上了劲,瞪圆了眼睛看。
老人在椅中闭目养神,并不多看常乐一眼。
不知不觉,外面钟声响,这一节课却告结束。老人一点头:“都没找出来?下堂继续,休息吧。”
那四人如蒙大赦,长出了一口气,都瘫在椅中——谁这么直挺挺坐一节课,还要聚精会神盯着密集图看,只怕都得累个半死,四人已经算是厉害,只是瘫倒。
“大哥……”莫非转头招呼常乐,却见常乐目光如电,还在盯着那画看。
“别打扰他。”蒋里轻声说。
“可是先生已经让休息了呀。”小草说。
“这和先生的命令无关。”梅欣儿一笑,“乐哥是和这画较上劲了。”
正在这时,门外脚步声乱,接着,便有人推门而入。
却是一气来了十几位学房先生。
这些先生一个个面带怒色,瞪着老人,老人却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只是坐在椅上晃悠着身子。
“凌先生!”一位先生一拱手,强压着怒火说:“我等学房先生轮流教导常乐五人,最后由他们选择一人正式担任他们的学房先生,这是楼主定下的规则,你怎能说破就破?”
“我就破了,如何?”老人闭着眼,晃悠着说。
“凌先生,我们尊你一声先生,是看在你年龄的分上。”一位先生大声说,“可您不但不是学房先生,在学楼之中也不教任何一艺,只是负责整理花园,哪有资格来教这五位天才少年?”
“不错!凌先生,你趁楼主、副楼主和大先生三位去神火督学监办公事之机,占了学房,驱逐当值先生,这也太胡闹了!”
“你快出去!我等看在你一把年纪的分上,可以不与你计较,但你若再胡闹,我们必告之楼主,到时楼主不把你逐出学楼,才算怪事!”
四少年听得目瞪口呆。
这老先生一早来到学房,便说自己是他们的新先生,然后便开始整治四人。四人被别的先生娇纵惯了,初时不服,结果老先生弹指白光如电,打得四个少年龇牙咧嘴,不得不服,这才老老实实坐直了,盯着那画看了这么久。
怎么,原来这老人家根本不是学房先生,甚至……听这意思,连先生也不是?
一众先生大叫大嚷不休,老人则一脸云淡风轻,等他们叫够了,才转过头来,眯着眼看他们。
“你们也知道这是五位天才少年?”他缓缓说道,“既然知道,那就该明白一个道理——凭你们的微末本领,是教不好他们的。不要误他们的前程,去吧。”
说着,摆了摆手。
“可笑至极!”一位先生气极反笑,“我们教不好他们,你一个打理花草的园丁能教好他们?”
“就是!”一位先生厉声说,“凌天奇,我们敬你一声先生,是看在楼主的面子上,可你当得起这声称呼吗?”
“别再胡闹了,真的耽误了这五位天才学子的成绩,你可负不起责!”一位先生沉声说。
老人也不再说话,只是弹指如飞。
四少年看到这一幕,情不自禁地捂住自己额头。
白光如电,却是射向了一众学房先生们,那些先生们立刻捂住额头,惨叫奔逃,四下躲避,最后被生生打出学房。
“凌天奇,你等着,等楼主回来,看他怎么整治你!”
“凌天奇,你敢动手打人,我必告到楼主那里!”
“聒噪。”老人闭目养神,一弹指,白光一闪撞在门上,将门关闭。
四少年望着门口,好一阵咧嘴。
常乐盯着那画,目光炯炯,身外一切仿佛全是云烟,不能乱其心,扰其念。
老人微微睁眼,看着常乐,微笑点头。
许久之后,常乐用力摇了摇头,懊恼地揉着眼睛,败下了阵来。
“第十八只,第十八只!”他愤愤地嘟囔着,“你个小猫崽子,藏到哪里去了?”
老人看着常乐,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不成,我就不信了!”常乐自言自语着,瞪大了眼睛,盯着那画又看了起来。
老人笑得极是开心。
学楼院门开,有马车疾驰而入,来到车房,有杂役过来接过缰绳,安置车马。
狮炎楼楼主展誉、副楼主郭琛,以及大先生林腾,面带忧色,自车中而下。
“世事难料,难料!”展誉一边向学楼走,一边感叹着。
“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郭琛叹息。
“此事……总觉得有些蹊跷。”林腾皱眉。
“这种话,不要再多说。”展誉沉声说。
“楼主,可这事确实……”林腾忍不住说,“这一场大火起得不明不白不说,烧焦的尸体数目对不上也不说,单说县丞大人何等身手,怎么可能死于一场火灾之中?就算是公子苏康也不可能就这样……”
“林大先生。”郭琛打断了他,低声说:“方才督学大人话中的意思,你还没听懂?”
林腾怔怔。
“县令大人很快便要调任。”郭琛说,“此时,最忌发生会造成巨大坏影响的事。县丞大人离奇死于宅中,与县丞府失火县丞大人不幸身亡,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影响更坏?”
林腾恍然大悟。
“不要再议论此事了。”展誉说,“我们要按督学大人的叮嘱,对楼内学生交待好,此事既不能瞒住,便要引导好,不能让他们生出疑惑而四下胡乱议论。”
“是。”
副楼主与大先生同时点头。
三人刚走到学楼前,便见一群学房先生迎了出来,一个个满面悲愤,情绪激动,把三人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