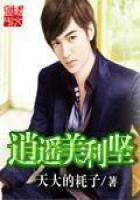来到当铺店门口,我又后悔了。
因为店门、窗户都上了板,从外面压根就看不到听不到里面啥光景啥动静。而两边又紧挨着别的店铺。
我只好又溜回胡同里,依稀估摸着当铺后门的位置,来到了一家院门口,透过门缝,望见正屋窗户有些模糊,知道那是亮光。
遂又两边观察了下,在确定了这家就是当铺的家后,便后退几步,一个蹿跳飞身把住了高高的墙头,翻了上去。
我坐在墙顶上往院子里看了看,除了东墙边垛着一堆柴火,其他再没啥。当然,院子太小,也盛不下多少东西。
我知道这儿的店铺都是两进两出的布局,也就是临街一排屋,后面还有一排,简称前屋、后屋。这院子相对就小多了。
我翻身把住墙头,慢慢出溜了下去,蹲在墙根下,听了听屋内没啥异常动静,就猫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窗户下,这回,能听到屋里的声音了。
只是,他们不像别的赌徒那样咋咋呼呼地喊破嗓子,而是偶尔有人说几句啥,好像是在赌牌的大小。
其中有那酒馆掌柜的,有当铺老板胡立仁,还有三麻子的声音,动静不大,但听声音都关注在牌上。
我听了一会,遂放下心来,既然三麻子没事,我也就可以回去睡个安稳觉了。
便又攀上墙头,跳回了胡同里,返回了酒馆老板的家。
其实想想那掌柜的,也怪磕碜人的,为了钱,竟自动腾出地方来,让我这个陌生人跟他老婆睡觉。
若我的话,即使给我座金山银山,也不会拿玲花做交易的。唉,人啊,贪婪是天性。
我返回酒馆后,轻轻推开门,见老板娘还在呼呼大睡,遂稍舒了口气。
只是她的睡姿太丑,可能是火炕太热,被褥已被她蹬开,就那么赤着身子四仰八叉地躺着,很撩人,也很不雅。
我转身掩上门,走到炕前,正解着衣扣,她的鼾声戛然而止,随即吧嗒了两下嘴,竟睁开了眼。
“你,去干啥了?”她揉了揉眼,冲我问道。
我心下一颤:“我?刚才去上茅厕了......”
她哦了一声,又一蹙眉头:“出去洗洗。”
我一愣:“咋了?”
她一瞪眼:“你说咋了!”
我靠,她还要呀?
这他娘的,花三十块钱来遭这个罪。唉,三麻子呀,三麻子,你个杂种净出些馊主意,这若再折腾几个回合,估计明天连路都走不动了,难道真要被人家硬拖出去?
我无奈地又出去洗了,回到屋里,竟惊喜地发现,老板娘又躺在那儿闭眼睡了。
心下窃喜,悄悄地上了炕,先把墙壁上的灯吹灭,脱了衣服,小心翼翼地捏着被角,钻进了被窝。
不料,刚钻进去,却被老板娘一把抱住。
我身子一哆嗦,还没反应过来,她竟翻身跨在了我的肚腹上,恶狠狠地低叫一声:“我的个宝呀......”
我娘,俺叫狗蛋呀,这一晚上下来,狗蛋也成瘪蛋了。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迷迷糊糊地睡着,就听厨房里丁零当啷忙活起来。
不一会儿,又听见这边屋门响,朦胧中,一双冰冷粗糙的手就伸进被窝里,抓住了我的大腿,我被震的一抖,猛睁开眼,见老板娘眯着眼笑嘻嘻地把脑袋贴在了我胸膛上的被褥上,那表情很惬意。
“醒了?”她咧嘴问道,满目含情。
看来昨晚她是真恣了。
我嗯了一声,疲惫地打了个哈欠。
“那就快起来吃饭,姐给你煎了一大碗鸡蛋呢。”她手在被窝里摸索着,声音颇为柔情。
咦,昨天那母老虎呢?难道真变成小猫咪了?
我心里疑惑着,乖乖地坐起来,在她的帮助下穿好衣服,下了炕。
“被褥我叠,你洗脸去吧。”她道。
我突然想起了三麻子,问道:“我三爷呢?”
她道:“刚回来没多时,和我家那个瘦狗在那屋睡死了。”
噢,原来他们在当铺那儿耍了一夜钱,刚回来呀。
这么说,这女人今天不赶我们滚蛋了?
我心里琢磨着,就出去洗了脸,回来,老板娘不在,但炕上已放着满满一大碗香喷喷,热腾腾的煎鸡蛋。还有一晚热水。
这生活,滋润呀。
我不由一阵感动,偏腿坐到炕沿上,端起碗就大吃起来。
刚吃完,老板娘也进来了。
不过,她今天变得漂亮了,准确地说是打扮漂亮了,头发挽着簪,梳的油光水滑,一丝不苟。本就通红的大脸蛋也愈发白里透红,可能是擦了粉吧,而且还穿了件新棉袄,枣红色的,两个大奶把胸前撑的老高,几欲喷薄而出。
腰间没系围裙,棉裤也是新的,蓝色,棉鞋面上还个绣着几朵花红柳绿的花瓣。
她咋这打扮呢?女为悦己者容?
我没文化,所以不太明白。
“吃饱了?”她笑咪咪地望着我,走过来抬手亲昵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受宠若惊,忙说饱了。
她轻轻搡了我一下,柔声道:“那好,累就先睡会吧,等快天晌的时候我再叫你。”
天晌叫我?干啥,撵我们走吗?
我一愣:“叫,叫我干啥?我三爷......”
我想知道三麻子把剩余的那二十块大洋给他了没有。心里既矛盾又忐忑。
若真赶我们走吧?三麻子应该还没得手,若不撵我们走吧,今晚又要累个半死,虽然我年轻轻的,鸟大体壮,又有副舵主俯身,可对这种体格如此健壮又极其贪婪的女人,我是真怕呀,而且是第一次有了怕的感觉。
“等中午,来了客,你在前面搭理,我下厨。”老板娘说道。
啥,啥?要我顶掌柜的那角色?还是充当小伙计?这万一当铺的老板又来,或他的小伙计来,我不立马暴露了吗?
我忙摇头:“我,不,姐,我真的不会照应客人呀,我大哥他......”
老板娘脸色猛地一沉:“这还有啥会不会的,要你做,你就做,那个瘦狗,估计到天黑能爬起来就不错了。”
“那......”我心悸地看着她,小声咕噜道,“我三爷把钱给你了吗?”
我想如果给她了,就没有义务再给她干活,这样还能安全些,不至于撞见那可恶的一老一少而露馅。
老板娘一楞:“钱?啥钱?噢......”她得意地一咧嘴,“不急,等过两天再说,嘻嘻......”
她说完,脸上竟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
我娘,这看来真要把我们留这儿了。
简短截说,中午,我战战兢兢地接待了两三拨食客后,总算没碰见熟人,尤其当铺里的那俩恶棍。
晌午过后,酒馆又闲了下来。趁着这机会,老板娘挎着篮子出去买菜去了。
我来到三麻子的屋里,见他已睡醒,正盘腿坐在炕上跟掌柜的算账呢。
原来,昨晚他们三人赌牌,掌柜的没钱,不想玩,但三麻子说没事,他先给垫上,结果一晚输掉了三十三块大洋。
等三麻子把借条挨张给他看了,掌柜的就坐不住了,哭丧着脸一个劲地小声说不算,因为他输的钱,最后都被三麻子赢去了,这左兜揣右兜里的事,能算欠吗?哥哥兄弟的,哈哈一笑就算过去了。
三麻子见他这样,似乎也不想追究,就道:“那好,这事先放着吧,等今晚咱再跟老胡玩去。”
掌柜的一愣:“今晚?你,你们不走了?”
他说着,转头望了望门口,咬了咬牙,小声冲我俩道:“这样吧,老哥,小兄弟,你们那二十块大洋我也不要了,你俩赶紧走吧,大不了我老婆回来朝我发顿疯,咋样?要不等她回来,你们就走不了了......”
咦?这事可行!不过三麻子应该不会同意,这大事还没办呢。
果然,三麻子嘴一撇,正色道:“老哥,你这话可不对,我们是欠你们二十块不错,但这三十三块你要先还上,账面两清了,我们爷俩才能走!”
我靠,三麻子这算盘真是打的精明,从昨天来店里到现在,不但酒菜白吃了,掌柜的还把老婆搭上了,最后一算账,他们反而还欠着我们几块钱,高!
那掌柜的一听,瞪眼张嘴地半天没说出话来,突然脸皮一颤,爬起来咕咚跪在三麻子面前,连声求道:“老哥,你,行行好饶了我吧,你若这样,你们逼不死我,我家那母老虎也得打死我了呀......”
掌柜的声之切切,并带着颤音,显然是极度恐惧。
三麻子烦躁地摆了摆手,道:“起来,起来,你这是干啥子,我还没死呢,这样吧,我们今天不走了,你也别怕了,今晚只要你顺着我的意来,等咱赢垮了老胡,这欠账的事就免了,行吧?”
掌柜的一听,连应。
三麻子让他出去烧水泡茶,说口渴了。
掌柜的忙不迭地出去了。
屋里,只剩下了我俩,三麻子冲我眯眼道:“那胖娘们妥了吗?”
我不知他要干啥,就点了下头,吭哧道:“反正脾气没那么大了......”
三麻子哦了一声:“这就好,不过,今晚你可不要贪恋了,你好好估摸着时间,等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你......”
他附到我的耳边,把后面的话低声说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