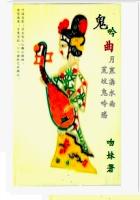我在跟李冰冰下了保证要娶她后,便在民兵队长姚明大同志的押解下出了门。
当然,姚明大还是非常顾忌我的面子的,或者是为了维护烈属李冰冰的声誉,刚出屋门,就冲院外墙根候着的民兵吆喝没啥事,要他们赶紧继续去巡逻。
然后才押着我回到了他家。
我和姚明大进了屋,见三麻子和王淑兰正对头坐在炕上神聊呢,看王淑兰那灿烂的表情,心情应该是很高兴的。
难道三麻子得手了?仰或是忽悠的差不多了?
我因被‘捉奸’之事,也没心情琢磨他们了,光我这一出,估计也得够郁闷几天的,唉。
王淑兰见我和他男人一块进来,忙笑问道:“咋了,明大,你们回来了?咱这大兄弟觉悟高吧,刚吃了晚饭就要去村口找你们帮着巡逻,你好好带带他,过些日子让他去当八路军,保证又能立大功!”
“是呀,”王淑兰话刚落,三麻子又紧接上了,“我这外甥,身高体壮脑瓜灵,革命意志和政治觉悟绝对杠杠的,我坚信,若去参了军,不用几个月就能成为英雄,当上大官......”
你娘,死麻子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都流氓犯被抓现行了,还啥革命意志呢。
我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炕下,而姚明大则沉着脸,冲王淑兰道:“你去西屋,我跟你说个事。”
我心里咕咚一下,坏了,他是要把我的丑事告诉王淑兰呀。
两口子一个民兵队长,一个妇救会会长,只要村里有一点小事都会沟通商量下的。
夫妻俩一出房门,三麻子的脸色唰地拉了下来,瞪着我,低声问道:“出啥事了?你是不是趴人家窗户上看大姑娘小媳妇的屁股了?”
我一咧嘴:“你说啥呀......”
“那到底是咋回事,赶紧说实话!”三麻子严肃道。
我见他如此严厉,也不敢不说了,就吭哧道:“就是,人家个女人叫我去她家学着扔手雷,我们正练着,他就突然进去了......”
我虽然轻描淡写,但三麻子很清楚我是个啥货色,恨恨地低声道:“你这是作死呀,深更半夜的,你去女人家里干啥,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我不服气地咕噜道:“那你还要勾搭王淑兰呢,大半夜的,一男一女的不睡觉,在炕上还能有好事?”
“你......”三麻子瞪着我,无语了。
我们这俩东西,是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
“我问你,那女的是不是情愿的?说实话!”三麻子又问道。
这种事,女人是不是情愿的是非常重要的,情愿,最多算通奸,不情愿的话,那就是死罪了。
我忙摇头:“没呢,我们就是闹着玩,她还挺欢喜的。”
“真假?”他继续逼问。
我不耐烦了,没好气地道:“我有必要骗你吗?”
他听了,这才舒了口气,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看来他有应对姚明大他们的办法了。
不一会儿,姚明大从西屋过来了,脸色还是那么严肃,一屁股坐到炕沿上,猛叹了口气,冲三麻子道:“老胡,你知道我们八路军的政策吗?”
我心一沉,知道他要把我的丑事抖搂出来了,下意识地低下了头,等着挨训斥。
不料,姚明大不等三麻子开口,就严厉地说道:“八路军是不信迷信的,而你,做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却顶风而上,打着给人算命,看手相的机会,兜售那些封建迷信,拉拢腐蚀我们党的干部,你到底包藏着啥子祸心?说!”
姚明大啪地一拍炕沿,惊的我一哆嗦。
我娘,这更坏了,肯定是三麻子勾搭王淑兰不成,被她告了状了。
面对姚明大的突然变脸质问,三麻子显然没预料到。
他一蹙眉,忽然呵呵一笑:“姚队长,你小题大作了吧,我跟淑兰妹子闲着没事,只是说着玩,哪还搞啥迷信呀,几句玩笑话,逗着乐乐而已,咱乡下老少爷们、娘们的不也都开开玩笑吗?你还当真了呀,唉,你们......”
“开玩笑?你说的轻巧!”姚明大伸手从兜里摸出一个玉坠,又啪地拍在炕上,“你这是开玩笑吗?”
晕,死麻子咋这么笨呀,你给人家这个,这不是找灾吗,忽悠明白了再给也不迟呀,这八字还没一撇就拿东西砸,你以为人家都是财迷吗,王淑兰可是革命意志高于天的妇救会长呀,政治觉悟不高的话,能当上会长吗?
就在我发懵的时候,三麻子却把嘴一撇,道:“小姚同志,你不会不认识这是个啥吧,就是给孩子拿着玩的破玩意,你以为我行贿你们了?”
“不是行贿,你说这个戴在身上能辟邪,打起仗来能让子弹自动避开,这不是封建迷信是啥?”
噢,他们说到这儿,我猜出了个大概,可能是三麻子要把玉坠送给王淑兰那孩子(孩子在她娘家)戴着,也顺便忽悠了几句。
我见那玉坠通体翠绿,起码值几十块大洋,看来三麻子为了勾搭上王淑兰,也是下了血本了,可惜姚明大同志不识货,经三麻子这一说,以为是块假玉呢,随手又扔到了三麻子怀里。
三麻子在姚明大强大的政治思想攻势下,顿感自己翻下了极大的错误,并认真虔诚地向他和随后进来的王淑兰认了错,道了歉,保证以后要提高觉悟,绝不学敌占区那一套,在这儿好好改造,尽力做一个对根据地有用的人才。
姚明大夫妻这才罢休,最后又安慰鼓励了他几句,夫妻俩一个提着枪继续巡逻去了,一个回到西屋睡觉去了。
其时,已是后半夜了,想想我们俩人,这刚来不到两天,一个成了流氓犯,一个成了神汉,不但大搞迷信活动,拉拢腐蚀党的干部,而且很可能还有别的企图。
这个罪,可真是不小呀。
看来,我们这种人渣,真是不适合在这土壤中生活。
姚明大夫妻走后,三麻子在那沉着脸呆坐了一会,抬眼见我也在发愣,遂没好气地道:“铺被褥,睡觉!”
我心灰意懒地铺了被褥,吹灭了墙壁上的煤油灯,连衣服都没脱就躺下了。
黑暗中,三麻子长叹了口气,低声咬牙切齿地对我道:“找个机会,把那姓姚的干掉!”
我脑袋轰地一炸,啥,啥?要杀民兵队长姚明大?我娘,这不是找死吗?这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呀。死麻子是不是疯了?
我忙小声道:“三爷,使不得呀,咱不是来避风的吗,这万一……你的仇还能报了吗?不行,绝对不能莽撞。咱还要在这过年呢。”
三麻子冷哼一声:“放心,小子,三爷心里有数,人的杀,年还要在这过......”
你有个屁数,有数就不会被那个王淑兰出卖了,哼!
我烦躁地转过身,背对着他,不再理。
“老子走南闯北几十年,玩过的女人无数,没想到在这破山沟里翻了船,奶奶的,走着瞧......”
三麻子自言自语地嘟囔一阵,见我不理他,也就揣着怨恨呼噜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醒来,因为不是英雄了,而是成了再教育的对象,所以王淑兰就不再端水伺候我们洗脸。
姚明大也没好声气,吃饭的时候,那态度和口气颐指气使,颇有些领导训斥下属的味道。
自然,原定的去附近各村宣传演讲的事也就取消了。
我估摸着,这儿也住不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把我俩赶走,最多寻个空屋破房子栖身,而且还会成为民兵重点监视的对象。
这他娘的一夜之间从高峰一下子跌落到谷底,那滋味,真是五味杂陈呀。
明天是腊月二十三,北方的小年。
王淑兰叮嘱姚明大出去的时候顺便割半斤羊肉,小年包顿饺子吃。
并从裤腰里掏出一个布包,翻了一阵,凑出一毛钱给了他。
三麻子乜眼看着,并没吭声。
姚明大走后,外面又叽叽喳喳涌进来一群妇女,嚷着要听英雄演讲,皆被王淑兰以我们忙为由,劝走了,不过,我从窗户里发现,人群里也没李冰冰,估计她是没脸再来了,唉。
妇女们刚走,三麻子对进屋的王淑兰道:“王同志,你们这儿今天哪儿逢集?”
大妹子成了王同志,王淑兰却并不感到诧异,奇怪地看着他问道:“俺村今天有集呀,在村口那儿,逢二排七,咋的了?”
三麻子哦了一声:“不咋的,来了两天了,怪闷的,我和小子想去集市上看看,可以吗?你们不放心的话,可以派个人跟着。”
他这一说,王淑兰反而不好意思了,忙说不用,你们也不是坏人汉奸啥的,就是有点老思想,等在这儿住段时间,多感受下根据地的良好向上的风气,思想就会进步了。到那时,咱们还是好同志,好战友。
三麻子谢了,带着我就出了门,穿过大街,来到了村口的集市上。
这集市不大,但很热闹,因为是年集,人也多,卖啥的都有。
当然最热闹的是卖鞭炮的,几个小贩为了吸引顾客,争相挑着竹竿燃放自家的鞭炮。
有小贩站在独轮车上,挑着杆子“噼里啪啦”放了一串鞭炮,大声吆喝道:“乡亲们,不服的往这儿看,八路军打鬼子,一个是一个,老万家的鞭炮,个个杠杠的......”
我靠,为了卖个鞭炮,这都扯到八路军打鬼子身上了,真是与时俱进呀。
我们花一块大洋买了一只大山羊,让屠户现扒了皮,拾掇了下水,而后又割了五斤牛肉。
这一下子,把周边几个商贩看傻眼了,我娘,这哪儿来的财神爷,咋这么有钱啊。
三麻子也不搭理,让我扛着羊,提着牛肉就大摇大摆地往村里走。
刚到集头上,我惊喜地发现了在人群中抱着孩子的李冰冰,心下一阵激动,忙走过去叫了声:“妹子。”
她闻声转头,见是我,也是一愣,脸蛋唰地红了。
人多眼杂,我不敢跟她多说,就把那五斤牛肉往她手里送,她哪敢要,背着手直往后缩。
没办法,我又赶紧从兜里摸出两块大洋,硬揣进了她怀里的孩子胸口里,扭头就走了。
三麻子对我的举动远远看在眼里。
待我走近,他问道:“就那娘们?”
我没吭声。
他叹道:“只要愿意,玩玩可以,可别陷进去拔不出腿来。”
靠,这都陷进去了,姚明大还逼着我要跟她结婚呢。
这些,我是不敢跟他说的,否则肯定会挨顿臭骂。
进了村,三麻子却并不走大街,而是拄着文明棍拐进了小胡同里,穿了两条胡同,三麻子抬手一指一家敞着屋门的破败的草屋,低声道:“吃了中午饭,你把这家的老头弄死。”
啥?我猛地一愣,下意识地又望了眼那草屋,见一个披头散发,极其肮脏的老头拄着根棍子从屋里出来,拖拖拉拉地往院墙边的露天茅厕走去。
我娘,他咋知道这家人的底细?我有些迷糊。
出了胡同,三麻子自言自语地道:“屋破院子脏,这能是正儿八经的人家吗,除了老光棍,还会是啥?”
“那,弄他干啥呀,怪可怜的,再说......”
我话刚到这,三麻子低声严厉地道:“啰嗦个啥,那种人活着也是遭罪,弄死他,会紧接着有跟他做伴的。”
“谁?”我一惊。
“民兵队长姚明大!”三麻子说完,眼里露出了一丝歹毒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