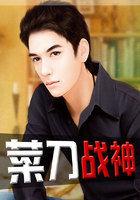我抱着驴脖子,假装拼力阻拦,三麻子也抡起文明棍朝着驴屁股啪啪猛打:“呀,呀,老实点,站住......”
这三弄两弄,把个驴车就严严实实地横在了山道上。
迎面而来的驴车上的鬼子一看火了,大吼着“八个牙驴”,就举枪要打,其时,双方相距约有七八十米。
这个距离,若对方不防备的话,我能一击命中,但鬼子们举起了枪,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身上,我就没辙了。
再怎么的,石头是绝对没子弹快的。
我脑袋轰地一炸,嗷的一声,抢地扑倒。不料,几乎与此同时,三麻子一文明棍又打在了驴的屁股上。
一闪一冲之间,那驴没了挡碍,轰地一头拉着车就向山下窜去。
车轮压着我的屁股就飞了过去,好在是空车,速度也快,我只觉屁股一颤,车子就稀里哗啦地过去了。
三麻子则防备不及,被驴车车弦一带,惊叫着抢了出去,咕咚一下扑在了地上,接连翻滚。
而山坡下的那车上的鬼子一看我们这狼狈样,不但怒气没了,反而乐的哈哈大笑。
大叫着:“@!#$%^&*!~#$%^......”
跳下车来就张胳膊拦驴车,只要被他们拦下,那驴是铁定要不回来了。
趁此机会,我抬眼望去,惊喜地发现,除了那俩鬼子,还有一个穿黑衣服的汉子,而且是光头加络腮胡,身形比俩鬼子几乎要大出一倍。
“大砍刀”!
我惊喜地差点叫出声来,一个蹿跳站起,手踹在俩兜里紧握着石块,边往下跑,边喊:“站住,站住......”
俩鬼子和“大砍刀”早把注意力灌注到了那飞奔的毛驴身上了,哪会理我?
只见“大砍刀”大吼一声,一个飞窜扑到了那奔近的毛驴前面,一把死死抱住了它的脖子。
在鬼子面前,正是他表现的最好机会。
不料,驴虽然被抱住了,但那驴车却因惯性,忽地冲了下去。
驴刹不住腿,往前一个踉跄,“大砍刀”也就势连连后退着,但双手抱着驴头仍死死不放。
这得多大的力气呀。
那俩鬼子见此,也嘻嘻哈哈地扑上去帮忙。
双方相距只有四五十米了,这个距离也是“飞石”的最佳空档。
我从兜里掏出一块石头,扬手“嗖”地掷了出去,石块在空中划了个漂亮的弧线,啪的击中了一个鬼子的脑袋。
那鬼子仰身跌了出去,几乎与此同时,我左手的石块也飞了出去,另一个鬼子也惊叫着扑在了地上。
这眨眼间的突变,把“大砍刀”惊的一愣,转头见我窜来,嗷的一声,撒开驴脖子转身向自己的驴车扑去。
而我也急着边奔边撒目地上,想再寻块石头,没想到的是,这山道上光溜滑的,竟没有。
我娘,我急了,转身往路边跑去,想从路沟周边寻觅。
但已经晚了,只听“大砍刀”狂吼着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剔骨刀,飞一般向我冲来,那步子沉重而又迅猛。
我大骇,也顾不得寻石头了,转身拔腿就往山梁上窜去。
“三爷,三爷......”危急时刻,我下意识地又叫开了三麻子,这也是形成的习惯,不管他能不能救得了我,喊出来就是安慰,就是希望。
然而,此时三麻子却趴在地上,连坐都坐不起来了,仰头见我奔至,大吼:“快救我......”
啥?
我一听更昏了,这自己的小命还危在旦夕呢,哪顾得上你呀,不定弯腰拉你的工夫,后背就会被捅上一刀。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三爷,对不起了,与其我死,还不如你替我挨这一刀呢。
我窜到三麻子跟前,他伸手要我拉,我却眼不眨地飞身窜了过去,拼命往山梁上窜去。
本来以为有三麻子在后面垫背,那“大砍刀”就不会追我,而会先把麻子捅死,再收拾我。那样的话,我也有时间寻到石头,反身相击了。
可万没料到,“大砍刀”也是个一根筋的二杆子呀,他不理脚下的三麻子,一个蹿跳掠过,迎头继续朝我追来。
我靠,命悬一线之际,我更昏了,哪还再有心思找石头呀,撒丫子就朝路边窜去。
突然脚下一绊,咕咚一下,我飞身抢到了路沟里,一头扎进了荆棘丛里。
完了完了,这回死定了。
不等我爬起来,只听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起,接着是一声闷吼:“你奶奶的......”
我能感觉到身后那个高大的背影挟着一股疾风,持刀向我扎来。
突然“啪”的一声枪响,我后背被“咚”的一击,一个沉重的物体结结实实地砸了下来。
我身子猛一哆嗦,以为刀已捅进了后背,心里一阵哀鸣,却没感觉到有刺骨的剧痛。
咦?难道被刀捅死来不及痛就完事了?也许是吧,比如那被我一石头击中脑瓜的鬼子,他不也来不及叫就见阎王了吗?
我娘,就这么就死了?也太轻松了吧,除了脑袋被荆棘扎的火辣辣的,其他也没啥感觉呀,原来死竟这么简单,只是,只是没来得及睡上刺死我的大砍刀的那个女人杜鹃,这有点可惜,还有玲花、“大花瓶”及龙种,还有温柔如水的小鹅,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赶紧向阎王爷去报到,想法子再托生吧,但愿别投到鸡狗鹅鸭或畜生那儿。不过以我的累累罪恶,估计阎王爷也不会再让我来到人世上来......
“滚起来!”
一个声音在我头顶上大叫,这,是小鬼?还是老阎王?不对呀,咋听着这么耳熟?
我努力地眨眨眼,突然醒悟过来,是,竟是三麻子的喊声。
“你死了吗?赶紧滚起来!”三麻子又喊了一声。
我这才如梦方醒,哇咔咔,老子这是还活着呀,好!
我忙身子一弓,我背上那个沉重的物体滚了下去,转头一看,原来是“大砍刀”。
只见他瞪着一双翻白的牛眼,直直地望着天空,剔骨刀却还紧紧握在手里。
他咋死的呢,应该是三麻子一枪击中了他的后心。
麻子,我没救你的命,你反而救了我一命,好人呀!
我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见三麻子拄着文明棍站在沟沿上,右手还提着那支王八盒子。
“三爷......”我百感交集地叫了一声,大嘴一咧,刚要嚎啕,三麻子却气哼哼地转身向山梁上走去。
我心里虚呀,也不敢再叫,抹了把脸,爬上路沟想去搀扶他。
三麻子头也不回地道:“把那畜生的脑袋割下来,留着祭奠!”
看来他的气还没消。
我返回来,抽出“大砍刀”手里攥着的剔骨刀,对准其喉管,“扑哧”一刀就扎了进去,因为血液不流动了,也没喷溅,只是在我顺刀的时候,从脖颈里涌出些浓糊糊的血来。
你个****的汉奸“大砍刀”,你不但领着鬼子害死了那么多与世无争的女人,还差点杀死我,这回,老子不但要把你的狗头拿去祭奠,还要睡了你的女人......
我心里恨恨着,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脑袋割了下来,看着他的一双牛眼还在瞪着我,我扬手跟皮球似的一脚踢了出去。
那光滑的血糊糊的大脑袋在半空转了几个圈,“呱哧”落到了路上,我走过去,一把捏住他的耳朵,提溜着就上了山梁。
这才发现我们的那辆驴车没影了,山坡下只有“大砍刀”的那辆驴车还在,那毛驴正在用嘴巴嗅着地上的一个死鬼子呢。
“三爷!”我冲着站在路中间的三麻子叫了一声。
三麻子道:“下去,把那俩矬子鬼的脑袋割下来,尸身扔路沟里去,把车也赶上来!”
我应了一声,把“大砍刀”的脑袋扔到他脚下,握着剔骨刀就奔下了山坡,先把俩鬼子的脑袋割了,把尸身扔进了路沟,而后赶着驴车就上了坡。
搀扶着麻子上了车,把三个咬牙瞪眼的头颅用盛猪肉的篮筐装了,扬鞭向“大砍刀”所在的大场镇奔去。
其时,天色已近黄昏,路上还没几个行人,橘黄色的霞光把四野映的光怪陆离,令人心清气爽。
“三爷,咱到镇子上住下吗?”我小心地问道。
“废话!”三麻子气还没消呢,这家伙心眼就是小。
我也不想解释了,再说也没法解释。
“那......鬼子怎么知道咱在镇子上?他们能来吗?”这是我担心的。
三麻子嘴一撇:“你是巴不得鬼子不来,好搂着那个小娘们,哼!”
我脸一热,麻子,记仇又吃醋,这是干啥呀。
“我不搂,你搂行了吧!”我也火了。
不料,三麻子却突然又呵呵笑了起来。
我心里猛地一沉,咦,难道这杂种真要夺我所爱?那可不行,这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忽悠到手了,他可别再横插一棍。
“小子,三爷老了,就留着给你吧,”三麻子叹了口气,道,“我估计不用到后半夜,武平县城里的鬼子们就会倾巢出动......”
啥?那,问题是,怎么才能让鬼子知道我们在镇子上呢?
我禁不住问了,三麻子冷哼一声:“这个你不用担心,自有人会去报信的!”
三麻子底气十足。
我也不便再问,还是赶紧赶路,早点见上杜鹃那个尤物才是当下最重要的,多在路上耽搁一分钟,就少一分钟的恩爱,因为麻子说过,下半夜鬼子要来呢。
还有,既然鬼子要来,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那样的话,我和杜鹃就没多少温存的时间了。
“驾!”我一扬鞭子,驴车哒哒地沿路直向远处的镇子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