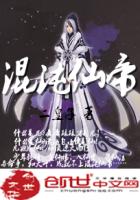唐绣瑾醒来的前一刻,脑中还回荡着自己死前那耗尽心力的最后一句。
她自然是等不到看那场现世果报了。
初夏的夜,空气中已有了一丝燥热。唐绣瑾甫一睁开眼,便感觉到了满身的湿意。她静静地睁大眼,面前是熟悉至极的浅紫色床幔,而她,端端正正躺在床上,手一摸,便是一头的汗。
这是……哪里?
唐绣瑾猛地坐起身,桌椅梳妆台,一件件都是自己最熟悉不过的摆设。便是窗台上那几株吊兰,也在月色下肆意舒展着叶子,仿佛隔年的时光在面前逐一回放。
她震惊地掀了被子,赤着足走到庭院中。月色正好,月光透过院中那棵银杏树落下斑斑点点的光亮,远处还有蛙鸣声隐隐传过来,给这静谧的夜添了几分活泼。
等等,银杏树?唐绣瑾抬头看去,确实是那棵与自己同龄的银杏树。是父亲唐英杰自她出生那日便在院中种下,如今算来,也应当有了十余载。
这不是梦,更不是厉韬将她救下了安置在某处。
在她的印象中,父亲被人诬陷贪赃那时,于抄家的当日,家中忽然起了一场大火,这棵树早已随着唐府的一切旧物在这场大火中烧毁了。
自己这是……回来了?
她觉得不可思议,不自觉地低头,正见到自己身上的罗裙,还是嫁人之前最爱穿的那件。
她身子微微颤抖着,走向那棵银杏树。树的背面,刻着几道纹路,每年一道,那是与她年岁相当的印记。她细细摸索着往上,十三、十四、十五,她心中细细一颤,手指停在了那第十五道纹路上。
也便是,如今的她,不过十五岁。
唐绣瑾提起裙摆,飞快地跑回了屋中,用火折子点亮了烛火。烛火随着她的动作而摇曳不休,在她停下脚步后,终于得以停息,在梳妆台上安静地燃烧。
铜镜中映出的,是一张尚显稚嫩的脸庞。
那双眼清亮逼人,没有肿胀的眼皮,没有干裂的嘴唇,没有星星点点的伤痕。那正是她开始一切之前的样貌。唐绣瑾心中仍是波澜四起,她不可置信地摸着脸庞,温热的,真实的,带着少女特有的馨香,眉眼轮廓,每一处都在提醒着她这一切的真实性。
确认了这个事实,唐绣瑾像是被抽走了全身力气。她转头看向方才被她折腾得凌乱一片的床铺,眼神慢慢转冷。
唐绣瑾多么希望,那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可她清楚地知道那不是。浓黑药汁灌入口中的苦涩,药物作用下痛苦不堪的每一日;杨菱珊锥心的每一句话,以至最后,来自自己亲生的孩子那致命的一刀。
刀尖入体的那一瞬,仿佛全身血液都被冻结。她来不及痛,因为那把刀的主人,以一种愤恨的目光看着她,稚嫩而愤恨。
那是自己怀胎十月生下的儿子,却早早被抱离了身边。
时间追溯到更久以前,那时她不过年方十五,与当时还是睿王的厉韬相遇。
她那样奋不顾身地奔向他,甚至违背礼法,怀着孩子嫁给了他,成了睿王妃。
再后来呢?她不曾想过,睿王竟怀着篡位的心思,在几番遭到父亲的拒绝后,恼羞成怒,对自己也冷落了下来。
可怜她挺着大肚子,在府中成了所有人茶余饭后的笑话。
再之后,便是唐府出了事,而她被软禁。到生下孩子,却又被逼着母子分离。
如今回想起来,原来这些事一环套一环,她唐绣瑾,原来在一开始便踏入了别人的局,甚至不需苦心设计,是她,为了那虚幻的所谓的爱,心甘情愿一步步踏入。
身体已凉了下来,心却因愤怒而火热一片。
唐绣瑾静静坐在梳妆台前,将前世的来龙去脉想了一遍。越想,便越是恨。
那恨是自前世带来的,穿越了生死,自然轻易不得解脱。颊旁不知何时沾了泪,冰冷一片。她用手背将泪一擦,再抬眼时,眼中已是决绝。
厉韬,杨菱珊。
我既没能看到天降惩罚,但上苍既给了我机会重来一次,那么今世,这笔账我们便从头清算。
噗的一声响,房内重新回归一片黑暗。
唐绣瑾在这黑暗之中回到床上,找了个舒服的睡姿,很快便入了梦。
这一回,不再是噩梦。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落下来,将半间屋子都照得亮堂。
“起床!起床!”熟悉的八哥鸟叫声响起来,唐绣瑾慢悠悠睁开眼,正见到小秀自外面端了一脸盆的清水进来,而那只八哥鸟,端端正正站在桌子上,对着她的方向一声一声重复。
这是她养大的鸟,因太过聒噪,每夜都养在小房间之内。因唐家家风严谨,小秀每日晨起便将这鸟带来喊自家小姐起床。
唐绣瑾有些爱怜地起身走到桌边,摸了摸鸟蓬松的羽毛,那鸟不甚情愿,躲了一阵,惹来唐绣瑾一声笑。
“小姐,快些洗漱吧,今日家里来客人,夫人特意嘱咐的让你早些准备呢。”
唐绣瑾微微皱了皱眉,“客人?”
她睡了一夜,气色很好。虽未梳妆,但面色由内而外地红润,更显得唇红齿白,分外好看。
小秀拧了干净的布巾给她,道:“小姐睡糊涂了?今日丞相大人的门生要上门拜访,老爷嘱咐了要好好招待的。”
门生?原来如此。
唐绣瑾微微一想便想起来了,外公当年是有这么一位门生,虽师从丞相,却从了商。早年与父亲也有些交情,因外公过了世,而外公唯一的孙女杨菱珊就寄住在这府上,便来拜访过一回。
时间点对上了,她心中豁达不少,微微想了想,嘴角攒出一个笑来,接过布巾细细擦了脸,换了得体的衣裳,这才出了房间门。
她要先去找一趟杨菱珊,今日可有一出好戏要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