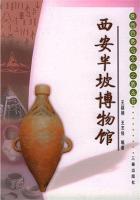民国女校里也有同性恋。但大多带点反封建的意思。市面上男人不可靠,要么是老家有老婆的已婚男,要么是行为不端不靠谱的“浮荡少年”,女校同学们对婚恋失去信心,便躲到姐妹情里找温暖,时间久了,一不小心发展出同性恋情,在所难免。
凌叔华写《说有这么一回事》,女学生云罗和影曼排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假戏真做,坠入爱河,形影不离。结果后来扮演朱丽叶的影曼嫁人,云罗陷入到无限的惆怅中。
庐隐在小说《丽石的日记》里有大胆剖白:“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以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清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恋爱了。”由此可见,民国女校的同学们,不是因为相互迷恋对方的肉体,进而发出恋爱的。她们更趋近于柏拉图的精神之爱,是你牵着我,我牵着你,铸造一个小小的温暖堡垒。外面的世界风雨琳琅,只要你我相连,就有温暖的小天地。她们的感情十分纯真,不是随便玩玩而已,她们因为怕,所以爱。
同性恋题材在当时可能是时髦。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也写了一篇有关女同学之间朦胧情谊的《同学少年都不贱》,也走柏拉图路线,后来她写《相见欢》,两位太太年轻时候,也有同性恋倾向,后来各自结婚,各自烦恼,但也“相见欢”。
徐讠于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崔万秋的《新路》里,也不乏女同故事的讲述。
丁玲也写过女同性恋小说,叫《暑假中》,对于sex的部分,有进步,写了,但也只是止于拥抱,接吻,剩下的,就留给读者自己想象了。比如,“嘉瑛觉到了那诚挚的眼光,和自己手上感到的一种压力,便很柔顺地把身子倒向她胸前,承淑便拥着她叫道:‘爱我!我要你爱我!’”
当然也有更直白的。郁达夫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里,就狠狠地写了一出“床戏”。郑秀岳和李文卿,一个为钱而投降,一个因为肉体而沉迷。扮演男性角色的李文卿被描绘成了一个男人式的形象,长得又高又大,脸上有“红黑色的雀斑”,脸盘子很大,“可以比得过平常长得很魁梧的中年男子”,再加上一副“又洪又亮的沙喉咙”,壮汉式的笑声,简直比男人还男人。可内心深处,郑秀岳喜欢的却是她的小舅舅陈应环。不是同性恋而做了同性恋。郑秀岳的故事,忽然就有了社会意义。
章衣萍的《松萝山下》和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也毫不客气,把sex的桥段,写得香艳刺激,大喊大叫。《退职夫人自传》里写:“我真忍受不住了,这样的夜里,你听外边又在下雨!给我一点安慰,像我丈夫给我的一样……亲亲我吧!你看,我心要跳出来了,我要死了……”
在《子夜》里,茅盾也写女同性恋,发生在女革命党人之间……阿弥陀佛。累不累?很累。绝不绝望?相当绝望。
美不美?也许,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