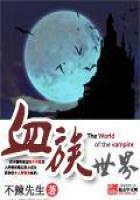“哦哦,属地上两位最勇敢的勇士要开始决斗了?”克拉尔从一扇门里步履轻快地走出,来到早已准备好的看台上,将戴着洁白手套的双手支在桌子上,“请原谅我来迟了。作为补偿,我为两位勇士举办了盛大的聚会,请来了两位曾经在乎、以后或许还会记挂于心的所有人。另外,我还精心准备了一个额外惊喜……”
“如果我,克拉尔·瓦沙克,没有猜错,我的小兄弟——鱼诺是决不会允许我当众偏袒他的,因此不仅今天的武器全部是最锋利的,并且在他们决斗时,这里会围满刽子手。他们除非一人死亡,否则绝不可能逃走,而我们则不醉不归,一起来商讨另一件事。”克拉尔拿起桌上的酒杯,摇晃着里面褐色透明的酒液,而后向里面挤了一滴血色的葡萄汁。
“我承认,我违反了魔法协会的规定,大度地向平民灌输了有关魔法师的知识。可我发誓那是为了你们。究竟是谁这样厌弃我,将我的好心呈现在魔法协会的大人们面前?”克拉尔瞥了一眼鱼诺,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酒,迷醉地闭上了眼睛,“总之,决不是我的小兄弟鱼诺。”
“好了,请恕我耽误了太久。”片刻后,克拉尔睁开了双眼。他转向鱼诺,笑容轻松自然,“该你了,亲爱的。我让所有人见证你,修改并拯救世界,对么?嗯,还有,用自己的力量,双手、双手!”他对着鱼诺握紧了右手,做出加油的手势,还俏皮地挤了挤眼睛。鱼诺不得不承认,若是真正的聚会,他会迷惑全场的女性。
然而现在是鱼诺的决斗,且被暗示了将一直处于魔法师的监视下,至死都不能使用一星半点魔法。否则克拉尔将永远羞辱他,在他想要拯救的人面前。
如此,鱼诺对世界而言,再无拯救。
“哟,你还在发呆,挑战的勇士!”埃弗里拾起地上的剑和盾牌,用剑与盾牌相撞的声音提醒着他的对手。
“你……竟然不恨克拉尔?”鱼诺望着埃弗里脸上轻松的笑容,心中充满了疑惑。埃弗里,他将要被迫为所有人演出一场死亡之舞,这场聚会踏着他们的鲜血欢庆,而他居然毫无怨恨。难道眼前的只是一场诡异的梦境吗?
“你也明白吧?在你还是阿尔瓦的时候,你的心里有过这座城堡么?有过与高尚沾边的任何一点念头么?当一件事物实在太高太远,它就消失了。我不比尘埃高贵一点,所以我想不到,也没资格想。反倒是你……”埃弗里忽然向鱼诺大步逼近,鱼诺看见阳光在他的剑刃上描了异常刺目的一笔。
“你就在我面前,不停地刺激我,让我记起童年的事——那个幻想尚未破灭的时刻里,所梦想过的所有事,还有现在的卑贱!”埃弗里的剑重重击打在鱼诺的盾上,爆出一片炫目的火花。透过它灼人的光亮,鱼诺看见埃弗里充满仇恨的双眼。它们让鱼诺明白,埃弗里所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折磨他,以爱之名。
“所以你也明白,克拉尔在利用你……”鱼诺略微失神的瞬间,盾牌差点压碎了他的头骨。他艰难地对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清晰地感觉到胳膊上的肌肉在颤抖。渐渐变得空白的脑海让他不断地产生一种奇怪的沮丧——就让那面盾牌压下来如何?怎样都会比现在轻松!
“你真是货真价实的魔法师!”连看也不看,埃弗里就已经知道了鱼诺的窘境,因而开始讥笑他,“那么你无论如何都要知道的答案,还是趁现在告诉你更好。”
“平民永远不会将贵族真正的蹂躏说出来。因为平民必须扭曲自己,使自己相信自己低贱,才能面对自己已经不想改变的生命!”
“你现在击打的,不正是贵族吗?!”埃弗里低声说出的真相龄鱼诺感到胸口犹如被重石击打,他闻到了血的味道,但同时也无比清醒。手里的盾牌开始在他的努力下慢慢倾斜,细微的金属擦划声渐渐刺痛了所有人的耳膜。
埃弗里的剑从鱼诺的盾牌上滑落,他机敏地趁势一滚,躲开了鱼诺的斩击,又荡偏了鱼诺连续挥向他的剑,用盾牌趁空隙击打了鱼诺的背部,趁鱼诺无力追击时迅速起身跑开一段距离,重新组织好自己的攻防。
“疼么?”埃弗里从盾牌与剑的缝隙中盯着鱼诺,笑容在染满灰尘的脸上变得狰狞,“你大概不知道,我在幼年便经常练习这招,与塞西尔。这一下,连他都会喊疼。”
“那你可以在盾牌后猜一下,我与达莲娜的父亲练过多少次这招。”鱼诺不为所动,神色自然地挥着手里的盾牌。然而埃弗里忽然冷酷地笑了,因为一股鲜血正悄悄沿着鱼诺的脚印蔓延,在他脚下画出一片树枝状的诡异纹路,就像古老而嗜血的禁忌咒语。
“它是血祭魔咒,我想你不知道吧?”沿着埃弗里的目光,鱼诺发觉了脚下的血泊。他耸耸肩,将盾牌丢在一旁,“正如你所说,我是魔法师,而你不是。”
“那可真要感谢上苍,我不是魔法师。”埃弗里讽刺道。他几乎要笑了,但对面的鱼诺忽然动了,而后埃弗里尚未绽开的笑容便永远凝固在惊讶之下。失去了盾牌,鱼诺的动作虽然露出了一些破绽,但明显变快了。在埃弗里分神回答的瞬间,鱼诺已经移动到埃弗里面前。埃弗里连忙举起盾牌,并且在一连串的火花中意识到,鱼诺的破绽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利用。因为,他来不及。
但鱼诺能支持多久?埃弗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很有耐心地等待着鱼诺的攻击停止。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鱼诺的脚步虽然露出了更多的疲态,但他似乎很有信心,一直没有停下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