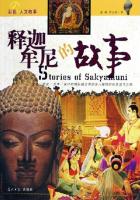孤独的外乡女人,坐在异乡的山坡上,想家。
哦,秋天啦。我爱它的高远碧透的天空中拂来拂去的白云,它的翠绿松林间比花朵更沧桑艳丽的红叶,它的透着寒意的碧水辉映着寂寞的蓝天,它的花肚皮的水鸟在镜面上划出的涟漪,它的猎猎飘扬一扯三千丈的悲风,它的欲留还去的无奈,它的欲说还休的悲伤,它的渐渐透进骨子里的苍凉。
就这样,从山下的村落里,突然飘出了时断时续的笛声,如梦似幻、丝丝缕缕地飘来缠绕我,缠绕我,一时越来越紧,越来越痛,瞬间便将我的心缠绑成茧!
我的心便在这茧里狂跳如鼓——我没想到在异乡,还能听到这熟悉的笛声,这最爱的像天空一样明丽悠远的笛声。
那吹奏的人,是你——那个优美少年吗?你有一双仅属于东方人的丹凤眼,眯起来的样子是那样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亿万年的沧海变迁之后,凤凰飞去,却将它超然物外的眼神留给了你!你站在故乡的草坡上,迎风横笛,衣袂飘扬,向着我们看不到的远方,用花瓣样的嘴唇,吹奏出丝丝缕缕的哀伤——
那时候,无人懂你。我枯黄的朝天辫,像你脚下的毛英英儿,向你淘气地翘着,示威,撒野;为了怕我掉进那条鱼虾可鉴的河流,你追我,逐我;而我,磕磕绊绊地去追逐红翅膀的蜻蜓、蚂蚱和妖媚的蝴蝶——它们在一朵朵花蕊里,提着花篮采蜜。
就这样,在他人的笛声里,我遥望千里外的荒坡,仿佛看见你栖身的那一抔黄土。我看见你飘逸的风姿,破土而出,随风而至,就这样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刻,孤零零的你来寻找孤零零的我。从林梢上、鸽哨里、从每一棵小草战栗的根部,都传来你忧伤的低唤:妹妹,妹妹,妹妹……
哥哥!我呼唤着你,向看不见的你伸出我的手臂。而今我的脸已刻满风霜,你却仍是一副少年的模样,在异地无名的山坡上,完好如初地来与我相见!
你带给我母亲的消息。透过你,我看见母亲的居所。她檐头的枯草,已经比她的头发还长了,数年前的秋天,在报社五楼的窗户旁,我向北遥望,尔后挥笔写下这些句子:秋深了,娘的长发
该在故乡的山岗枯黄了
在女儿的手指不能及的地方
正被秋风冰凉的梳子
胡乱地梳理着
娘呵,在你生我的时候
我们是母女
你不会想到30年后
为母亲梳头的女儿,是风
为女儿梳头的母亲,是梦写完后,朋友们相约到山上去,在北坡的乱树间,看见匍匐的荒草,颜色是熟透的黄,长及数尺,一缕缕像瀑布一样柔顺,果真像被梳子梳过了,朋友们说起这首《风梳头》,惊异于用词的准确,意象的苍凉,而我折身走开,不忍卒睹。
哥哥,你小小的身躯,如何温暖故乡那大片的黄土?我想你唯一的骄傲,是倚着母亲而眠。最卑微的母亲,也是一轮燃烧的太阳。她的光芒可以穿越沙土,爱抚你。哥哥,在沙土之下,你把身躯蜷缩成婴孩的模样,缩回到母亲腹中,你是安全的了。故乡那条险恶的河流,再不能生生地将你吞噬。
可是醒里梦里,犹是你伸着的手啊!哥哥,我恨不能啼破梦境,去拯救你;恨不能用我的手,去挽住你一闪即逝的生命;你的手就那么一直摇着,在浪尖上摇着,在水草里摇着,在石缝里摇着,直至渐渐沉没。你无望的求救之声,化为一串泡泡,日里夜里,在水面上叹息!
你像一片卑微的草叶,瞬间从我面前生生地消失,我该去哪里为你寻找凶手!亿万年的长河里,从来都是命如草芥,从来都是无理可讲,从来都是无迹可寻,这该诅咒的一切啊,我该去向谁哭诉,向狰狞的命运,还是仁慈的上帝!
于是我就只好一次次回到梦里,向梦去讨要希望。在梦里我将手伸向你,伸向你,却依旧够不到你,我向你哭喊着:哥哥,等着我,不要沉落,等着我长大,等我来救你……你报我昙花般的一笑,瞬间就化为了涟漪……
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过去,我小小的哥哥,你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该老了。村里那些小孩子,已经没有谁知道,曾经有过一个你;而你的坟丘,只有村里最年长的人,能找得到。逢年过节,我只好画一个圈儿,将纸钱烧给你。
那一年,我带着3棵小松树回到故乡。我拨开足以埋没我的荒草,寻找你;我知道你在最荒僻的角落里,等我;等我来看你,等我带给你世间的消息,等我将你刻进石头——我知道你怕自己睡得太久,忘了自己前世的名字……哥哥,我无钱为你竖一块墓碑,只好让小树为你做个标志。3棵松树分别栽在了父亲的檐前、母亲的檐前、你的檐前。然后,我就坐在你的面前,号啕大哭!
你可在与我同哭?哭父,哭母,哭自己!父母归去时人已白发,而你却是青青如盖的年纪。这叫我如何不耿耿于怀,这叫我如何放得下你!想起你总是泪湿青衫,想起你总是意气难平!
可是那3棵松树,很快也枯萎了。在死的悲伤面前,连植物都不愿意苟活下去!
哥哥,我该用几生几世,才能忘记你;哥哥,你们走了,却把我留给世间;你们走了,却要我活着,你可曾想过这生生分离的痛楚?
哥哥,在你和母亲的房屋之间,是否还留有我的位置?我需要的地方很小很小,不过是几棵小草的位置,不过是几只沙里狗做窝的位置。原谅我吧,我累了!想把自己的心,埋在沙土里。
流年里,我身背行囊,向着一个又一个远方,在每一个异乡,都不忘寻找你的身影,我相信在一个我从未到达的地方,你还活着,你只是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哥哥,那个曾在你笛子上拴一块红绸的女孩,如今也像她母亲一样渐渐老去。在你坐过的草坡上,我看见她痴痴遥望的身影。她粗糙的手,将凌乱的头发抿至耳后,耳朵上的银耳环像摇曳的铃铛。她干瘪的嘴唇,被秋风割裂;只有路过的大雁,听得懂她的呢喃……
芦苇花白了的时候,我看见她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歌唱:“在深秋的景色里我已是一朵凋落的花,为何我的青春时光,还在山那边,梦见心爱的少年郎?”
你离去的时候,我还只有小名,你不知我的大名,这么悠远幽深的路,你是如何找到我的?你的赤脚踩在荆棘之上,让我感到切肤的疼痛。为了寻找我,你将来自于同一个母亲的血洒在棘尖上,瞬间化成了粒粒的红果。
在白云之下,荒草之上,我看不到你的面容,但我感到你风一样软的手,在抚摸我童年的面庞;你冰一样凉的指尖,为我擦拭着拭不完的忧伤。
哥哥,似水流年里,是我遗落了你,还是你丢失了我?这短暂的相见,我能留住你什么,你能带走我什么,我们又能为彼此做些什么!看这广袤的土地,哪是我们的摇篮,哪是我们的坟墓,哪是我们的家园!相见之后,你是否又将沉入深渊,抵达黑暗,直到彼岸重逢的那天?
我伸出手,抓不住你,抓不住一缕最细的风,却从指间漏尽了前尘旧梦。我坐在扶摇的茅草丛中,独抱双膝,泪落如雨,不知谁能听见我心中的悲恸!
一只鸟儿从荆棘中飞出,围我盘旋低啼,声声啼血,又落到前面的树上对我殷殷叮咛几声,便远远飞去!
——妹妹,好好活着,替我活着,替我们活着!只有活着,才会有希望;只有活着,在黑暗的深渊里,我们才能获得最终的救赎!
——哥哥,我会活着,苦也要活着,累也要活着,死也要活着!替你活着,替你们活着!替那些渴望着生却被死神掠走的生灵活着!
隔一轮硕大的斜阳,你就这么披一身火的羽翼,越飞越远。哥哥,你可听见:在故乡,那个坐在门槛上的女人,犹在为你歌唱:
“风已经捎走过往,烈火焚尽了凤凰的翅膀,那个少年或许并不存在,那种感觉却地老天荒……”